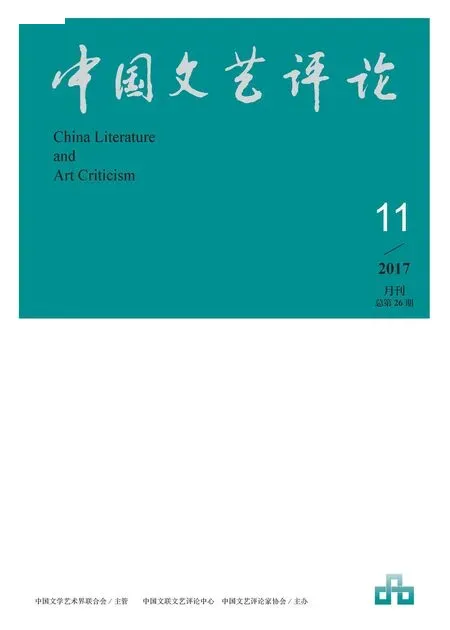冲突与反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张春梅
冲突与反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张春梅
本文尝试从媒介和粉丝的角度着手阐释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指出首要而且必要的一点是把握其媒介性和空间性,而不能惯性地依照既定的文学评价机制来定义网络文学。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分析“何谓网络文学”,并指出传统文学以及文学传统在网络文学中的表现,特别肯定其在类型化机制中的整体形象塑造所携带的时代性和精神症候。本文认为,假如以网络写作和非网络写作来划分写作形态,网络文学也要自省其限度,而当下的精英写作需要审视网络文学与读者及大众心理的密切关联。
网络文学 传统文学 文学传统 共空间 网络力
关于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已有很多论述。但总的看来,二者摆在一块似乎总有些拧巴,关系不那么顺溜,不像说起电影文学和文学、戏剧文学和文学的时候总能找到相应的杠杠来比附,并将其逻辑化。到底是什么使这两种均以汉字作为主要书写方式的“文学间”有了问题?甚至某些硬件不容置疑的存在使此问题变得根本化而不可通约?也就是说,这干脆就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两种表达方式?各种疑问越发将我的思路带向寻觅二者的“不同”,“同”似乎很自然地被丢向远方。
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常常将“文学”视作一个有固定本体的范畴,一旦如此,凡出现不符合“文学”规定的表现皆被视为异类,手机小说、微信小说,加之网络小说,开始之初都屈居在这个范围之内。相应地,“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相较于“文学”的规定性而言,却都是在强调其“文学”的底子之外,加上一些大而化之的修饰词罢了,诸如“传统”,诸如“网络”。但显然,“传统”这个修饰词比之“网络”拥有太多的想象空间、意识形态意味和充盈的文化,因此也就不证自明地担负起了“文学”的历史和文化表述职能。我们常见的话语如传统文学、现代文学,基本上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如今又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摆在一处,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区别,直接将其定位于已有的文学形态。换句话说,存在于网络文学与文学之间的问题,被化约成为网络写作与既有文学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因为网络文学呈现出的样态实际上与既有文学(也可说传统文学)没有根本区别,还是在编故事,写人物,依旧是汉字,网络文学也就是文学的一种。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基本上)=网络文学。对这样一个推演过程我表示存疑。一是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文学”本体,对此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德里达、福柯都曾尝试做出回答,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二是如果网络文学不存在什么问题,我们为何不干脆取消“网络”二字,直接将其划归文学大家庭呢?
所有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在于一个梗——网络。这两个简单的字带动起广阔的“异度空间”,它标志着传播方式、媒介以及关于文学场域和文学关系的变迁。我个人主张,在言谈网络文学时,必须要首先并时刻把握其媒介性和空间性,必须限制经意不经意地把网络文学拉回既有文学标准的企图和心理暗示。这种时候,现象学的“悬置”是很好的策略。只有搞清了何为网络文学,才有可能去追踪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当然,这又将涉及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网络文学独独与传统文学关系如此紧密,却很少听到网络文学与现代文学或者其他什么文学有这样的联系?以上两个问题是本文论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时必须面对的关键。
一、何谓网络文学
可是,要搞清网络文学何谓,又岂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关节点在于作为作品,它同样需要有读者,而这个读者又几乎可以确定是经过了上述所谓“传统文学”的给养而就。因此,在言谈网络文学时,一种围绕网络文学的关系图就已经开始呈现,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实际上是建构在新旧媒体的关系之上。单纯强调网络性,或者只强调其文学性都是不够的。除非我们能够列举出网络上的“文学”与已有传统文学迥然不同,比如我们常听的“爽”“撩”等,但这些显然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身体感官表述在通俗文学中早已有之,又怎能以此作为网络性的固有特征?只能说,它有,却不独有。当我们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通俗文学联系起来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很自然而潜在的“去差别”“去陌生化”的惰性倾向,似乎只有将其归为已有领域才安全,依照麦克卢汉的说法,这实际是一种对旧习惯和旧媒介的麻木机制在起作用。但我们越拒绝,结果可能就是以更快的速度向着新媒介的方向发展——网络文学的发展速度之快就是最直观的事实。
在这个迅捷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领域冒了出来——读者,或者更准确的说法——受众。以受众作为中介,我们明显看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不同,后者读者的参与是在后期,也就是作者完成并与读者见面之后,当然,这中间也有作家依循所谓的“大众心理”和“市场”所做的揣测,但确定的是,读者并没有在写作过程之中现身,并改变其创作行程。这个意义上,传统写作可说是作家的独立创作,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文人独自创作,因此,文学的专有性、独尊性和不可重复性是其表征。但“网络文学”就不同。在“网文”发布的过程里,写手与读者是随时随地不可分的一体,没有读者,那这个“文”的命运基本就是消失。读者是跟随着写手的不断“更文”一起存在,如影随形。这样的读者也在不断演变,从普通读者,到粉丝,再到余兴未尽的同人创作、批评,就形成了与传统文人创作非常不同的读者。甚至可以说,“网文”世界的读者已经自成一格,是一个有共同趣味、共同追捧对象的群体或者部落。这个群体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催更”,可以就“文”的某个人设(人物设计)、某个情节、某个坑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影响写手的写作方向,还可以在后期一系列传播链条中发挥作用,如出书、拍电影,郭敬明的粉丝在《小时代》的市场份额上起的作用已不是什么秘密。从这个角度看,读者,或粉丝,是网络文学非常关键的一环。
因为读者的存在,改变了写作的环境。过去的创作是个人创作,因此是具有隐私性质的,有个人空间。但网文的写作方式和阅读机制,决定其写与看基本处于同一个时空之内,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写者就像与读者面对面,屡见不鲜的是,写手会在一开始像写日记一般说说自己最近甚至刚刚干了什么,自己的身体情况怎样,有什么想法,这些属于私人的东西基本以“公开”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写者与看者之间是一种近乎对等的关系,甚至有一种亲近感。从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一个网络写手日更千字、万字这样耗费脑力体力的状态是如何维持下来的。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质疑这种“亲近”背后的“金钱”诱惑。但“金钱”诱惑难道在传统作家那里没有吗?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的市场化走向不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把市场作为一个背景,再来看两种写作方式的差别,其实是清楚的。公共空间的存在,使“网文”处于共同创作的机制之中。而同时“在网”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还是整个意识参与其中。由此,网络这一媒介的功能完全得到凸显。这不仅是电脑介质存在,还要求网络的存在。急速的网络流将写者和看者置于迅捷的、四通八达的电流之中,其流动性、可变性和高速度为网文的“长”“全”“编”提供了可能,而这些也成就了网文的特质。
网文正是在共空间的机制下产生的,即写什么的问题。由于写手与读者基本处于一个仿真的空间,甚至就可以被视作真实空间,在这里可以无话不谈,几乎没有什么禁忌。而“禁忌”却正是传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作者和作品都是独立的,在印刷时代处于“唯我独尊”的位置,因此,只能是作者说什么,我们看什么,由于看者与作者同时处于各自的“私空间”,看与写很难在一个线上,而大多数也是被牵着走。在这种情况下,隐私与禁忌也处于压制的状态。换个方式,假如读者可以借着写者的手实现自己的隐私,或者说出自己想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显然,内容,或者写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文的魅力。读者和写者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从现在的网文看,那些在现实世界不能说出或做的事情生出了无限可能性,这与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如出一辙,只不过,那个“作家”是个体性的,这里的“写手”却有着群体性。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无论是“穿越”,还是“玄幻”“武侠”“耽美”等,都是有十分的社会性和心理走向的。所以,千万别说“网文”瞎编,或者晦暗恶俗,实在是现实有之,以前或许没有说,如今借着二次元的世界洪流在群体的推动之下说出而已。这种力量的“摧枯拉朽”不能小觑。
网文也与共空间有关,即以怎样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故事。请注意,我用的是“说出”,而不是“写出”,因为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共空间决定了“理解”的重要性和“推动”故事的力量。要让写者和听者同在一个结构之中,就得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过去的文学性强的语言显然带有很强的个人特征,那么,网文的同时共在写作还能如此吗?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讨论网络写手的个人差异问题,即不在于雅俗、精英或大众,而是如何使用口语的区别。被称为“文青”的网络作家猫腻总是说自己实际上写的也是小白文,其意义也在此列。“甄嬛体”,或者“红楼体”,也还都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对那个时代的想象性模仿,更多的是将现代口语直接加之于所穿越的对象,而且无往不利,无论写者还是看者,这叫一个“爽”!至于脏字、错字、达成共谋的“新创”,都构成了网文合法化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这些“新创”的“默契”越来越多,网文的“圈子化”“部落化”日趋明显。不了解这些“新创”,你很容易被“新”带来的压力弄得知难而退,于是,“圈子”更稳固地成了“圈子”。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网文的写作来源也借助网络生长的大众文化形式如游戏、动漫、博客、微博等,这些形式之间构成相生相长彼此融合的关系,构成媒介融合之势。
网文依然离不开共空间,即网文的推手,网文运营商或网站,普通读者、粉丝、弹幕、跟帖、不同品级的批评、排行榜等,维持或者促成一个网络作家的诞生,也可能很快就将一个写手拉下马来。这种速度与力量绝不是报纸上的“连载”能够比拟。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网文与报纸连载还是有质的不同。IP的意义,更加重了网文周边的力量。中国网络文学十几年来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蓬勃的发展是基于两个核心动力:“有爱”和“有钱”。“起点模式”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把“有爱”和“有钱”落实进以“粉丝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中,从而建立起一支覆盖全国的、数以百万计的写作大军,汇集起无数以各路“大神”为号召、以各种书评区/贴吧/论坛为基地、以月票/打赏/年度评选等制度为激励的“粉丝部落”。这个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才是网络文学的核心资源。
这个共空间引申而出,即网文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并决定其情感结构。这是我尤其要重点谈论的问题。或许,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使其与旧媒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形式上,网文有自己独有的特征,但是在情感结构上却既是依赖性的,也是革命性的。受到传统文学的熏陶,以及熏陶程度高低,这个自不必言,有不少作家原本就是在大学中文系学习,或者是文学爱好者。更多的写手,却是来自于现实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行业,或者有不同喜好,是不同群体的“迷”。将自己私密的情感体验以公开的形式见之于众,这恐怕也是网络的一大功效,当初的九丹、木子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发布之迅速、关注之浩浩荡荡,成名之迅捷,断不是传统文学作家可以比拟的。可以说,把“八卦”堂而皇之地“说出”,并且事无巨细地“说出”,这些原本属于边缘的、裂隙之处的存在,反而构成了强大的网络力。这一点,进而构成“网文”本身一大特征:对故事的不知疲倦的追求。这种“追求”之下,“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此,若把“长”作为网文一个标识,则必须看到背后的“暴露和追私”诉求。
“网文”的物理存在,也就是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实体是什么?我认为,是多媒介的纠缠。这原本不是个问题,但当很多“大神级”作品被线下出版社以纸质的形式出版之后,就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在纸质文本和以二进制形式编码而成的线上创作的“网文”之间,哪个代表了“网文”?当下常常听到的一种描述是“收编”,就是说这些“网上”写作的“写手”或者实现了终南捷径,这是有意为之;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委曲折向“传统作家”的路子,并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当然,现在谈“体制内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方面,各地“互联网协会”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创作并没有因为“互联网协会”或者“收编”而转向,或者停止。写作依然在进行。至于改变了什么可能才是真问题。回到我们前面说的,到底哪种才能代表网文的“实体”?我想答案还是确定的,自然是“网络的”为本。倘若这个是确定的,那么,纸质版的作品就不是“网文”,最多只能算是“网文”的减缩版。因为大量的写手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写手对情节的交代和设计,即大量的“作者有话要说”;读者对人物投出的“地雷”或者“灌溉营养液”,如“蟹蟹萌萌们的留言和霸王票支持”;不定期在章节之后出现的网评,每天的“更”文,每周的打榜,通过字限的时间,版权问题,诸如此类,这些都是“网上的”有机组成部分。倘没有这些,遑论网文?
传统作家的写作过程是属于自己,这大概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因此,作品写成之后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荣誉,或者能否得到读者喜爱和批评家的关注,是处在不确定的状态,很难由自己掌握。也因此,这种“孤独写作”和“个体世界”成为传统作家为人称道的部分,是作家成为“精英”的主要原因。“网文”写手却一改这种写作模式。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刻,就基本上与读者共在,阅读的数量和“打赏”的多少始终伴随着写手的沉浮,自然成就感也在其中。这一过程伴随着“写作”突破规定字数和规定读者的标准而时时鼓荡于心。换句话说,“网文”写作是在时时被观看的状态下完成,因此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感和表演感,那种“展示”之中的愉悦和激情可以想见,这种“居间的”“看与写共在”带来的体验是传统作家无法感受到的。弗洛伊德把作家的写作与白日梦联系在一起是指借用写作来实现隐在的无意识和欲望,写作是个人在做梦,将这个解释放之网文,却是身在现实世界,却借助网络平台公然与大家一起“造梦”,而且常常是长年累月,每天都有大概固定的时间共同在网上生活。
“网文”写作与写博文是不同的。博文常常会陷入“为他人而写”,很多博址是与其他网址链接的,从而形成一个关注的网络。而且,博客的“名人”和“日记”性很突出,后来就有些“发布明星公告”的味道,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这个倾向。其“门槛”相对而言是“高”的。但“网文”的写作,却并不受水平高低、身份高低或者是否名人的限制,一个“化名”便解决了这些问题。在最初的写作中,最关键的是“故事”编得如何?是否吸引人?是否有长制作的构想?烂尾之作何其多!这些都是对“写手”的考验。相比之下,“网文”的公布并不难,也就是与读者见面是在最初时刻发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而传统写作者,要想让作品公之于众,却必然要倚赖传统媒介——报纸、刊物或者出版。两种媒介的区别也就出来了,网络显然更大众化,在权力的设置上也更直接而简单。当然,随着国家净网力度的加大,网络运营商管控能力的增强,经济因素暴涨式的凸显,“自己”的力量能否保存或者朝什么方向发展,恐怕就是正在发生之中的变数。
二、当历史或传统弥散在网络文学空间
以上网络文学特征种种,莫不与传统文学或者既有文学传统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却也在媒介、写作方式、与现实的关系等诸方面与传统文学构成尖锐的冲突。且不论传统意义上的作家群对网文不算少数的嗤之以鼻,即便是在网文的发展之路上,大概在前十年,不少以网文起家的写手也常在“有名”之后与之渐行渐远,甚至回避网络作家这样的称呼。我以为,这并不表明“网文”的规定性在进行自我拆解,而就在与传统文学秩序拉拉扯扯的过程中,“网文”世界渐渐形成,各种类型文、同人写作以及众筹等形式的存在,表明网文已经有了自己的阵地。
一个明显的征象是网文中充满了各种“传统”的影子,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宗教的、神话的、民俗的,比比皆是,甚至因此形构出不同的类型文,而“传统”本身所负载的意义的双重性也体现无遗。如“传统的”一词所涵盖的“过时”“迷信”“民间”等意义在仙侠类、盗墓类、修仙类、玄幻类等“文”中得以焕发生机,并成为代表网文的标志性文本。另一堪称典范的文本是穿越文,无论是作为“清穿”标志的《梦回大清》,还是掀起收视高峰的《步步惊心》,其所对应的是所谓“架空”背后的历史想象,今日观众的“清史”知识多为此类文的喂养而成。要说这些文本是瞎编也好,乱写也罢,在某些具体的部分如宫廷规矩、器物、礼仪、言谈方式甚至具体的生活都力求“种田”式的精确。这样做显然是写者和看者的“合谋”,在“如何真”上着实下了功夫。在《临高启明》这部类似“跑团”文的见面会上,作者吹牛者就说到吸引“粉儿”关注的兵器知识是来自类似“兵器大全”或“兵器制造”的书。同样地,在各种文中我们见到大量的细致的对一些经典的引用,如佛经、《山海经》《道德经》《周易》等,不但粉饰了文的“古气”,有时就成为勾勒全篇的底本,修仙文多如此。这并不一定说明写手对这些文化传统有多么精深的研究,大幅的引用基本可以证明这一点,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网文得以立命的一个重要根基就是依托、借用了各种可资考证的史料或者野史。到现在为止,清朝的各个皇帝差不多已经被写遍了,而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民国军阀混战,也都在“穿越”或者“历史”的视野中编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至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诛仙》《斗破苍穹》一类的玄幻修仙文是否代表了道家文化的当下复兴,还是来自网络游戏如《仙剑奇侠传》的滋养,此游戏本身又经历了从台湾到日本再至大陆的旅游线路,这种难辨出身的复杂性恰恰讲述着网文发生发展的环境与多媒体的融合之密。这也提醒我们在习惯性地讨论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时,不能忘记其生成的多种可能。《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曾分析2003年最早连载于幻剑书盟网站上的一部网络古典仙侠小说《诛仙》,说:“萧鼎稳稳地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坚定地承袭着中国古典志怪、神魔小说的衣钵,将玄怪奇幻与江湖风云很好地捏合在了一起”,这是看到了该作与传统文化的谱系,但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的关联恐怕还需再细细理清。
对文学经典的改编、改写或者解构是传统文学直接进入网文的明显表征。这在初期的网文写作中尤其突出。2000年开始在论坛上出现的今何在之《悟空传》,现已拍成电影与观众见面,只是大伙的反映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当年受到网文版冲击的读者粉儿更是反应强烈,都认为电影失去了当年的锋芒和指斥天地的豪气,仅仅剩下了豪华景观和形象展示。两种媒介,一个文本,一个编剧,却出现不同的表现和观者体验,媒介的不同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说话的时空环境早已世易时移,今夕不同于往日。《悟空传》出炉的时间,恰恰是网文刚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的时间,这刚刚“触网”的写手并非新手一个,他力图从传统文学秩序之外找到“自由”发生的空间,网络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李寻欢、邢育森、安妮宝贝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再来看这初期的网络作品,很难将其划归几年之后形成的“类型文”系列,其症结便在于传统文学或者文学经典的滋养,而不是“读者粉儿”和市场的合谋。《悟空传》显然与文学经典《西游记》连成一条鲜明的谱系,但在精神气质上与电影《大话西游》系列更亲近,突出了孙悟空、唐僧的个体性和反叛气质,同时充满世纪末的语言狂欢。这是暗合那一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朱文等人的“断裂问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卫慧的《上海宝贝》,九丹的《乌鸦》、绵绵的《糖》,以及安妮宝贝文本中充满都市文青小资气质的薇薇安,都在把“个人”+“自由”推向前台。这些作品既承接了后现代的解构热潮,同时暗合大众文化的日常审美需求,在文学与大众、大众与个体之间进行了链接。倘若我们想要否定这些网文与文学传统的联系,显然是不能够也不实事求是的。但我们又必须看到,随着网络文学网站逐渐成熟、写文机制逐渐健全,写手与网站的关系逐渐稳定成一种工作关系和生活来源,读者粉儿的队伍逐渐庞大到可以决定一个“文”的生死,文学传统在网文世界的存在不再像初期那样直接拿文学经典下手(当时有大量的“红楼”系列、“西游”系列),而选择将文学传统与故事连接起来,或是人物的文化素养,或以之为文本发生发展的线索,或与某一经典形成对话、致敬格局,或将某些母题或文类辅以大量的故事发展成网文系统。可以举例来说明。如穿越文中的男女主,有的在穿越之前并没有什么古文根底,却借助超现实的记忆力在穿越后的世界大秀特秀唐诗宋词,《绾青丝》《女帝本色》《醉玲珑》皆在此列,这差不多是穿越者在异世界的必杀技。如修仙历史文,常将某一经典摆在重要位置,作为修炼升级的境界之镜,这方面《周易》和《道德经》是用之最广的,像《将夜》《朱雀记》。而《雪中悍刀行》不仅如此,还将《红楼梦》坐落到其中一个女子王初冬身上。猫腻的《庆余年》则直接将《红楼梦》的记忆变成促进故事发展的线索。说到文学传统成为叙事线索,Priest的《默读》直接将《红与黑》《洛丽塔》《基督山伯爵》等变成案情的关键,可谓做到了极致。还有一些写手专门从已有的演义传奇下手,演绎出绵延数年的故事,《新宋》《隋乱》是此类中的佼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传统委实反哺了网文并使其具有了生发的广度。
而要说到文学母题在网文中的发展,言情和武侠可能是最突出的。这两种文类与世俗和大众生活的密切以及在中国受众中的影响力由来已久,能够在网文世界有深刻的根基与此有关。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尽管网文主要以类型存在,但言情和武侠基本上是以兼类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在修仙类文中,杂有言情和功夫几乎是自然而然,在穿越文中,男女主也差不多都是文武双全,而爱情则是屡试不爽的良钥。在前面说到的《新宋》《隋乱》这样的长篇历史文中,江湖草莽与秩序中之将帅若不是因了“侠义”和“武功”,魅力不仅会大打折扣也会拖住其延宕的脚步。可以说,言情和武侠在各种类型的网文中遍布,类似《斗罗大陆》《斗破苍穹》这样的打怪升级文,也少不了他们的滋养。在这些文中,有庙堂,有江湖,有战争,有边塞,有蛮族与识书知礼的世俗眼光,同时有对大漠的向往,种种空间杂在一处,使得故事光怪陆离,同时又因有惯常的体验而充满期待。追根溯源,关于民族与边疆的书写,似乎离不开汉唐时期的边塞诗,尤其是有唐一代的边塞诗体现了康健有力征服四方的魄力,而有意思的是,这些边塞诗多是以中原的征服者对蛮夷的征服为观看主体,所以才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这也常被教科书称为“英雄气概”。这些诗中的匈奴、或者突厥、吐蕃等异族的形象多数模糊乃至不可见,但有了“醉卧沙场”的气魄和“为国杀敌”的立场,被征服的一方自然被放在了相反的方向。后来的武侠小说尤其是香港武侠延续了这样的脉络,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敌人”逐渐有了不同的映射,总之是对国家有侵略之心的外来之敌,也因此,金庸、梁羽生、萧逸等的武侠小说以其豪气、爱国、侠肝义胆赢得了大众的喜爱。但网文中所谓的礼仪之邦和蛮族间的关系却精彩纷呈,不是上述那样单一的面貌。且不说《九州缥缈录》中来自蛮族的吕归尘如何帮助中州兄弟成就大业,《挽天河》直接设计了所谓发达文明之地的中原王朝在一片颓败之中败给异族朝廷的结局。这种变化在以往的武侠小说中鲜有,却展示出当下受众对生活、文化乃至政治的认知是不拘一格的。
三、网文的限度和启发
若说网文与传统文学或者文学传统无关,那是自说自话,上面提到的诸种表现都说明二者关系之密切。但若避开或者无视网文已经形成的独有的创作方式和文化场域,那也只是盲人摸象,甚至掩耳盗铃。
除却网文在形式上、类型上和媒介所生发的质的规定性,网文在文化诉求和文化心理的表现上也显示出集中的力量。这是由多文本和长文本的特征推出来的文化现实,不容忽视。其中一个突出的领域是关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几乎在所有的文本中都有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即便是由一帮男性编织的《琅琊榜》,也无损夏冬和霓凰郡主的荣光,而所谓“纯爱”文中的男男二主,实际上也有一个寄居在男性躯壳上的女性灵魂在熠熠闪光。还以武侠为例,我们可以见到女性被赋予了何种气质和力量。这是一种名曰“刚健”的气质,在历史文或者职场文、后宫文中都能找到印记,大凡男女主角都是“有生气”“有活力”“有胆识”“敢爱敢恨”之人,看看若曦(《步步惊心》)、窦昭(《九重紫》)、青丘白浅(《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芈月(《芈月传》)、北瑶光(《蛇君如墨》),就知此话不虚。这种特性在以往文学中的女性身上并不是太明显,琼瑶的女性已经是独立思想的标兵,但在“爱”的名义下多被取消了社会性,至于阶级差别、贫富差异等都被见识和个性抹平。在“网文”中则直接换掉以往的世界,建构一个“我主沉浮”的新世界,女性也随之获得了璀璨的光芒。天下归元笔下的人物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或是当了皇帝,或是给皇帝都不做,但无论如何都是纵横四海的人物。尽管多数作品最后的落脚点依然是岁月静好,但类似《凤囚凰》这样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也不乏多见,关键在于,女子成了网文中闪光的形象群。这无疑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征象和折射,对我们认识当下的女性心理和女性位置都是一种启发。
这些女子光辉的形象又悖论性地与另一个现象扭结在一起,很值得玩味,即似乎写手和读者对“人类”和“起源”都很关注,大量作品将视线投向远古,仙侠妖兽纵横,但不管如何古怪,却总是有个权力中心。修仙、玄幻、穿越、升级打怪,大约都可摸到这一脉络,这很有点补偿心理的意思,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体现了底层草根对社会体制最高层的想象,并且倚靠大量的宫廷礼仪、器物、服饰的描写尽量“使其似真”,但又时常会加入当下的感受,这就很有点后现代主义的味道。往过去说,是“皇权”。那么,现在呢,写当下的作品呢?其实也大略如是,只不过在今天的社会里,取代皇权占据更重要位置的是:谁给自己发钱?因此,公司,写的就是霸道总裁,写老板,写上司,如风靡一时的《杜拉拉升职记》,这些时间发生的环境——公司——也类似一个宫廷机构,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若是国家发钱,那就写的是具象化的单位,像揭秘类大抵属于此类,如《第二首长》。
这就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极权”位置缘何如此受重视?为什么总是在一个支配者/被支配者的结构之中展开故事?写法上也很有意思。像《琅琊榜》,看似来势汹汹但实际上只是底层(其实还不算是底层,应该是政府高层,但相对于塔顶为低)想要有个更开明的领导,于是乎自己将被选之人供上王位。这一过程其实是有协商意味的,断断说不上是革命。《甄嬛传》就又不同。皇权的象征性是在女人一步步走向“狠绝”的过程中慢慢堕入尘埃,但这显然是个人行为,“四郎”的死,并没有挡住“权力”在甄嬛手中的扩大化,所以,这就像是接力游戏:一个退出,另一个马上接手;一个皇帝死了,还有另一个皇帝。只不过,这个“新帝”却是在“女人”的支配之下享有权力。这就又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女人在这些“极致想象”中的位置。《甄嬛传》的作者是流潋紫,《女帝本色》的作者是天下归元,在这些作品中,女人都获得了象征性的最高位置,但反讽的是,这些女人莫不是在“情感”的名义之下为男人守护“江山”。到底是“谁”的江山,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意义的归属并不仅仅在于最终如何,在漫长的篇幅之中,中间的过程:女人如何张扬、女人如何让男人俯首称臣、女人之魅力如何风华绝代,这些也是写作的重点。只是,“情感”的软化剂和依赖性在这个过程中如影随形。我很难说这是一种政治趣味或者皇权中心的内设,但大量的文本似乎也说明网文的限度和犬儒心态。
反过来看,网文的类型化走势在集束力量和反映现实文化心态上对传统文学也已构成强劲冲击,它对准读者心理,尽情倾泻情感、欲望、对现实的看法和对理想人生的想象。你可以笑其浅显,笑其玛丽苏,但你不能无视这些人物身上的力量和吸引力;你也可以笑其浅薄的岁月静好,笑它只会投其所好,却不能否定这些情感的温暖和并不算奢侈的希冀。最起码,网文抓住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也抓住了正在不断分化的市场,而同样需要读者的“传统文学”,正视这个曾经被视为“垃圾”如今已成对手的存在,去研究现实和读者,显然并非多余。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为何这么多的“傻白甜”被“粉儿”心甘情愿地接受?也许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不如网络文学与大众心理来得更准确。
张春梅:新疆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