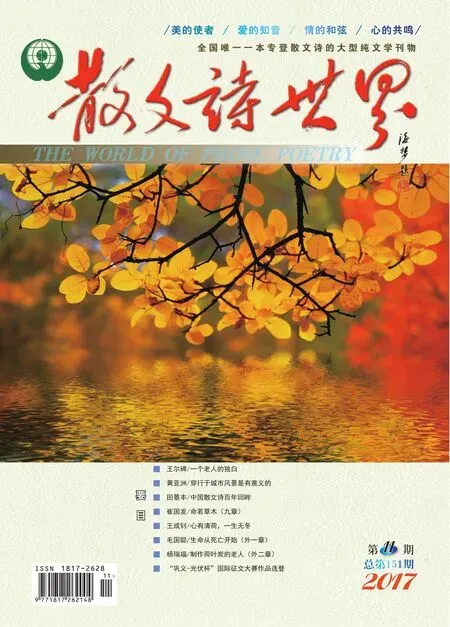制作荷叶炭的老人(外二章)
上海 杨瑞福
制作荷叶炭的老人(外二章)
上海 杨瑞福
1
一部记录中药材制作的电视片《本草中华》,无意间挽留了老人瘦削的身影。
相信这一辈子,我们都无缘在荧屏之下相遇。让我抬头看清您清癯的脸就够了。
您从朱自清才踏过的荷塘边来,从《诗经》里游进阳光的鱼儿身边来,从杨万里手中放飞的红蜻蜓翅边款款而来。
不为摘花,那是爱嬉闹的少女才做的事。只为剪叶,把夏天怀抱的一池碧绿,化作长长久久的相思。
在才燃点起的火炉上,一个铁锅,小心翼翼放入一层又一层的荷叶。它们肯定哭泣过,老人心知任何的骨肉分离,都会忍不住悲哀和动容。
四张雪白的纸,安放在缓缓升温的铁锅旁,逐渐变黄。
老人知道,一念之间的成败,已到需要揭盖的时刻。
火候将决定这些荷叶的命运,或成为炭,再磨成粉末之后,加入一剂良药的行列:或成为灰,在抛弃的废物堆中怨叹宿命。
2
老人把荷叶终于烤成了炭。
他揭开盖的刹那,是喜悦,还是遗憾?表情或许会被不住滴下的汗水冲刷,只有坚毅能够暂时停留脸上。
炉子里的火光,希望能把所有被风吹凉的心焙热。
荷叶不再是我们熟悉的绿色,那只能证明春花秋月已流逝,它们无需介意过去的活法。
如果借助炉火的高温,从而获得更久远的存在,但在赞美和诽谤之前不发一言,您同意这样被迫的选择吗?
叶面上的脉络如此地清晰,如同老人手上凸起的青筋,是不得不衰老,又不愿向岁月屈服的标记。
有人说,这是骨肉之躯必须经历的火化,躯壳里暂时寄放的灵魂,是否都需要这样一种舍命的煅烧,才能够追求不愿轻易腐朽的永恒?
荷叶一身的黑色,似乎在表白,夜总与光明绝缘,又好像正恳求涅槃之后的浴火重生。
土尔扈特人的家园
1
在决心东归的日子里,里海平静的湖水突地卷起了怒涛。伏尔加河的下游,安静放牧牛羊的土尔扈特人,在俄国失去了往日的安宁。
从此做一个顺民吧,低着头,安心度过匍匐在皮鞭之下的日子,而不必因为昂起头,就必须时刻抚摸身上的条条血痕。
屈辱也会成为震撼天地的力量。乌拉尔河前的峡谷,注定是埋葬一切胆怯者的坟茔。
木制的精美宫殿,被自己亲手点燃的一把火烧尽。
于是,往日并肩作战的哥萨克骑兵,成为返乡之路上道道难以逾越的埋伏。
圆月弯刀,并非砍向侵犯国境的敌人,而是决战于辨别生死之门的不归之途。
所以,一个民族的骨气,必须以染一身的鲜血为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否过于昂贵?
当十七万人的队伍,在曾经逗留和生活的土地上,最终留下了十万具遗骨,供亲人们在梦中焚香祭祀。
2
二百年后,历史昔日的伤口已经结痂。
当年殊死到达伊犁河的祖先,他们俯首亲吻的土地,已长满了茂密的酥油草,不顾一切啃吃的牛羊,更懂得在饱食后仰头歌唱感恩。
作为土尔扈特人的后代,他们牢记着:“草原之大,没有存放私心的地方”。
作为土尔扈特人的传承,他们必须把浴血的精神,编写成永久传唱的史诗。让身边的每一匹马,都反复聆听马头琴模拟的悲壮喊声、鼓声和风声。
即使在秋季转场的时节,在拆下蒙古包重新出发的间隙,都不忘记提醒勒勒车:“又要远行了,向着东方,向着信仰,向着天鹅的鸣声,向着奔涌河流的源头”。
水草丰美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才是勇士一生的最终归宿吗?
请到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门前的两块巨大的石碑上,去勘查四种文字铭刻的真相……
3
一个原本骁勇的民族,是怎样在岁月的风霜锈蚀之中,失去了以往的锐利?
躲藏在皮鞘里的箭,已经迷失了发射的目标。
悲哀和悲壮仅是一个字的差别,却相隔天和地的距离。
不希望仇恨如奶牛的乳汁一样丰盈,但应该记住,草原上苍鹰盘旋的雄姿。
我们不能阻止羽毛的飘落,但愿它在新的土地上发芽情歌。
身前流过的每一条河,从此张嘴便唱出悠扬的长调;轮子碾过的每一条路,都是父亲胸脯上永不折断的肋骨。
南浔的旧日风光
张石铭旧居
在妩媚的江南,随意找一个小镇寄放乡愁,并不难。
隋代开掘的京杭大运河,缓缓流过南浔的身边,似乎这里注定要传承千年以来的传统,复制出唐宋明清一代代的文化底蕴。
张石铭说了一声:不!
活在众人的眼中,你应该算一位难得的儒商和收藏家了。太多的木雕、砖雕、石雕和从法国进口的玻璃雕,必须以恢弘的楼宇来容纳吗?
这么容易在摇摇欲坠的清末,感觉到世事即将的巨变。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无法指点江山,还不如退守家园,把中西文化的结晶和精华,尽情收罗到手边把玩。
因此,你生前所建的244间楼房,用来供家眷居住太过奢华,用来储存普天下之宝物,兴许局促。
是功,是德,姑且待死后任人评说,你听不见。
嘉业藏书楼
江南外在的风貌也需要风雅内涵的衬托,比别家的藏书楼幸运,多了一块清朝末代皇帝亲笔所题的九龙金匾,匾上的题字“钦若嘉业”,堂而皇之赠送了南浔藏书楼,一个无比显赫的名字。
和别的水乡并排在一起选秀,它们不选河,不选园,也不选如雀鸟掠过的的众多名人,有嘉业藏书楼在,南浔便独多一份书卷之气,足以傲视天下。
在民间蜂拥而建的藏书楼中,它修得最晚,但可以炫耀自己,曾经60万卷、18万册的最多藏书,其中包含的秘籍和珍本,是如何看花了世人的眼。
宋代和元代的刻本,如今静静躺卧在手无法触及的玻璃柜里。仿佛它们的一生,注定要隔绝人们在使用之后的赏析。
因此,这些感觉冷冰冰的玻璃柜,越发像极了玻璃棺,棺里所藏的“镇馆之宝”,在白天游人参观时绝不出声,在无人的夜间走动幽灵。
杨瑞福,男,1946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宁波。上海市作协会员,正高级高工。在四川三线工厂从事发电设备的技术工作三十八年,汶川大地震后回归上海故里。1979年开始写诗和散文诗,有诗和散文诗发表在多种诗歌报刊上。主要代表作有诗集《把阳光贴在窗棂》;获得过上海和国内多次诗歌比赛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