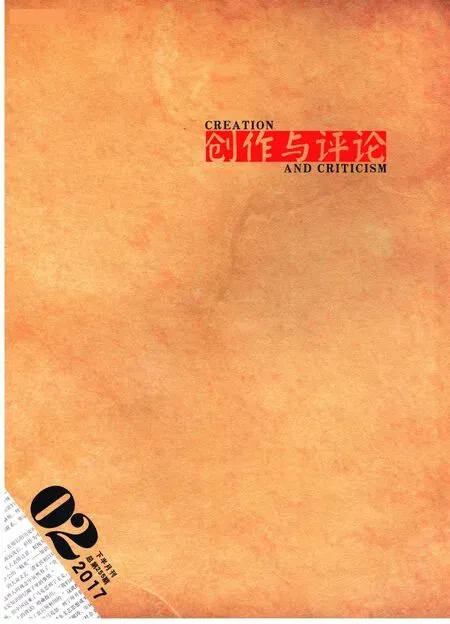青春的梦呓 诡谲的灵慧
——评戴潍娜的文学创作
○ 房 伟
青春的梦呓 诡谲的灵慧——评戴潍娜的文学创作
○ 房 伟
戴潍娜是一个“精灵古怪”的女诗人,也是一个充满想像力和冲击力的女作家。阅读她的诗歌和小说非常令人愉悦。潍娜的写作似乎带有80后一代人共有的鲜明印记:华丽的文笔、不羁的奇想、灵慧而又不着现实的文风。但与此同时,我更看重的是她独有的女性书写风格。在青春的苦闷与真诚之间,在世界的多维体验之间,戴潍娜笔锋大胆越轨,却干净透亮,想象奇特却诚恳坦荡。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而且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许都会被她水晶舞蹈般的叙事风格所吸引。应该说,戴潍娜以独特的感知力与创造力营造出了独特的写作空间,在她的作品当中,青春的梦呓与诡谲的灵慧并存,独特的女性化书写为读者开辟了崭新的阅读空间。
一、有关梦境的营造:神秘体验的独特表达
如果要说戴潍娜的写作有哪些特点的话,如真似幻的梦之世界的营造应当首列其中。“梦”是戴潍娜作品当中一个非常鲜明的主体意象,在她的作品当中,梦境、梦呓、梦幻、梦想共同构建了一个似童话而又非童话,似神话却又绝非神话的独特世界在这个超越现实的独特世界里,作者表达出了自我对历史、真实情感以及理念的个性化思考,形而上的哲学化思索使得作家的作品在难懂的同时得到了一定的深度。
戴潍娜笔下的梦是干净、轻灵而又不失深度的。在她的小说《天年小镇》当中,一个像桃花源一般游离于尘世之外的海滨小镇成为了故事开展的所在地,这个古怪而又天真的小镇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镇上的人们均知晓自己的天年,也就是自己的大限之日,年轻的音乐家汉舍与植物学家方糖兄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这个单纯而又美好的世外桃源,在镇上,他们结识了美丽的姑娘白雨点并与之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三个人的世界里充满了忧伤与快乐,却又是无比美好的。无奈,渊博的音乐家与植物学家却不知道在小姑娘那双如卵一般的能受孕的圆眼睛后面隐藏着深深的忧愁:白雨点的曾祖母大限将至,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善良而又耽于幻想的白雨点希望通过减少自己的天年来给亲人续命,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触犯了小镇由来已久的天律,最终导致祖孙二人共同离开了此生,走向了来世。而痴情的汉舍与方糖兄在变故之中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圈套”,并将希冀给予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可以说戴潍娜的小说并不以故事性见长,包括《天年小镇》在内的一系列童话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只是重组变形后的再表达,但是作者作品当中那种独特的体验及体验背后的深刻性是一般童话作品中不易见到的,一部《天年小镇》,无疑是一部人类生存境遇的微型“启示录”,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中蕴含着的是人类对超绝现实、打破“确定性”以争取属于自己的未来的渴求与希冀。与《天年小镇》相类似,小说集《仙草姑娘》中的其他篇章也都饱含着作者对世界与人生哲理化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不是显在的,而是潜在的,是带有神秘色彩与作者个人化体悟的,因此可以这么说,戴潍娜的小说是柔软的,这种柔软带有神秘色彩,而在神秘的背后,却又有着坚硬而又不易破碎的内核,这种内核之中包含着人类的希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含杂质的纯真的希望,才使得戴潍娜的童话写作不流于幼稚与肤浅,深入到人性的内里来表现自己的独特内心体验。
又如《那个名叫S的灵魂》当中“我”在那个夏天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真实的梦境还是虚幻的真实?文中的那份回忆带给“我”的是深刻的人生体验,但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真实的迷茫。正如文中所言:“我记得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每回忆起一次,我的生命便重新启程,好像午后一个最美的还魂觉,醒过来时一看,才不过一刻钟的光景,可梦中却已过全了整个人生……”与《天年小镇》相较,同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绝美世界,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湘桂走廊南端封闭的小村落,为情所伤而对生活失去信念的“我”为寻找意义而有意避开城市的喧嚣,踏上了追寻灵魂的旅途。在这个纤尘不染的美丽村落里,“我”认识了老彭、姑妈、婆婆、小肥皂、道长等一系列人物,他们让“我”领略到了与俗世不同的风光,而直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形象都有着一双同样的眼睛,是同一个灵魂——一个名叫S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安抚“我”,让“我”重新获得爱的能力,而事实上,他做到了。其实,S是否存在,S是谁在文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亦真亦幻的灵魂让“我”重新获得了接纳世界的能力,这就足够了。作者戴潍娜对神秘体验的书写在这篇小说中达到了顶峰,梦境有如深邃的眼睛,在陌生中透着澄澈,不可知的灵魂神秘而又不失灵性。
有关梦的书写不仅仅表现在戴潍娜的小说当中,也体现在她的诗作里。她的诗作是隐秘而又敏感的内心体验与充满着神性的迷狂交织在一起的华美乐章,梦的迷朦轻灵与亦真亦幻给她的诗作插上了一双柔软的翅膀,而不可透视的神秘性与驳杂的语词又给她的诗作披上了一件不易解读的个性外衣。在《幕间戏剧》一诗当中,戴潍娜通过对一场戏的思考,表达了自己如梦似幻的感受:“家庭安宁有如墓床里的暴动/是爱人?是知己?少女从裙裾里给他掏出十个情敌/提香清洗过后现出墨索里尼/她立志五十岁后学习抽烟、酗酒、海睡晚起/祝我们都过上不健康的人生!生日宴会上她举杯/酒精渍进身体,有如底片被冲洗”。这种梦幻般的感受源于现实却又不着现实,独特的感知使得诗作所表达的感情近乎迷狂。与之相较,《眼》在对神秘性的书写上更胜一筹:“不睡/是/一只贝壳扣在她眼下/颗颗夜晚明珠般不肯黯淡/猫头鹰瞳中她脚趾甲盖是月光石/喙般的鞋跟一盏盏踩灭灯笼”。幽暗的夜、亮闪闪的眼睛、神秘的女人、不睡的猫头鹰……仿佛将人们带回了中世纪的古堡,在合不上的眼睛里,瞳中之人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魔法的世界。
二、灵慧的诉说:个人化情感的别样阐释
戴潍娜的作品是充满了灵气与智慧的,这种灵与慧既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上,也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青春的荷尔蒙在作家的笔下喷薄,诗性的情感同样在其中缓缓流淌。戴潍娜的小说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与动人的细腻,她在写作中也追求着生活中诗意的节拍,《守节的光阴》就是一篇能给读者带来感动的小说。在这篇小说当中,戴潍娜从男性的视角切入来进行写作,讲述了男主人公邱耀武与高干子女张小芹充满了血泪的悲剧性的恋爱史。年轻的男主人公与张小芹自小便对对方心存好感,成人之后的他们在爱神的引导之下最终双双坠入爱河,恋爱中的男女是疯狂的,一场夏雨过后,“我”第一次见识到了小芹绝美的胴体,并用相机永远地将其定格在了那个美好的早晨,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张照片,毁掉了那个活泼而又善良的姑娘的一生,那卷胶片上的美并不是人人都能欣赏的了的,当这份隐秘的图像被世人发现以后,社会的压力最终导致了男女主人公天各一方,并最终使女主人公小芹度过了悲惨的一生。透过这篇小说,我们能够看到作家对诗意生活的追求及对美好心灵的赞颂,在她的笔下,少男少女们敢于冲破束缚,让自己的感情尽情地释放,这何尝又不是作者戴潍娜的人生追求?因为有着对生活的无尽热情作依托,优美的文笔才不显得生硬与做作,这也正是作家的成功之处。当然,作家的写作也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处理《守节的光阴》这篇小说的时候,作家为达到一定的悲剧效果,在文本当中添加了过多悲剧要素,导致作品当中的某些情节戏剧化过于明显。
戴潍娜的灵与慧更多地表现在她的诗歌创作上,她的诗歌创作语言是隐晦而又充满魅力的,她所选用的语词是华丽的,她所营造的诗美空间是广阔而又精致的。在组诗《历史的棋局》当中,戴潍娜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这一组诗中,有着作者对史诗与想象的思考(《史诗与想象》),有着作者对现代性的体悟(《现代唐传奇》),有着作者对真实自由的追寻(《广场上的鱼鸟》),也有着作者对历史终极的探索(《没完没了的棋局》),不管是对哪一个向度的书写,均能够显现出戴潍娜作为一名女诗人所独具的慧根且看《现代唐传奇》这首诗:“山峰之巅,两个唐人/头戴巾冠,身着青衫可入黄梅戏的模样/古国简约地活在一首诗里,唐人不信它法的永生/活着就是一次次死去……男唐人解下一块腰上的残布,给女唐人胡乱一裹,他们就和现代人一般无二行走在柏油道路上。有关现代性的书写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已不罕见,古今对比的方式在王小波的“怀疑三部曲”当中有着很好的运用。在戴潍娜的笔下,通常意义上的“唐传奇再一次被解构了,取而代之的是诗人所构建的“现代唐传奇”。在诗人的笔下想象中的盛唐气象是活在诗中的古国远古、盛唐与当下似乎只隔着一层一戳就破的窗户纸,现代与古代的区别似乎也只不过是腰间的一块残布而已,这种略带俏皮的书写方式无疑非常好地展现出了诗人的才华,而“活着,就是一次次死去”这一沉重的命题又给稍显轻浮的文本平添了几分沉重,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与《历史的棋局》相比,《面盾》的语词更加晦涩,意象更加繁复,而语言也更加华丽。“诡谲”是对《面盾》诗风的最好概括,在这首诗作当中,作者用艰涩的语词和奇诡的意象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构建了障壁。《面盾》的“诡”是显而易见的:“透过昆虫的翅,她看见盾脸上繁缛的花茎/像一片湖水,倒影出心头的缠蛇/那比日日夜夜更为漫长的鞭/雷电把你的柔情送进她耳骨深处/在那里,死后,骨头和骨头亲热/如同在无星的海面宅邸/尖刀般的浪涛上她与暗夜互赠诗篇”。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仿佛能够听到隐藏在自然之中的无数精灵在窃窃私语,痛苦与快乐在阴暗中不停纠葛;而“被分割的云团”“蒙面人的脚印”“盾脸上繁缛的花茎”……等一系列的神秘意象似乎表明作者在有意识地构建一个异于常识的感官世界,这在给读者带来阅读冲击的同时也增加了诗歌解读的难度。在诗作当中,一副无形的面具成为了隔断心灵感应的厚厚盾甲,面盾的背后是我们所无法参透的终极奥义。
三、另类感悟:女性观照下的“夜”书写
毫无疑问,戴潍娜是一名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作家,在她的作品当中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不过,不同于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戴潍娜极少用“性”以及那些极具对抗性的话语来拓展自己的写作空间,相反,她通过对个人无意识层面的细致描摹,用自己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成就了独抒性灵的“夜”书写。对未知的恐惧是戴潍娜“夜”书写一个很重要的层面。相对于代表着阳刚的男性,女性天生对于外界有着更加细腻与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小说《那个名叫S的灵魂》当中,来到陌生世界的女主人公不断寻找生活的出口并在偏远的小村落中获得了灵性的自由,对“大叔”具有依赖性的她最终在灵魂S的引导下释放了自己饱受压抑的情感。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故事其实正代表了以女主人公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觉醒,由依赖男性到走向自立,这是女主人公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而之所以称作家的写作是“夜”书写,主要是因为小说的整个基调是阴性的,作品当中的女主人公并非通过果断而直接的方式向男性群体“开炮”,而是通过近似于逃避的温和方式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与自由,这种宁静与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那个带有着一定男性特征的灵魂“S”所给予的,这就极其鲜明地体现出作家写作在本质上的矛盾性——既具有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特征,却又因“阴柔”的天性摆脱不了灵魂上的“小鸟依人”,也可以说作家的写作在根本上未能摆脱由所谓的性别缺陷所带来的限制——无法完成对外在恐惧的突破。而在诗作《帐子外面黑下来》里,作家书写当中的“暗夜”体验则更加明显:你呢喃的长发走私你新发明的性别/把我的肤浅一一贡献给你……这些悲伤清晨早起歌唱的鸟儿都死了/永夜灌溉进我们共同的肉身……你的痛苦已被我占有/帐外的麻将声即将把小岛淹没/我渴望牺牲的热血已快要没过头顶。这首诗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压抑与幽怨,而在诗作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中的负面感情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女性对黑暗的恐惧造成了心理体验上的变态与扭曲;另一方面是带有阳性气质的主体形象的缺失使得作品包藏着颇具闺阁气的幽怨。这些情感构成了作家创作基调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夜”书写的困境:通过温和的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突破男性主体所构建的话语霸权。
对女性所受的不公待遇的批判与对理想性别关系的渴望同样体现在作家的“夜”书写当中。在诗作《被盗走的妈妈》中,作者借“妈妈”表现出了广大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我不需要任何财产、条约或武器,只要存在/就可以活活把你逼进灶房、杂役和倒满洁厕灵的洗衣机……当才华、抱负、远大前程这些事儿终于与你没关了/你得到一个名字——叫女人”。诗作当中的美丽女性在风华正茂之时有象群般的男人为之倾倒,而当年华老去之后,她便由公主变成了女人,更加可悲的是,无数的女性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心酸的历程。诗人在这里并没有止于抱怨与发牢骚,而是从更深远的角度上思考了女性不公正命运的源头,虽然阴性的书写特征决定了诗人未能高声呐喊,但“当才华、抱负、远大前程这些事儿终于与你没关了/你得到一个名字——叫女人”这样的诗句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性别上的不公正给女性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巨大摧残,简单的倾诉也有了巨大的语言张力。
小说《守节的光阴》与《天年小镇》则更多地歌颂了女性的美好并表达了对构建和谐性别关系的渴望。不管是《守节的光阴》当中的张小芹还是《天年小镇》当中的白雨点,都是活泼善良、纯洁美丽的美好女子,她们不仅有着出众的外表,也有着坚定地内心,是“自为”的女性形象。不管是小芹的独当一面,以一己之力承担整个社会的非议,还是白雨点甘愿折损自己的天年以换取亲人的长生都表现了作家对柔弱却又坚强的伟大女性形象的歌颂,性别上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被这种书写方式所遮盖了。而两篇小说当中男女主人公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的理想状态更是作家内心浪漫情结的诗性表达因此,也可以这么说,理想与浪漫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作家的“夜”书写,作家的“夜”书写本质上是自主性与妥协性中和的产物,这也使得作家的写作得以在一个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而没有堕入过于偏激或顾影自怜的写作陷阱。
戴潍娜是一位颇具才情的80后女作家,她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她的写作是青春与梦幻、诡谲与灵慧的结合体,独特的女性心理体验与哲学化的思考,为她的作品涂上了一抹不易解读的神秘。我相信,人生体悟的加深与写作风格的成熟,将会使得她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