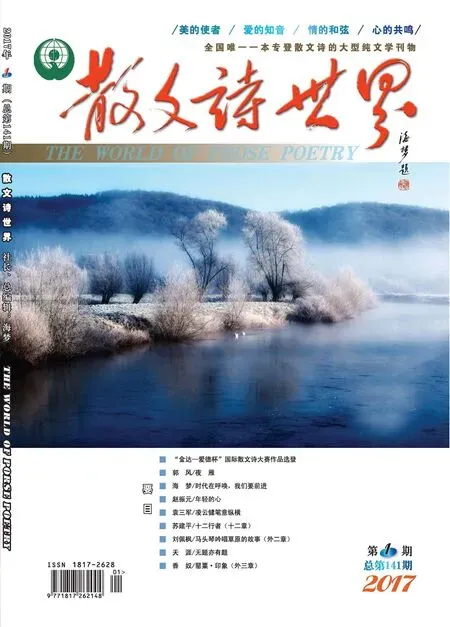零散的思绪(六章)
贵州 卯旭峰
零散的思绪(六章)
贵州 卯旭峰
母亲的借口
神龛上的灰尘还没打扫干净,菜园的篱笆破洞还没堵上,猪圈门还没上锁,几只母鸡还没有着落……
搬进小区数天了,母亲还盘桓在乡下老家。
每次电话催促,她总有各种借口,各种不来的理由。
母亲放不下的,太多。
她放不下堂屋里供奉的神灵、宗祖。放不下居住过几代人的老屋。放不下菜香萦绕的灶台。放不下生蛋的那几只母鸡。放不下忠心耿耿的花狗。放不下菜园里的菜苗、葱蒜。放不下鸡鸣犬吠的院子。放不下炊烟袅袅的村庄。
几十年来,母亲在她的村庄,劳苦惯了,忍受惯了。她担心适应不了新的生活。
逗留老家的那些日子里,母亲在梳理自己过去的岁月。
这一生,不堪回首。忆旧感伤的泪水,濡湿了菜园。
那个家,经历了太多的苦——贫穷,歧视,白眼,冷遇、欺凌、屈辱。一个个不忍回顾的画面,清晰地浮现。
淡淡忧郁,覆盖了母亲的脸庞。
她怕坐吃山空,怕收入低微的儿子,承担不了生活的重负。
她还顾虑,城里那个相逢如陌路、对门不相识的冷漠小区,邻里关系如何相处。
然而,无论有多少个借口,终归要妥协。
毕竟,借口,抵不过残酷的现实,
也改变不了风雨飘摇的人生。
对不起一条狗
狗比人更懂感情。
我家那条花狗,从来就不会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盗鸡鸣。
作为一条八岁的老狗,它与我们家结下了深深的感情。
逢年过节,祭祀过宗祖,喂过花狗,我们才能进食。狗不会说虚情假意的奉承话,心里却记下了恩情。
八年如一日,默默守候在房前屋后,守护着一家人恬适的梦境。
花狗弄不明白,我们一家为何离它而去。偌大一个县城,竟然容不下一条狗。
人去屋空,房门上锁。小院里,只留下一盆煮熟的土豆,以及鸟语声声。
一条老狗,静卧在屋檐下,默默地等待。
日升月落,时光流转。
吃完那些冰冷的土豆,它爬过篱笆,到二叔家蹭猪食,囫囵几口,又回到小院中,哪里也不去。
我不知道,老狗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白天和黑夜。
每次回老家,它都卧在屋檐下。疲惫地站起身来,继而精神焕发,摇动着绒毛稀疏的尾巴,像一个撒娇的孩子,围在我们身边打转。
每次离开,老狗总是神情忧郁地目送我们走远。
挽留的目光,拽不住远走的脚步。渐行渐远的步伐,踩碎了一地的失望。
也许,狗也会伤心绝望——漫长的等待,遥遥无期的归期。
花狗进食日少,绒毛渐稀。
初一那天,母亲回老家敬神。她看到的,只是一团杂乱的尸体。
一群苍蝇,嘤嘤嗡嗡地飞舞。
母亲挖一个土坑,算是把花狗厚葬。
一铲又一铲厚重的黄土,掩埋了花狗的忠诚,掩埋了花狗的一生。
却无法掩盖我们的无情,以及愧疚。
清明,跪在外公的坟前
没有纷飞细雨,没有欲断魂的路上行人。
一轮红日高悬。遍野山花争艳,满山林木苍翠。
这是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跪在外公的坟前。
面对一个陈年的土堆,作揖叩头,焚香烧纸,奠酒敬茶。
外公二十出头就病逝,长眠于地下。那时,他年幼的女儿,还不知道爸爸这个称谓。
如果外公的时光能定格在六十余年前,他还没有我今天的年岁。我就可以与他对饮山野,共话人世的苍凉。
对他叙说,或给予他谴责。就着一壶土酒,讲述我失怙的母亲坎坷曲折的人生。
一个土堆,掩埋了外公作为人父的责任。一个孩子冷凉的际遇,却从此开始。
跪在外公的坟前,似有千言万语,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静静地看着纸钱一张张化为灰烬,看缕缕青烟袅袅升腾。
年届花甲的母亲,内心已然安静了。不再诉说外公离世后,她所经历的艰辛,所遭受的生活磨难。
这么多年来,外公背靠青山,看四围苍松吐翠,看山花争妍,看云霞变幻,看鹰在苍穹上孤独地盘旋。
或许,亘古寂静中的外公,应该还有期待,等每年一度的清明,等他流淌于人世的血脉。
多年过去,在这个黄昏,我才走到了外公的坟前。
我想跟外公握手,想和他拥抱,想在他的怀里,大哭一场。
伸出双臂,碰触到的,只有坟头冰凉的石头。
想和外公说说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启齿无言,只充塞着满腹的愧疚。
说什么都显苍白,我来得太晚。
再多的话语,也将如坟前的灰烬,晚风一吹,四处飘散,渺无踪影。
在外公的坟前,只能静静地跪着,跪着。让外公听听,他的血液,在我体内汹涌澎湃的声音。
一堆荒冢静默在枯草中
说不清这是那一代祖人。
一个小小的土堆,被枯干的杂草淹没。
周围遍布牲畜粪便,荆棘丛生。
每年清明,散居在四方的后裔,都来荒冢前祭奠。
多数人,都不知道荒草下面,长眠的是哪一位祖先。
匆匆焚香烧纸,匆匆敬献果酒,匆匆作揖叩头,匆匆抬足离去。当然,难免为祖人的尴尬处境唏嘘一番。
荒冢周边,异姓的豪碑林立,奢华大气。
集资立碑,是每年清明不变的话题。
多年过去了,荒冢依旧,口若悬河依旧,夸大其词的宏大梦想依旧。
有些困苦的家庭,承担不起无谓的奢华。
那一块小小的墓碑,刻不下太多想不朽的名字。
也容纳不了太多的功德。
世故的白菜
一辆板车一棵树,一堆白菜一老翁。
坡道陡峭,白菜沉重。
老者把板车停靠在路边,喘气,抽旱烟。
夏日的阳光,火辣辣。把从未谋面的人,撵到了一起。
聊收成、价格、市场。以及,白菜从青变黄,从黄变青。
依靠白菜养家糊口,得设法满足顾客的需求。颜色,只不过是一瓶农药的事。
可怜的白菜。价格高的时候,送人一棵,还想要两棵;价格低了,送两棵,一片菜叶都不想收下。
老者的叙说,伴随烟子从浓密的胡须间冒出来。
啪!老者一泡浓痰砸在地上。
激荡起一片灰尘,几缕尘嚣。
黄昏,山村即景
等人,在一个陌生的山村黄昏。
山陌生,水陌生,一张张匆忙而过的面孔,陌生。
这个黄昏,我只熟悉自己,熟悉拂过脸庞的那一缕微风。一切都在黄昏里匆忙着。只有我,安静地坐在车里,打量着陌生的村庄。
对面那一户人家,并不知道我正在挡风玻璃后面,静静地看他们。
男人在井边打水。
大女儿身着校服,洗菜。
老二蹲在屋檐下,背靠墙,把本子放在膝盖上写作业。
黑脸老三追赶花脸老四,农家小院里,洒落一地天真的欢笑。
老五蹲在门前,用尿水和泥,揉捏童趣。
老六在女人怀里哺乳。光着小脚,不停踢蹬。一双小手,抱着那一只饱满、颤悠悠、源远流长的乳房。
半遮半掩的肚腹里,难道,老七也在踢蹬?
夜幕降临。那一户人家,房门关闭,灯光亮起。一群小孩儿,叽叽喳喳。
身旁的竹林里,一群小鸟也入巢了,啾啾啾啾。
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明天,竹林中的小鸟,不知将飞向何处。
小孩们将走向哪里?
那栋房子里,也将只留下严重超载、体力透支、被压榨干的,两副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