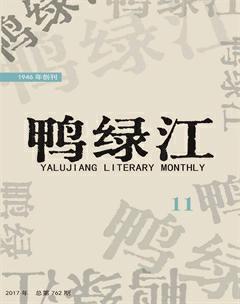底层问题与“先锋”的遗传基因
刘诗宇
在鬼金2017年出版的小说集《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封面上,有这样几个引人注目的词汇:“中国卡佛”“吊车司机”“性爱与死亡的奏鸣曲”“黑色故事集”。前两个词说的主要是作家本人的身份。与美国小说家卡佛一度是工人一样,鬼金一边在轧钢厂开着吊车,一边却坚持写着小说,写着那种能够发表在《花城》《十月》等纯文学期刊上的严肃文学。在当下严肃小说、诗歌的创作主体中,像鬼金这样拥有“双重身份”的作者并不算少,但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严肃文学与“底层”“民间”的割裂趋势似乎越演越烈,因此鬼金的身份非常吸引眼球。普通读者以及文学研究者们相当关注这样一个来自底层、书写底层,却又似乎出手不凡、字里行间透露着大量纯文学的熏陶的作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文学的技法相结合,进而写出一系列“新”的故事——能够与一般深受学院派欢迎的作家作品相区别的故事。
后两个关键词侧重指文本的审美特质。性爱与死亡的主题式概括,以及“黑色”的美学风格,不禁让人联想到80年代以来“主导”着当代中国严肃文学发展的先锋文学。时隔多年回望,先锋文学贡献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于历史与人性的另一种思考与书写的方式,但是其与市场的契合点却似乎始终在一些极端、阴暗、暧昧、丑陋的因素上,例如死亡与性爱。小说集的封面已经勾勒出了鬼金这部作品关系到的两个重要范畴——底层与先锋——我并不质疑这两个范畴的准确性,并且我接下来对这本书的讨论也将从这两个范畴展开,但是我希望能将讨论从身份与极端性的“噱头”中延伸到底层文学的客观性与先锋书写传统的复杂性中去。
一、底层文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底层文学这一概念因前所未有的泛化而边界不明,因此虽然鬼金的这部作品并不是像《那儿》《问苍茫》《马嘶嶺血案》那种意义上的底层文学,但是《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里七篇小说所共同的荒芜而破败的轧钢厂背景,使我们在讨论这部小说集时,还是无法绕过底层文学这一概念,以及泛底层文学所面临的问题。
底层文学从兴起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在书写对象与读者、作者无法形成一种对等状态时,底层文学应该如何处理苦难。许多人会质疑,如果底层文学因为由作为精英的作家创作,发表在一般报刊亭乏人问津也根本无法买到、在网上也难以看到电子版的纯文学期刊上,而远离了底层文学书写对象的生活,那么底层文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存在着两个也许并不矛盾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底层文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重塑文学的“风雅精神”,让一度被社会正义与道德所忽略的底层世情重现于底层之外,撼动“中层”与“高层”的内心;一部分人认为无论这种风雅能否实现,底层文学应该为真正的底层人士提供日常生活之外的一种告解乃至精神的“出路”,文学所能提供的,不应仅是让读者反复重温日常生活中的痛苦。
是否书写、如何书写苦难不仅是文学技巧上的问题,更是文学立场上的问题。大量的底层文学都以肉体上的残缺或死亡、精神上的堕落或迷茫作为人物的结局。许多底层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其对现实的反映极具震撼力,但当这种泛悲剧化安排成为一种普遍趋势,结合着上面对于真正的底层人“看不到”或“不看”底层文学的质疑,一部分底层文学难免背上“消费苦难”的罪名。
两个问题背后藏着盘根错节的逻辑链条,本文首先想讨论的是《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回答如上所说的问题。理清鬼金小说集与这个重要问题的关系,不仅能让对文本所承载的审美感受的阐释与文学史意识相联系,更能使这一文本承载的社会与文学史层面的“意义”得到显现。文学史如大浪淘沙,但是具体时代中每一个文本的内部,都有着一个能够辐射整个时代的微观风景。
鬼金对于底层的处理,首先具有一种全面性,《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中的七篇小说从不同角度拼贴出了一个东北轧钢厂的全息影像。《彩虹》写无父无母的三姐弟,如何在夹缝之中苟且偷生,如何从悲惨的童年中逐步获得伤残的人格;《二春》写轧钢厂社区中的一个先天不足的傻子,在母亲死去、弟弟入狱、女友被其家人强行带走、自己的腿被打断、睾丸被砸碎之后,最终死在了雷雨天坠落的大钟里。《彩虹》与《二春》描写的毫无疑问是生存在轧钢厂“金字塔”最底层的人。《芝英》写理发店女郎和猪肉贩子的婚姻生活,在轧钢厂的生存群落中这二人已算得上是众人间的“中产”。《李元憷》《旷夏》《朱弭》三篇的主人公颇有些相似,他们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无法赢得世俗的尊严,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借由哲学、文学等书籍上探到了轧钢厂生存空间的“上限”,在挣扎徘徊中,他们俨然是轧钢厂的“精神贵族”。《明莉莉》一篇中的老朱也属于这种痛苦的“精神贵族”,而女主角明莉莉因为调职报社,而显得与轧钢厂的生活氛围略有些游离,但人物的悲剧命运却始终无法超脱轧钢厂的宿命。通过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划分,鬼金用七篇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轧钢厂精神图景。
不幸的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幸,在鬼金的故事中,东北大地经济的滑坡让轧钢厂变成了一座废墟,这里除了满地的废弃金属,便是苦难与无法被满足的欲望。在七篇小说中,有五篇涉及了主要人物的死亡、残疾、入狱,从表面上看,鬼金对于这些故事的处理似乎与一般的底层文学并无不同,但是如果按照上中下三个层次对七篇故事中人们的苦难命运与悲剧结尾进行细读,则可以发现人物的命运实则相当丰富。形形色色的苦难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人性的丰富性。
二、性欲与尊严带来的永恒苦难
《彩虹》的主人公是三个少年,而作者在开篇就设定了一个母走父死的背景。轧钢厂虽然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因钢铁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曾经辉煌过,但是到了鬼金的故事中,生命和道德都在这里变得极端脆弱,而彩虹、天真、可爱姐弟三人必须在这个残酷的世界自力更生。这篇故事中有一处场景描写极其出彩:
电闪雷鸣过后,暴雨从天而降,天地间连成一片。可爱给二叔拿的烧纸落在院子里几张,被雨淋湿,很快变成了纸浆。我翻看着一本《王老师跟小学生谈作文》,可爱疯累了,蜷缩在炕上睡去了,彩虹给他盖上被子……暴雨的院子里,出了水井在那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了。地面上的积水汪着,雨大,水汪变成了小溪,从墙根的一个水洞流出去。我突然感到什么滴在了我的头上,我没在意,继续削着木头匕首,不小心划伤了一下手指,但我不在乎,把伤口处放到嘴里啯了几口,继续削着。又有什么滴落在我的头上,我抬起头看见屋顶漏雨了,那纸糊的棚顶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水印,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动物。我没吭声,去厨房,找来一个脸盆,放到那个地方。
这个片段发生在彩虹姐弟父亲死后,三人找到谋生的手段之前。可以想象,无论是墙上的漏洞,还是漏雨的屋顶,都是孩子无法修复的。三个小孩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去学校读书,吃的都是父亲活着时剩下的东西,而且他们住的地方马上要被狠心的叔叔婶子夺走……他们身边的一切消耗都是永久的“减法”,三个孩子的未来看不到任何出路。这种感觉让人惶恐、焦虑,但是在鬼金的处理中,三个小孩的精神状态并不能说得清是否悲伤,他们只是在继续手头上的事情罢了。
彩虹、天真与可爱三姐弟所面临的处境,毫无疑问与我们常常说的苦难相关,但是鬼金的处理提示着我们,对于真正在“苦海”里成长的人来说,衣食无忧者对于“苦难”的定义往往是失效的。从这个角度上,鬼金的创作也许对底层文学应该如何处理苦难这件事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对于极为熟悉轧钢厂里一切的吊车司机鬼金来说,苦难本身自有其辩证法,它是一个在接受者与观察者两种视野中的可以出现清晰差异的概念,也许并不必强行将两种视野进行统一。这也就是为什么鬼金没有站在一般常识的角度上,将彩虹三姐弟处理成因为父母缺席就始终悲天恸地的苦情人物,因为那可能只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的本能想象。
在《二春》一篇中,鬼金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二春是个“先天不足”的傻子,大多数时间痴痴呆呆、心智不全,但私下里自己偶尔也有着一番心思。弟弟三春是轧钢厂保卫科科长时,二春可以随意偷铁换钱,尽管他会被废品站的人克扣,但至少吃穿不愁。后来三春贪腐事发,二春失了庇护,只能捡废品,饿极了甚至去垃圾堆里捡些吃的,就连在暖气管道下面睡觉的地方也被另外两个乞丐霸占。这种处境当然也与我们常识中的苦难相关,但在文本中二春的痛苦并没有持续很久,顶多是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般,懊恼一番之后便在土谷祠睡下,醒來之后一切都云淡风轻了。在这里以二春的故事为例,鬼金或许再一次回答了关于底层文学与苦难的问题。对于真正长时间经受苦难的人来说,苦难常常就化作生活本身,而无谓悲喜,就像我们并不会看到任何一个拾荒者就泪流满面一样——彼时在没有文学化的渲染与煽情时,我们时常会默认拾荒这件事就是那个衣衫破烂者本来应有的命运,而不值得大惊小怪——苦难对于经历与旁观来说,是截然不同的。
有了这样的处理角度,所谓悲喜在鬼金的轧钢厂故事中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与一个曾经被强暴并且心智失常,且患有“兔唇”的女拾荒者结合是一件怎样的事?在鬼金笔下,二春与这名叫作二华的女拾荒者的恋爱被处理得如同春风拂面。在普通人看来这是面对命运逼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但是在《二春》中这却与任何一段让人憧憬、悸动的爱情一样:
二华这时候,坐在她的纸盒子上,从兜里掏出来一块糖……把糖放在嘴里一半,咯嘣一声,咬下来另一半,伸手递给二春一半说,别人给我的糖,给你一半。二春说,我不要。二华态度坚决说,给你,你不要,我扔了。二春凑过来,说,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心眼好的人。二华嘿嘿地笑。二春伸手要接糖,二华看到二春的脏手说,你看你的手,这么埋汰,把嘴张开。二春只好张开嘴,二华把半块塘扔到二春的嘴里……二华顺手捡起几个落在衣襟上亮晶晶的糖渣,放到嘴里。二春吃着糖,二华吃着糖,两个人吃着糖,一句话都不说。
以半块糖为桥梁连接的身体背后,是两个社会边缘人的相互信任与接纳,这让一个简单的片段变得极为动人。二春对二华的感情里伴随着性的冲动,伴随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就像正常人的爱情一样。在鬼金的笔下,逆境中偶尔的风平浪静就包含着顺境中可能难以想象的雀跃与幸福,这是事件本身与人的情绪特质结合之后焕发出的另类光彩。
那么在书中对他们而言真正的苦难是什么?《彩虹》中的叙事者天真是个颇有些复杂的角色,他怀揣着三棱刮刀在钢铁厂里好勇斗狠的感觉颇有些苏童笔下小拐的感觉;而他用废品卖钱、企图发家致富的状态又和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比较相似;他在草地上对着天空自慰、想象自己是每天陪在菩萨旁边的释迦牟尼,又不禁让人想到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王二。这几个角色骨子里都为尊严、情欲以及两者抟化成的人类文明社会的普遍的“界限”束缚着。天真虽然并不如上述所说的三个形象那般具体,但对他而言真正的苦难也是由这些因素而来。正是受困于尊严与肉欲,天真一直追逐着肖浪生的幻影,诱奸了李园却又不敢真正承担责任,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能够包容他的肉体和精神而惶惶不安。最终彩虹为了解救天真而委身于保卫科长李连德,天真因为连累了姐姐而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与羞耻感,而他泄愤、报复的形式竟然是强奸了彩虹。这样的安排虽然看上去有些仓促和勉强,但也基本符合《彩虹》通篇中,所有异性都被天真视为潜在的“性交对象”这样的叙述语调,道出了人物被欲望牢牢束缚,爱也诉诸“性”、恨也诉诸“性”的痛苦处境。
天真的弱点几乎可以辐射到鬼金笔下的整个轧钢厂世界。《二春》中二春与二华在苟活之中发展出一段令人心酸的“爱情”,然而二春投射自己感情的方式却仅能止于性。在二华喂二春吃了糖块之后,他满心欢喜,然而释放这种欢喜的方式却是在没人的时候不断地念叨一句话——他先天的境遇就决定他不可能赋诗一首以歌颂爱情,而只能不断地重复着“妈嘞个巴子的,小逼”这句话,感受着这里面来自于异性以及性交等对自己完全陌生之物带来的刺激感——是因为二春天生痴傻、人近中年而始终没碰过女人,所以只有兽性而缺乏人性的表达方式吗?细读《二春》,不难发现这句脏话中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性”在轧钢厂世界中近似于一个魔咒,性欲变成了让二春等角色内心始终填不满也掏不空的“原罪”,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可以寄托精神的地方。
不仅是二春,乃至《明莉莉》里的老朱,想从高升的妻子明莉莉那里寻求身份认同,也只能借由床笫之间的肉体交流乃至肉体折磨。《李元憷》中李元憷从“你好春天”那里获得世间唯一的慰藉,其体现也是“你好春天”愿意与他在乱堆的书籍中做爱。《芝英》中的李臣、《旷夏》中的旷夏也皆是如此,“性”和“欲”成了人们面临的最严重的苦难。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无论是否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尊严都被来自物质生活的蔑视煎熬着,而这些问题,最终都被转折到“性”上。
“性”方面的空虚与苦闷,是《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是轧钢厂世界中底层苦难的一个核心点所在。这样的安排虽然在《芝英》以及其他篇目的部分段落中显得有些“刻意”,但从这个角度去讲述底层世界的苦难,或许也为底层文学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答——如果对底层面临的苦难的书写,最终能够落到人性根本的局限上,那么所谓“消费苦难”的困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三、“血统”与底层世界的恶性循环
在《二春》中,有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片段。二春的父亲顾三金是个酒鬼,一次酒醉后顾三金看到痴傻的少年二春,心头火起,竟然將二春活埋在了轧钢厂附近的土山上。索幸二春的母亲肖美兰及时赶到,拼命将二春救出,后来肖美兰与小瞎子亮三的母亲马慧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还不是那个驴操的顾三金,喝了酒,耍酒疯,嫌弃二春闹了,是傻子,借着酒劲,拿着锹,到后山上要把二春埋了,要不是我从厂里回来得及时,二春可能……肖美兰眼泪汪汪的,老天爷这是作的什么孽啊?让我遇上这么个驴操的。要不是他天天喝大酒,二春生下来也不会这样……
随后马慧道出了一段近似的命运:
我家丁国强当年要不是老去卖血,我想亮三也不会这样(天生眼盲),说到底,都是我们父母作的孽啊?我也想过随便找个地方,把亮三扔了算了,可是每次都不忍心……我也想再生一个,可是,丁国强那身体卖血败坏了,怀不上了,这也许就是命吧,他卖血给亮三治眼睛,什么北京上海的都跑遍了,还是没治好。身体也败坏了。
鬼金从性与尊严的角度,将对底层人而言的真正苦难进行了交代。对类似天生痴傻、眼盲这种于旁观者视野中更显苦难的命运,鬼金则采取了另外一种书写策略。借人物之口,东北轧钢厂之所以沦为底层生存空间并且充满生离死别、压抑与煎熬,得到了一种“血统”角度的阐释。只要这种“血统”繁衍下去,轧钢厂的黑色故事将在一种“生生不息”的“恶性循环”中不断继续下去。
顾三金为何酗酒?丁国强为何频频卖血?这两种行为背后的推手都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生存之困——然而这种情况下卖血是饮鸩止渴,酗酒则是自我欺骗。近几年东北经济的“断崖式”下跌其实早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就埋下了种子,也许工人顾三金与丁国强们是新一代时势与政治的牺牲品,而外力又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相糅合,为他们的后代打上永世不得超生的诅咒。
在《二春》中,二春知道自己是傻子,但他并不曾真的为自己痴傻这件事本身而感觉到痛苦,因为我们这些旁观者眼中针对他而言的苦乐,已经超越了他的认知极限。二春与二华的爱情一度是甜蜜的,他也知道美女芝英是“天鹅肉”,而二华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此与二华在一起已经让他感受到了最大的满足,但是可以想象,即便最后二春不死、二华也不被带走,两人结合之后产生的下一代,也将是旁观者眼中经受苦难的一代——一个先天痴傻的父亲,与一个精神失常且患有兔唇的母亲,他们的后代有可能扭转未出生就已注定的厄运吗?
在《二春》中,瞎子亮三娶到了一个身体正常且漂亮的媳妇,甚至连傻子二春都因嫉妒亮三“光明”的未来而与他“绝交”。亮三的未来是否真的得到了“光明”?在《李元憷》中,鬼金借李元憷的回忆不动声色地道出了亮三的结局——亮三的媳妇“理所当然”地嫌弃了瞎子丈夫而与别人私奔了,亮三痛苦之余自缢身亡——二春和亮三在小说之外抽象成轧钢厂所有“先天不足”的人们,他们的未来之路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封死了,这些延续着同样基因的人在轧钢厂中永世不得超生。
这种安排在我看来正是鬼金的高明之处,也是文学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的独特之处,同样说的都是人的逆境、一个区域的衰落,用形象与故事很多时候能比冰冷的数据与干枯的论述走得更远。
如果说二春与亮三的例子是极端而鲜明的,那么旷夏、李元憷等人则相当于在悄无声息中被打入悲剧的命运中。《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的封面将鬼金比作“中国卡佛”。卡佛擅长的是借助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让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身份与关系——比如由父亲身份引出的父子关系,比如由丈夫身份引出的夫妻关系——的本质与另一面得到恰到好处的揭示。在我看来,这部小说集中的《旷夏》一篇中的一些段落与卡佛的这一特点颇为相似。
《旷夏》让一个父亲讲述自己死去的儿子旷夏的一生。在这篇小说中作为叙事者的父亲形象与着墨不多的母亲的形象很能说明家庭关系如何影响一个人,甚至不知不觉地将人赶上绝路。为了说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必须先将旷夏的人生经历简单复述一下。旷夏从小孤僻,学习一般,后来进了技校,毕业之后进入轧钢厂当吊车司机。这本来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但表面的平静下,旷夏的心境与对生活的期望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出现了致命的“错位”。旷夏喜欢读书甚至达到病态的程度,通过读书让自己的精神有了一些不同之后,他拒绝改变自己间接改变现实,用消极的方式企图对抗现实,拒绝循规蹈矩的生活,而始终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旷夏的人生有几个重要的节点,在他初成为吊车司机、开始在一个“地狱”般的环境中工作时,他的灵魂与现实就开始出现割裂。旷夏心态的失常始于这样的人生遭际,而此时虽然母亲对他的工作环境也非常不满,但除了以泪洗面母亲保持着缄默。作为叙事者的父亲的语调非常具有许多中年男子说话的特点,即便是在对亡者的自语中,也不忘了“自我吹嘘”——小说中多次出现了“我本来想找人花钱让你去当兵的”“我还可以动用我的关系帮你的,但(我)不是那种喜欢麻烦人的人”——仿佛一切都在父亲的掌控之中,只是自己不愿意“出手”罢了。
在旷夏的命运开始误入歧途时,作为父亲与母亲,两位老人采取了“不治”的态度。母亲的眼泪是数千年来中国女人的一个基本表达方式,用哭泣表态同时也是用哭泣来逃避行动。而父亲强作镇定的吹嘘同样是在逃避实际行动,还仿佛是在体现一种不干涉的“大度”,支持儿子“要在轧钢厂把我的牢底坐穿”。虽然从习惯的思维来看,母亲的哭泣与父亲的镇定看似无可指摘,但实际上这种判断的背后则是,在千千万万个类似旷夏所处的家庭中,父母在该对子女行为做出干涉时,却因为个人能力或认知的局限而选择袖手旁观。
实际旷夏的母亲也是一个可怜人的形象,然而我之所以认为她的哭泣是一种“不治”的表现,是因为她在另外一个时刻表现出了无比强硬的态度。后来旷夏与一个比自己大,并且结过一次婚、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相恋,这段时间旷夏出现了难得的快乐状态。然而此时母亲站在传统的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观念上,先是准备好了农药打算以死胁迫,之后背地里找旷夏的女朋友谈判,使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在这一事件中母亲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进取状态,并且成功完成了自己的目标,这说明旷夏成为吊车司机时,母亲认为事态远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远没有触及自己观念中的“禁区”。从《旷夏》整个情节来看,这件事是对旷夏精神的又一次严重打击,而此时父亲再次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在其他的自语中,父亲表现出一副通情达理、能够在精神上理解儿子的姿态,但实际上在他应该出手支持儿子时,他始终是缺席的。
以如上两个事件为代表,鬼金写出了一般底层家庭中家庭关系对下一代命运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以父母之爱“好心办坏事”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并非所有父母都具备替下一代判断人生选择利弊的能力,而此时他们仍然盲目地坚持自身判断的权威性,不知何时应该缄默、支持、反对。以旷夏、李元憷等人为代表,虽然鬼金笔下的这些“读书人”形象本来就带有致命的人格缺陷,但是他们的悲剧命运与家庭关系的影响不可分割。这一层面上,他们的命运与二春、亮三等人一样是先天注定的,因为没有人有权选择出身与家庭。
因此从二春到旷夏,在鬼金笔下,轧钢厂的黑色故事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循环,而无论是真正对于底层人自己而言的苦难,还是对于旁观者而言的苦难,在鬼金的小说中都得到了相应的解释。《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对于苦难的处理并非仅止于呈现,相对成体系化的故事中,不仅有命运的悲苦或怜悯,其中还有相对苦难而言的平淡与快乐,还有着对于这一切背后原因的探究。
四、先锋的挽歌与“读书人”形象
鬼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我是先锋小说的遗腹子”。在那篇访谈里鬼金对自己的话有所解释,其大意是先锋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是绕不过去的,与此同时,当年的先锋作家重拾“传统”,多少让他觉得有些不知所措。鬼金在访谈中还说到“中国少有你不看名字一看文字就会知道是谁的作品的作家”,然而在阅读《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时,我想即便不看名字,文本的语言、叙事腔调、人物、美学风格也会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在先锋小说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作品。
因此,除了底层文学之外,先锋文学是谈论鬼金这部作品时第二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尽管鬼金的小说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底层文学,也未必是纯粹的先锋文学。上文中“性”与“尊严”为底层人带来的永久苦难,实际上也不只是一个底层文学范畴内的话题,鬼金从这个角度对文学如何处理苦难的问题的回答,其实更像是先锋文学的方法与意识触及底层题材之后的一个自然的“化学反应”。
从先锋文学对后世当代小说的影响入手,是分析这部小说集中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结构意识以及经验范畴的绝佳角度。首先说人物形象,先锋文学在80年代名噪一时之后,其代表性的作家迅速成为当代文坛的中流砥柱,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这些作家持续不断的创作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概念的边界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这一批作家特别擅长塑造一种“多余人”式的形象,类似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一群大学生、徐星《无主题变奏》《剩下的都属于你》中带有痞子特性的主人公、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余华《兄弟》中的宋钢、苏童《河岸》中的库东亮、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谭功达与谭端午,都属于这一人物谱系。这一人物谱系的“多余”特质几乎构成了先锋以降、直至今日严肃文学人物形象身上最为典型和普遍的一种精神特质。
严肃文学所谓70后、80后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带有这样的气质。在鬼金的《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中,《李元憷》《旷夏》《明莉莉》《朱弭》中的男性“读书人”形象,与这一“多余人”形象体系非常相似。也许针对鬼金笔下的这一类人物,会有研究者倾向于用“知识分子”形象去指代他们,但此处之所以不用“知识分子”而用“读书人”来指代李元憷等形象,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一词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失去了一个概念的精确性,社会责任感的确认让严格地讨论“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奢侈的事情。而李元憷、旷夏等形象之所以显得多余而痛苦,其原因也许就在“知识分子”如何“降格”为“读书人”的过程之中。
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为例,谭功达曾经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但因为个性上的弱点以及命运弄人而失败,他从一县之长变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多余人”。到了他的儿子谭端午那一代,乌托邦的梦想与现实越来越远,曾经谭端午至少还是个追寻梦想蔑视现实的诗人,但后来他也只能将自己的桃源梦藏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任由肉身经受俗世的种种折磨。
到了鬼金的小说中,这些读书人的命运更显得可怜得多。在《李元憷》《旷夏》《朱弭》中都有着不得已而搬书、烧书、卖书的情节,书就是这群人的精神寄托,而在轧钢厂世界中,他们的精神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如果说在“江南三部曲”中,人物心心念念的改革让他们还多少与“知识分子”这个光辉但在今天也显得有些尴尬的词匯有所联系,那么在鬼金的小说中,这些彻彻底底与所谓“知识分子”绝缘,而单纯是“读书人”或者“爱书人”的角色们,只能空留一腔指向不明的余恨。在这部小说集中,读书人形象对现实与命运的不满,时常化作对轧钢厂的“恨”——书中多次出现“要在轧钢厂把我的牢底坐穿”“让我做这轧钢厂最后的守灵人”——希腊文中的“哲人”指的就是“爱智慧的人”,而没说他们必须改变这个社会与现实,而轧钢厂中那些爱智慧的人,却只能带着与轧钢厂也是这个现实社会同归于尽的愤慨、悲凉与无奈,四处碰壁,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所谓“遗腹子”,指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但父亲已经死了。“遗腹子”们很难名正言顺地对自己的血脉追根溯源,他们生来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一环,生来就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庇护伞。鬼金说自己是先锋小说的“遗腹子”,这里面其实不无来自历史、社会与文学剧变层面上的唏嘘与悲凉。李元憷等形象酷爱读书,喜欢精神与先贤的字句与思想相伴的感觉,他们延续着80年代沉淀来的历史惯性,却不知历史的巨轮早已离开这条轨道。不难看出,小说中的读书人们,几乎就是作家的自况,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小说集里,作家也只能用读书人如被钝刀割肉般的处境来讲述一个警世的寓言——如果你对现实生活的期望在于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在爱人与朋友面前从物质与社会地位的角度赢得尊严,那么仅仅读书对你的现实生活而言是毫无疑义的。
在鬼金的这部小说集中,有两个颇有些特殊的形象,一个是芝英的邻居肖浪生,一个是二春的弟弟三春。即便这两个角色的命运殊途同归,都进了监狱(对于肖浪生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只是借人物之口表达一种相对确定的猜测),但作家却从未正面描写过他们内心的痛苦。在轧钢厂世界中,肖浪生靠着长相和风趣、三春靠着身为保卫科科长拥有的生杀大权,夜夜风流、不愁吃喝,理所应道地傲视二春、亮三之流,当然也无视着李元憷、旷夏、老朱们。所谓的精神追求和来自道德、伦理方面的煎熬在他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而似乎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轧钢厂中真正适者生存的人。为什么小说集题为《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从先锋文学或者说当代严肃文学的人物谱系走下来,我们不难发现,包括鬼金小说在内的一批创作,正是为一个逝去的时代、为风光不再的严肃文学与读书人而作的挽歌。
从先锋梳理开去,其实鬼金的小说中有更多可以被分析和讨论的东西。比如说鬼金曾经从对先锋文学的追思谈及对小说“结构意识”的重视。在这部小说集中,我们也能很明显地看到鬼金努力从多篇小说中寻找一个可以串联在一起的“结构意识”——例如人物在不同篇目中“旁见侧出”,以使轧钢厂世界的不同时间、区域出现互动;例如在多篇中都出现的“大爆炸”事件,是一个让读者在多篇未明确交代时间的作品中寻找先后顺序的“标尺”;例如意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混同,以及类似芝英魂骑白马、旷夏化身小羊认父、一个日本人将自己砌在水泥墙中不吃不喝某一天又突然神秘消失等超现实事件之于小说结构的“节点”式意义。这些都是鬼金在小说结构意识方面的匠心所在。
又比如鬼金带有浓郁先锋“味道”的语言。在我看来,先锋小说沉淀下来的语言经验是一种“转述”式的语言,之所以先锋以降的大量小说中可以完全不使用引号,人物的对话也不再追求个性化,甚至小说的叙述时间可以错乱、复沓,小说可以不顾情节逻辑而去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某种程度上都得益于这种“转述”式的语言。这既是好事——让更多的题材可以被纳入写作,让更隐微的情感在文本中煥发光彩,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相对“便捷”的方式进入创作——但同时可能也是一件坏事,因为文学与现实相连通的能力、既往文学所承担的意义与责任也因为这种“转述”式语言被前所未有地消磨着。
斯蒂芬·金有一本创作谈名为《写作这回事》,在这本书中斯蒂芬·金的说法或许可以为说清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恰巧,鬼金曾经说自己的笔名是由“鬼子”和“斯蒂芬·金”组合而成,这两个作家代表着他非常喜欢的两种创作方式。在我看来,斯蒂芬·金的创作虽然因以恐怖小说知名,而被划入到通俗文学领域,但是无论是在内容和形式上,他的创作都意义非凡。从形式上,相比于上述的“转述式”语言,斯蒂芬·金使用的常常是一种“在场感”极强的语言。为何先锋作家在处理当下经验、书写一些当下的生活场景时,总是显得不如讲述历史那般游刃有余?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就与唐诗宋词使用的文言难以处理科学民主与工业文明一样。斯蒂芬·金的语言虽然未免体现出一种“图像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语言对于小说如何处理具有“当代性”的生活经验将非常有参考意义。
内容上,在恐怖或惊悚题材之外,斯蒂芬·金基本无所不写,无论是纯文学最感兴趣的人性问题,还是普通读者更感兴趣的传奇、罗曼司,这些在斯蒂芬·金的笔下从来就是难分彼此的。而今天中国的严肃文学则并非如此,固有的文学评价机制和人为制造的严肃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对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让当代严肃文学所处理的经验范畴不断萎缩。打破种种经验范畴之间的壁垒,也许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我要将以斯蒂芬·金为代表的一些小说家放在比先锋作家或更广义的中国严肃文学作者更高一筹的位置。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告别过去、呼唤未来的时代,先锋意识、乡村经验、严肃文学看似渐入“黄昏”,此时我更期待的是作为斯蒂芬·金的鬼金,能为当代文学带来更加不同的风景。
【责任编辑】 行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