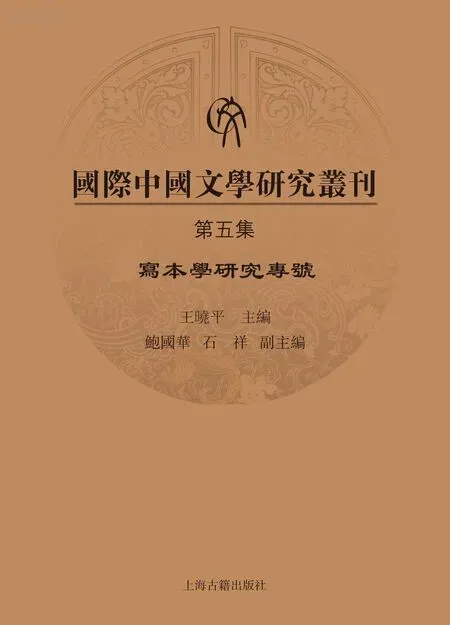《本朝文粹》校訂本考察*
于永梅
一、 引 言
《本朝文粹》是日本平安時代仿照我國《唐文粹》編撰的漢文經典選集,完成於11世紀中葉,其在文學史與思想史上的地位近似於我國《文選》,是日本古代最具代表意義的漢文學總集,是研究我國文學在日本傳播與影響的重要資料。
要想弄清一部傳世文獻的面貌,并對其進行更好地研究,最佳的辦法是考證其最善最古老的版本。但是近代以來,《本朝文粹》的校訂本大都是以其成書600年後出現的刊本爲底本。這600年間經過了多次的轉寫,導致産生了訛脱,並派生出多個異本,這樣就使刊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以刊本爲底本的校訂本的準確性自然也就值得商榷。
因此,本文就對《本朝文粹》現存校訂本進行整理,並以現存寫本中被認爲是最善最古老的身延山久遠寺藏寫本(以下簡稱“身延本”)爲對照,考察分析現存校訂本在對寫本釋録中存在的問題,比勘其文字、篇籍的異同,糾正其訛誤,力求接近原文真相,爲論證域外漢文文獻的漢字漢語、典故以及校勘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空間。
二、 《本朝文粹》
《本朝文粹》由藤原明衡編撰,共十四卷,收録了自弘仁年間(810—823)至長元三年(1030)間漢詩文的精華,有賦、詩、對策、表、奏狀、序、願文等38種文體共432篇作品,其中以奏狀、詩序和願文爲核心。主要作者包括大江匡衡、大江朝綱、菅原文時、紀長谷雄、菅原道真、源順、大江以言等宇多、村上、一條各漢文學繁榮期的代表人物。作品的風格以駢儷體美文爲主,兼收述懷的抒情文、平易的記録文、猥俗的滑稽文等多種多樣的作品。
通過這樣一部《本朝文粹》,可以通覽整個平安朝的漢文學世界。其中收録的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中國文學的影響。通過對《本朝文粹》的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起到的積極作用,還可以爲我們從文學的視角瞭解日本的社會文化、解讀日本的中國觀提供重要的參考。
《本朝文粹》初次刊刻本是寬永六年(1629)的木活字本,之後是在此基礎上的正保五年(1648)附有重校訓點在内的雕版刊本,並得以廣泛流傳。與其他古書相比,《本朝文粹》的古寫本數量衆多,由此可見本書在當時受重視的程度。其中,身延山久遠寺藏本被認爲是現存最善最古老的寫本。但是,除了身延系統的諸本以外,其他的古寫本却多爲殘缺本。
身延本是《日本文粹》傳本中優秀的古寫本,可以説是傳承至近世初期的所有完本的最古祖本,也可以説是《本朝文粹》現流布本的原本。身延本書寫於鐮倉時代建治二年(1276),由清原教隆加點,於昭和三十三年(1958)被指定爲重要文化財。清原教隆來自明經博士清原家,任鐮倉幕府將軍的侍講,對幕府的文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别是金澤文庫的創始者北條實時得到了教隆的言傳身教。教隆是鐮倉時代首屈一指的碩儒,爲衆多經書施以校點,王朝以來博士家的書籍通過金澤文庫得以傳承至今正是教隆的功勞。
三、 《本朝文粹》校訂本
身延本雖然是現存最善最古寫本,固然也避免不了有訛舛之處,但其誤字脱字遠遠少於近世初期的寫本。身延本的詳細訓點是由鐮倉時代的頭號鴻儒所加,與其他的鐮倉鈔本相比,各熟語詞章的音讀訓讀的差異以及細部的異同雖然多處存在,但是總體上,身延本展示了繼承王朝時代傳統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當代共通的訓讀方式。從對異訓的注記以及對日本漢文加以訓點這一意義上來説,也是國語學上的重要資料。教隆以及後人添加的與諸本的校對、音義、訓讀等注記内容也非常豐富。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瞭解與當時存在的諸本之間在文本上、訓讀上的異同。另外,行間眉上或紙背記載的音義、出典、人名、字句的略注等,也足以使我們推察出當時該書注解的情況,也爲該書的校勘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但是明治以後却鮮有使用身延本做底本來對《本朝文粹》進行校訂的。明治十九年(1886)田中參校訂的《校訂本朝文粹》(東京九春堂刊),是以正保五年刊本(1648)爲底本。此書對金澤本以及現已散佚的弘長本等進行校對,書中爲了閲讀理解方便而附加了返點和送假名。大正七年(1918)國書刊行會刊《正續本朝文粹》襲用了田中校本。大正十一年(1922)以田中校本爲底本的柿村重松著《本朝文粹注釋》(東京内外出版株式會社刊)有詳盡的注釋,又以對成語故事的出處進行準確詳實的考證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好評。昭和二年(1927)刊《校注日本文學大系》卷二十三《本朝文粹》沿襲了以上諸本。昭和十六年刊《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卷二十九下所收《本朝文粹》是以神宫文庫藏寬永六年(1629)刊古活字版爲底本,與十幾種古寫本、田中校本、柿村注釋、朝野群載等其他相關諸書進行校對的基礎上完成的校本,是校訂史上的一大飛躍,現在作爲最善本而被廣泛使用。但是,國史大系本功績雖大,也不乏疏漏之處,書中有對古寫本文字的誤讀以及未讀等現象。雖然也使用了身延本進行校對,但實際上進行對比發現,國史大系本並未真正參照了身延本。由此可見,作爲最善本本該作爲校本的底本來使用的身延本,在當時却幾乎没有受到重視。
到了近代,1964年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9,岩波書店,以下簡稱“舊大系本”),是以正保五年刊本(1648)爲底本,並與其他古寫本、田中校本、柿村注釋、《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本等進行了校訂。遺憾的是此書也未使用身延本爲底本,而且衹是抄出《本朝文粹》部分文章進行校訂。不過對抄出的文章附上了訓讀文,便於讀者閲讀這一點值得稱道。
1992年岩波書店再次出版了大曾根章介、金原理、後藤昭雄校注《本朝文粹》(《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27,以下簡稱“新大系本”),這次身延本的重要性終於得到重視,收録了以身延本爲底本的《本朝文粹》全文,爲每篇文章進行了統一編號,並標注了標點符號以及訓讀符號,篇末還附上與他本的校異。身延本缺失的卷一使用同系統的静嘉堂文庫藏本進行了補充。新大系《本朝文粹》還對部分文章進行了詳細的訓讀以及注釋,更加方便了讀者對文章的理解。新大系《本朝文粹》是迄今爲止對《本朝文粹》進行的最細緻的整理,對文章的統一編號方便了讀者查閲,對文章的訓讀以及注釋較舊大系本更爲準確,是目前《本朝文粹》文本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校本。
1999年勉誠出版發行了土井洋一、中尾真樹編著的《本朝文粹的研究》(校本篇·漢字索引篇上下,以下簡稱“土井本”)。該書對《本朝文粹》進行了較爲系統的研究。由校本篇和漢字索引篇組成。首先在校本篇中,在對散存各地的古寫本原本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整理出信賴性較高的校本,並附有校注。本書以最善本的身延山久遠寺本爲底本,並對其進行忠實的翻刻。在校本篇後附的解説中,對身延本以及其他古寫本分别進行了書志學角度的考察。另外,在漢字索引篇中,以單個漢字作爲檢索對象,並附有每個作者的作品編號表。土井本的校注較新大系本更爲詳盡,沿用了新大系本對作品的編號,並在此基礎上,標注了每篇作品的行數,每行字數與身延本保持了一致。
四、 新大系本與土井本的問題點
綜上所述,對《本朝文粹》的刊本進行的校訂,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在管見範圍内,迄今爲止以最善本身延山久遠寺藏本爲底本進行校訂的衹有新大系本和土井本。二者均參照其他各寫本對身延本進行了細緻的翻刻、校注或是對作品的訓讀以及注解,爲我們研究《本朝文粹》提供了便利,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但是二者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新大系本在對身延本進行翻刻的過程中,被認爲是後人補寫的部分並没有完全採用。對“弟—第”、“太—大”、“花—華”等通用字,並没有按照身延本原本面貌翻刻,而是都統一了字體,在校異中也没有提及。土井本在對通用字的處理上,雖然本着遵循身延本原本用字的原則,充分展示了身延本的原貌,但衹是對不同寫本中的文字進行了校異,並未考證文字使用的真僞。而且在對作品加注標點符號這一點上,有過度參照新大系本的傾向,其準確性還有待考察。
新大系本和土井本存在的問題大致可以歸納爲以下幾種: 文意理解上的錯誤、忽略原文修辭的錯誤、標點符號的使用錯誤等。下面就以具體例子來分析。



又如,《本朝文粹》卷十二,同是兼明親王的作品《髮落詞》中有如下一句,新大系本與土井本均將其加標點爲:“寧不見彼松柏。秋霜屢落,不改其緑。亦不見彼瓊玉。夜火三宿,無改其潔。”《髮落詞》是兼明親王在生病之後所作,文中描寫了自己生病之後,昔日如玄雲一般的頭髮,今日都變成了白雪。接下來就是此句:“我寧可不去看那松柏,即使秋霜屢屢降臨,也不改其原本的緑色。也不去看那瓊玉,即使受夜火多番光顧,也不改其原本的純潔。”用松柏以及瓊玉的不改其本色來與自己的頭髮由黑變白進行對比。而且松柏與瓊玉這兩句爲對句,屬並列關係。因此,正確的標點符號應該是這樣:“寧不見彼松柏,秋霜屢落,不改其緑。亦不見彼瓊玉,夜火三宿,無改其潔。”新大系本與土井本此處的錯誤標點,可以認爲也是忽略了對句這一功能所致。
由此可見,目前的校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問題,這與《本朝文粹》收録的作品數量多、内容繁雜、涉及領域廣、大部分作品還未被解讀有着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對《本朝文粹》收録的所有作品,包括標點符號在内的準確校訂將是我們今後要去解決完成的課題。對《本朝文粹》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是一項非常龐大的工程。不過近年來,已逐漸有後藤昭雄等研究者對《本朝文粹》部分作品内容進行解讀的研究書(如後藤昭雄《本朝文粹抄》一—四,勉誠出版,2006年,2009年,2014年,2015年)的出版,這爲我們進一步瞭解《本朝文粹》的作品内涵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也爲將來能夠做到對《本朝文粹》全文進行解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 結 語
《本朝文粹》收録了平安時代200餘年間漢詩文的精華,作者多爲當時漢文學繁榮期的代表人物。作品風格多樣,通過一部《本朝文粹》,我們可以通覽整個平安朝的漢文學世界。編者藤原明衡是當時漢文學的佼佼者。在《本朝文粹》編撰的平安後期,漢學雖有逐漸衰退的趨勢,但漢學是在朝爲官之人必備的學識素養,大到詔敕政務,小到私用日記書簡,均以漢文來書寫。但當時的漢文並不滿足於達意這一實用性,而是注重使用出典以及對句這一技巧的四六駢儷文,因此就導致人們迫切需要作詩作文用的參考書來模仿使用。而《本朝文粹》的編撰,不僅注重在文學美學意義上獲得評價,而且網羅當時各種日常實務文例的意圖也非常明顯,這正順應了當時社會的形勢需求,因此對之後的日本文學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説《本朝文粹》是日本漢文學的基本文獻,作爲平安時代的史料也擁有着不可或缺的價值。而對《本朝文粹》最完整的原始資料身延山久遠寺藏寫本進行研究,更是《本朝文粹》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環。
日本漢文學作品是域外漢文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特有的課題。而其寫本研究屬日本文學研究的難點,屬當下前沿課題,爲中日學術界所廣泛關注。由於寫本的脆弱性和保存的難度,今天它們正處於日漸消失的危機之中。加强對這些面臨散逸危險的資料進行搜集整理,就顯得尤爲重要,是中日學者迫在眉睫的任務。
我國學者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獻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和成果,就可以爲解讀域外寫本提供參考,而這些域外寫本的信息,也會爲敦煌以及其他國内寫本的整理擴大視野,提供新的參考材料。將敦煌寫卷研究的經驗,運用到《本朝文粹》的寫本研究中,能夠多視角地對文本進行解讀,並從新的角度闡釋中國文學對域外文學所産生的影響,進一步認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由於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期待着能有更多的中日學者來共同完成。
——《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李叔同卷:印藏》评介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