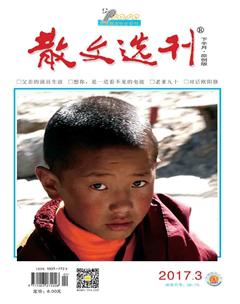李梅岭的仰望
白杨
如若说李梅岭仅是余干的一只小手掌,那也必然是掌背,而且绝对是掌背食指的骨结处———于百万多人口、三千多平方公里的泱泱滨湖大县,她394米的纯粹海拔,足以构成余干的绝对地表高度———让百万余人仰望的一种高度!
那次北上被李梅岭意外截留,缘于白君。她在这个仅18平方公里的林场任职。那个距县城空间距离四十公里、时间距离四十分钟的弹丸之地,垂臨余干与东乡之界,却于她有着异常的眷恋、不离不弃,宛如她二十年前初恋的纯醇心事!她手机里真诚地邀说:“来李梅岭看我吧!”
于是,一阵风就把我吹去了李梅岭!
那个数亩见方的院场,几栋平常稀松的楼屋,一顿简单搭配的午餐,片刻仓促匆忙的时光,自然没能带给我更多触动。然后就是去李梅岭———风自然是吹不上去的,是白君的一个同事开一辆防火面包车,将我们塞内驮载而上。
没有阳光,薄雾低垂,寒风冷冽,时光凝重。去李梅岭的路上,因为静谧而让一切的声响变得真切得有些夸张。车子摇摇晃晃,在迂回狭窄的水泥路上穿行,估摸十几分钟,水泥路的尽头,一山突兀而起,超然而立———白君说,这就是李梅岭了!
眼前的李梅岭,两山夹翠,一路蜿蜒而上,却是比“之”字还急的弯度、近六十度坡度的山土路,满是雨水冲刷出鸿沟、重轮辗压出车辙的山土路,俗世之外、尘埃之上的山土路。还未从一路的惊悚和坐车的庆幸中回过神来,车子如醉酒般已跌撞而上,低速挡的机器轰鸣,与几许余干口音和几声爽朗笑声浑然天成,自成默契,惊起几只野鸟从林中飞向天宇,像哪个乡下顽童洒出的一把石子———而我所见的李梅岭的林,阔叶稀疏铺展,红叶纷纭相见,勾勒出一幅斑斑驳驳的冬林写意图。
白君说,白云峰寺立世千年,享誉千年,香火千年,就因其灵而深得左近乡民所信,甚至南昌、东乡之辈也朝拜而来,是以,每每庙会之期,总是人影如潮、人声如鼎,也是以有了而今的翻修扩建之举。我复而伫立,此时有人撞响大钟,钟声凝重而悠远,久久不散,惊起一对苍鹰在天空盘旋俯视,俯视李梅岭,也俯视我们;亦如李梅岭俯视干越大地,也俯视干越苍生!
他们自是在梵音檀香中朝拜祈愿,将自己的心事无尽倾吐,将自己的渴求无尽想象,而我,则立李梅岭峰之巅、白云峰寺之侧,任山风猎猎,吹皱我衣襟,也吹皱内心的波纹———或许,白云峰寺的存在,才让李梅岭真正有了仰望的高度和铭记的分量;而在祈祷之后、许愿过后,又有多少人不选择将这李梅岭所遗忘?站在李梅岭之巅远眺,山川如脊层叠远去,流云苍茫薄雾织缦,城镇星散村庄静默,一切都慢了下来、静了下来、淡了下来,一如返朴后的缱绻心事。
下山时,车被开得颠簸起伏、腾挪跳跃,让我内心忐忑、身心激荡。复回头仰望,李梅岭静默如旧、矗立如昔,我未曾留下些什么,也未曾带走些什么?的确,仰望,总是目光的仰望;而遗忘,更多是心灵的遗忘,这我知道!目光的仰望总会被峰回路转所隔,被时光荏苒所阻,被利益欲望所淡;而遗忘,更是每每发乎心间,不需片刻,不经须臾———我只能在他消瘦孤独的身影消逝之前,再复仰望,仰望那尖寂寞的苍茫、那杵静默的荒凉、那些游碎的时光,哪怕不久后随俗世的尘埃再复遗忘!
这遗忘,或许是天注定的。正如刘卿所诗:“明日天涯去,相思不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