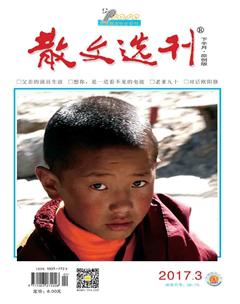桑葚
金国泉

我现在才知道桑葚竟然是水果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且昨天看见爱人从超市买回来包装精美的一盒桑葚,我才恍然大悟,桑葚竟然也很有贵族气──
我一直认为水果这个词很有贵族气,而桑葚不能称为水果。我甚至野蛮地认为桃子也不是水果。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是野桃树,每到夏天便毛茸茸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水果应该是难以买到的,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桑葚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它既无如水果一般润泽的果皮,也无坚实的果核(这个结论我后来才知道是错误的,桑葚是有核的,只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也不怎么甜蜜,酸溜溜的,更上不了桌面,很下里巴人。那时每到春夏之交,树荫下,有时是喜鹊,有时是麻雀,喙食时不小心掉下来后,我们就如同喜鹊、麻雀们一样争着抢着捡拾的桑葚,却可以与苹果之类的水果相提并论,让我真是有些感叹。
柏拉图的《斐多》中有一句话,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美本身出现于它之上或为它所“分有”。柏拉图的“分有”说让我想到,是不是水果被桑葚部分“分有”了?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柏拉图还有另一句名言:认识就是回忆。这句话对我触动更大。因为我坚信许多东西是因为回忆而美好。这自然包含了我对桑葚等果实的认识的改变。但实际上我是先认识了桑葚,然后才认识了“水果”,从这方面看又与柏氏理论相悖。也许世上的事本就矛盾。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鳩兮,无食桑葚。”《诗经·氓》这样描述桑葚时,虽巧妙地描述着男女爱情,但也不经意地勾勒出了一幅斑鸠争食桑葚的田园美景。桑葚之盛也就溢于言表了,且与我儿时景象几近一致。
桑葚又名桑果,既可入食,又可入药,中医认为其味甘酸,性微寒,入心、肝、肾经,为滋补强壮、养心益智佳果,具有补血滋阴、生津止渴、润肠燥等功效。这是我看见爱人买了桑葚后,“百度”搜索到的结果。在这之前我对桑葚的这些功能一无所知。我想许多人可能也与我一样,无知且无奈。但我总觉得这多少有点放大镜或显微镜的味道,小得不能再小的一颗桑葚,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功能,几乎成了一粒精心制造出来的药丸!现代人似乎很热衷于制造功能,喜欢将功能一再叠加,也一再附加,让许多美丽的阳光照在它上面,几乎是“万千宠爱于一身”。比如一部手机,本来是用于通信的工具,却硬生生地使它成具有阅读、看新闻、游戏、微信、QQ、购物等等功能,几乎无所不能,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大世界。我可能真的是“out”了,我的手机一般只启用电话及短信两个功能,就像我只知道桑葚能偶尔填一下肚子,解一下渴一样简单。我就像贾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也是我之所以对现实世界感到无奈的原因之一。
桑葚在我的家乡叫桑苞。在我看来很形象化,真有点像花朵含苞欲放的感觉:桑葚挂在枝头的形状很优美,那紫嘟嘟、圆润润的桑苞,挂在桑树的枝头,令谁都垂涎欲滴。虽酸溜溜,但仍然能为我们解馋解渴。这看起来的矛盾和我们乡下人有肉就把白菜放在一边,没有肉就将白菜端上一样———桑葚既是白菜也是肉,只是它韬光养晦不让我们知道它那么有营养。
可桑葚韬什么光,养什么晦呢?
桑葚成熟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端午节过后。记得我那时候由于家庭管教甚严,既爬不上树,也下不了湖。我的童年因而少了许多乐趣。以至于现在许多人对于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却不会游泳、不会爬树匪夷所思。我自己也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那么害怕我上树与下湖。现在的家长似乎仍然没有几十年前我父亲的安全感那么强烈。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被放牧着、畅快淋漓地玩耍,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到树梢、钻到湖心而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我的上树下湖的功能因而“被迫”终生萎缩。我只能以他们之乐为乐。这种“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像树上掉下来的桑葚──我一直想,那帮着我们度过了一个饥饿,但仍然很美的童年的桑葚,却没留给我一点好印象,可能就是因为我只是吃着我的小伙伴们扔下来或者鸟儿们争抢时掉下来的桑葚的缘故。这是桑葚的失败还是我的失败?
我小时候胆子非常小,又非常惧怕父亲──我想可能二者是相通的。当然,那时的我没有遗憾的感觉,除了有些许片刻的烦恼之外,很快便抛之脑后与伙伴们打成一片。或帮他们看衣服,或帮他们拿家什,虽不畅快淋漓,却也自得其乐。我看着他们玩,这也无形中加重了我在他们中的分量,因为有没有被大人们发现全靠我说了算。有时候我一句谎话会吓得他们光着身子屁滚尿流。这自然也就弥补了我不能与他们同乐的不足。
一般上到树最顶端的,或钻到湖最深处的总是我的堂兄泉伢。泉伢大我一岁多,由于年龄相仿,因而很少叫他哥哥。他也从来没有感到我有什么不妥或失礼的地方,叫他时他总是乐呵呵的。泉伢不仅上树下湖是行家,捕鱼捉虾弄黄鳝什么的也无一不精,就连筢柴火也比我胜上好几筹。但就是这样一个能手,几十年来他也仍然没有富裕,仍如过去一样很穷。用家乡的一句俗语来说叫作“用锅铲都铲不起”。为了能延续单传的香火,几次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他也因此几乎倾家荡产。他在外务工,干的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体力活,挣的血汗辛苦钱。虽然他放弃了传宗接代这个难圆之梦,却将这个梦转化成一肚子的怨气,酗酒、赌博使他原本来之不易且不多的血汗钱流水一样白白流走。没有钱,甚至有时连春节也没有回来陪陪老母。二婶在家望眼欲穿,堂嫂带着三个孩子终日守着一亩三分地发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去年却溘然西去,丢下几个儿女及妻子,让谁都会心生悲悯。
生命总是如此吗?泉伢展示的是什么,隐去的、不让我们看清的又是什么?站在这片过去争抢桑葚的树下,看着头顶上满枝满树的桑葚,束手无策的我真的就有了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所写的“最怕听的,就是滴答的坠枣之声”的感觉。
桑葚坠落之声,在夏天,但我听来如听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