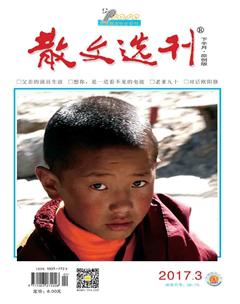二胡独奏
尹其超

那年重阳节,艳阳高照。局里组织退休老干部到地雷战故乡参观。上车,和陈局坐一排。“九月里九重阳,收呀收秋忙,谷子糜子收上场,红个旦旦的太阳暖堂堂……”听着车里扩音器放送的陕北民歌,正想和陈局长聊聊这首二胡伴奏的歌曲。一转头,见他面色憔悴,赶忙改口表示关心:“最近身体怎么样?”陈局说:“自从去年老母亲去世,我就一蹶不振。”“老母多大年纪?”“阴历98岁,阳历99了。”“这是喜丧。”陈局感叹地说:“人不管多大年纪还得有个妈啊!我都70岁了,就觉得谁也比不了娘亲。”
说着,陈局动起情来———
“虽然母亲病中对我们兄弟姊妹说过:‘我死了,都不用哭,你们都尽孝了,我很满足。可真到了她临终时刻,我觉得自己将失去所有的幸福和快乐。母亲一生辛劳,但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耳朵不灵,我怕跟她说话,她听不清楚,就想让她在最后时刻听着音乐,减少痛苦。
“我之所以想起拉二胡,因为我听过‘莫扎特效应的传说:有人把20个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听莫扎特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一组什么也不听,然后回到一起回答问题。听音乐的学生普遍比没听音乐的学生回答问题快且准确,说明音乐能触发神智。一位博士观察水的表情。他发现,一个人面对一盆水说话,你对水客气,它结晶体的花纹漂亮,相反,你对水粗暴,它的结晶体紊乱难看。我想,水在人体中占65%,我用二胡奏出优美的音乐给母亲听,她体内水的结晶体就漂亮,老妈就一定会舒服些。让老妈舒舒服服地走,是我最大的心愿。”
情感的共鸣真是没有时空的界限。一路上,陈局的诉说如弦索之响,丝丝缕缕,深邃动人。
夜深了。在老母亲弥留之际,我执意独自守在老人身边,一直在为母亲拉二胡送她最后一程。二胡曲一首接一首地拉着,我看到老妈原来痉挛的脸松弛了,面容更慈祥,她一定听到了我的呼唤。
我拉着《纺棉花》乐曲,眼前现出老妈操劳的身影。她一生用怎样的毅力和瘦削的肩膀扛起培养我兄弟姐妹5个人的重担?因为父亲在外边谋生,下地干活主要靠母亲。我有一个姐姐,1岁夭折,有一个弟弟5岁拉痢疾去世。若不是家境困难,怎么能让小小的生命刚刚诞生就离开人世?妈妈受此打击,已够深重,可就在她39岁时,父亲又生病,离她而去。天塌了!一家人只能靠妈妈下地干活维持生计。抚养年幼的孩子,她瘦弱的身躯拉着锄杆,她细细的臂膀抡着镢头,农活是一个男人都难以胜任的重体力劳动,一个小脚女人把农活全包下来,艰苦劳累可想而知。晚上还要缝缝补补,为孩子们的吃饭穿衣操劳。母亲虽然没有纺过棉花,可她心灵手巧,靠绣花副业补贴家用。每当领回“满工扣锁”原料和图纸后,将其固定在有4个支腿、近两米见方的木撑上,而后开始照图数扣。母亲绣花是很讲究的,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戴上自制的白色套袖,从一边开始,绣花针在密密匝匝的网格中,时而穿、挑、结,时而上、下、飞,在空中画出美丽的弧线。我拉着二胡,眼前一会儿出现波纹或雪花状的图案;一会儿伸展出漂亮的荷叶、大朵的莲花,针线匀密,网扣洁净,大小对称的菱形从一角向整个撑子绵延……绣花费工夫,也累人,为了赶工,母亲总是绣很久才抻抻腰,舒展一下酸疼的肩背,揉揉干涩的眼睛。我拉到曲调高昂时,多么盼望老妈还能“绣呀绣呀绣呀绣,一天能绣出百朵花!”我拉着二胡,揉着琴弦,心在颤抖,眼前浮现妈妈眉头未解的结,看到妈妈灯下劳累的疲惫。
我拉到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时,眼前出现冰雪覆盖着的村边小河、小河没有桥,母亲背着从山上搂来的松毛,颤颤巍巍地踏上随时有可能塌陷的薄冰。一次,妈妈摔倒在冰面上,脚脖子立即红肿起来,可负重的老妈艰难地爬起来一瘸一拐背着网包挪动,她老人家比拉着《三套车》那匹可怜的老马还要吃力,蹒跚的脚步沿着“今后苦难在等着它”的冰河踯躅前行……夜,冷月洒满大地,二胡曲旋律低回悲婉。我守着妈妈,凄凄的肃穆更衬托出屋里的寂静。母亲就要离开我了,咫尺天涯,情何以堪?人生一世,就好比是一次搭车旅行,要经历无数次上车、下车;时常有事故发生;有时是意外惊喜;有时却是刻骨铭心的悲伤……降生人世,就坐上了生命列车。总以为最先见到的那两个人———父母,会在人生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遗憾他们会在某一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孤独无助。他们的爱,他们的情,他们不可替代的陪伴,再也无从寻找。
老妈39岁守寡,一直住在威海长峰,离威海市15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吻干我脸上的泪花,温暖我那幼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想起我母亲在小山村度过的一生,情不自禁地拉起了《妈妈的吻》。这歌词表达了我的心愿,希望能吻干妈妈脸上的泪花,温暖妈妈操碎的心。生活多么困难,妈妈也设法供我们上学,我考上离家15里地的初中,住校要缴5元钱,我缴不起,就走读。一天,放学时下起大雨,山水冲下来,小路泥泞,我披上一块油布,迎着风,顶着雨,也得往家走,怕妈妈惦记。走不动,天又很快黑了,就在我怕迷路的时候,一个闪电劈了过来,借着光亮,我看到前方一个人影撑着一把破雨伞艰难地走向我,我抹去脸上的雨水,一眼认出是妈妈来接我!她已经冒雨走了十几里地!浑身湿透的妈妈擦干我流下的眼泪,扯住我冰凉的小手……此刻,我拉着二胡曲《妈妈的吻》,早已泪流满面。
好容易熬到初中毕业,无论如何母亲也不让我再考高中了,家里供不起。正巧烟台艺校到威海招生。说不用缴学费,还管吃住。我从小跟我哥练习了几天二胡。那是自己做的二胡,找个筒子,绷上蛤蟆皮,没钢弦就用丝弦,拉好弓子,自做自拉,算是学会了一门“手艺”。由于对音乐的爱好,结果还真被艺校录取。老娘说:“真是么(mo)人么(mo)命,你飞出了穷山沟?”可我上艺校也给家里带来灾难。那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3月份开学,到7月份才算有正式学籍。所以,新生还没有粮食指标,要自己带粮票。全家当时一共有80斤苞米,妈给我兑换了40斤粮票,到了学校,按当时学生定量一个月供应31斤粮食。我带的粮票只够一个月的。学校要收下个月的粮票时,我写信向家里要,我的老舅给我来信,把我臭骂了一通:“你有没有良心?你把粮票都拿走了,你妈在家过的什么日子?你还要粮票!你想要你妈的老命?”我没敢再向家里要粮票,可学校总务处的教师说:“你再不缴粮票,就开除学籍。”当时真是进退两难,好容易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学校,因缴不上粮票就放弃学业,于心不甘。我站在学校院子里,孤独无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跑到海边声嘶力竭地呼喊。最后还是大海回应我一个折中的念头:找老师商量,能不能寅吃卯粮,一个月一个月倒,把以后放寒暑假该发给我的粮票先借出来用?死缠硬磨,苦苦哀求,终于,博得老师的同情,就这样挨到了暑假。我上艺校,好了自己,亏待了老母,她在家吃糠咽菜,艰难度日。人世间的真情和爱,没有比母爱更伟大更真实更无私的了。我不记得年幼时妈妈有没有心思吻我,但我确信妈妈把心留在我身上,妈妈把情洒我心中,妈妈把爱注入我的细胞,妈妈把青春延伸在我的生命里!她的银丝换上我的乌发,她的衰老换来了我的青春……我拉着《妈妈的吻》,沉甸甸、飘忽忽的旋律,深深浅浅地诉说着我的心迹:让乐曲抚慰她老人家疲乏的心灵,陪伴妈妈灵魂的再生。虽然,我也老了,可是,我不想远离更老的母亲;虽然,拉二胡,尽孝心,可是,我知道,不管我用何种方法都难以报答母爱之恩。
《常回家看看》是我们威海人的作品,我曾给母亲拉唱过这首歌曲,她喜欢得不得了。可我这次拉起“回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我的心情从天堂彻底坠落到深渊。回家,每逢回家,不是向老母道出游子的哀愁、向家人述说思乡的心切,而主要是感受有老母亲在的温暖。今天妈妈就要离我而去?我为再不能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而惋惜,为不能再听妈妈的唠叨后悔不已。其实,妈妈并不唠叨,她具有一种非常乐观明亮的性格。我很少记得母亲对我有过什么责备和训斥,见她动怒,更是非常稀罕的事。母亲对儿子的种种期待和要求,我基本上是从她对我的各种鼓励以及在向左邻右舍夸耀我的语音中分解出来的。母亲有几个儿媳,却从来没有在人前说过她们一个“不”字。拉着《常回家看看》,我想起当年给母亲添堵的一次“回家”。我跟夫人很少争吵,一次激战也是为老妈,几乎动了手。我不能容忍任何人说老娘的“不是”,气得回了老家。老妈听说夫妻吵架,二话不说,抡起擀面杖就撵我回去:“你长本事了?还想打老婆?赶快回去赔礼道歉!”她不依不饶,我好歹央求才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老妈一大早就起床了。那时我还在睡梦中。她在做饭,动作那么轻,生怕吵醒我。可我还是醒来了,躺在床上听到擀饺子皮的均匀节奏……我起床后见老妈正在包蒸饺。我说:“不用這么麻烦,我吃什么都行。”老妈说:“不是为你包的,这是让你捎给儿媳妇。”老妈就是这样,明明知道媳妇说了她的坏话,还大清早费时把力包媳妇喜欢的威海名吃,我看着满头白发的老妈那么认真地灌浆、和馅、捏褶……心酸的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我于母亲,是愧疚的。让母亲高兴的事,太少太少;让母亲烦忧的事,太多太多。向母亲索取的爱太浓太浓,而奉献给母亲的心意又太薄太轻……
弥留之际,她一言不发,眼泪不断从眼角沁出。老母亲就要上路了,我就像徘徊在迷离草原上的孤马,惊惶失措,情不自禁地拉着《病中吟》、拉着《送别》……凡是我能拉的二胡曲都为母亲一个人独奏。
我不知道是不是二胡曲萌动的气息弥漫到了母亲的躯体,母亲身高1.7米,常年下地干活,人都缩了,腰也罗锅了,可她在最后时刻挺直了腰板,恢复了身高,平平地躺在床上,静谧、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