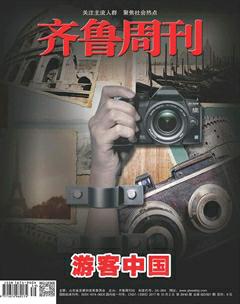中国云游史
米绪


“旅行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地球生物的本性。”
虽然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但中国人的远游史没有被路引和闭关锁国所管控。“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在这一点上,古今大同。
李太白仗剑天涯,诗情与酒意不相上下。乾隆帝六下江南,笔墨不及緋闻传播率更高。
“旅游”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梁朝诗人沈约就写过“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这个旅游,和今日通常意义上的旅游相近。而最早的“旅”和“游”却相对独立。旅,多义,指的是因为经商或其他原因离开定居地,强调生活空间的变化。而“游”则侧重于动态的位移,强调过程,如游玩、交游等等。结合二者之意,古人的“旅游”则要久远得多,也更富有想象空间和诗情画意。
美好始终在远方
关于中国最早的旅游达人,有人认为是大禹。其人疏浚九江十八河,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但以他几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估计看遍万水千山,也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感觉更像是苦哈哈的出差,远不如周穆王的旅游精神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他极富传奇色彩,被后人誉为自驾游的先驱。据说他坐着八匹马拉的车子,沿着渭水东进,到了盟津,渡过黄河,沿太行山西麓间北挺进,直达阴山脚下,转而长途西行,到了昆仑山,又向西走了几千里,到达了西王母之国。据史书记载,周穆王自镐京至西王母之邦,行程共1.21万里。他和西王母宴会酬答,留下了一段佳话,更是为后人所羡慕。所以,现代人更喜欢在精神上在现实层面效法周穆王,跋涉千里、看遍山水,得遇知己,获歌“祝君长寿,愿君再来”。
在《穆天子传》之后,巡游就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式旅游。嬴政称帝10年,巡游5次,在“威服四海”之外,也增加了游玩环节。为了让巡游更加方便,他还在全国修建了“驰道”,想来就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他在泰山举办的“封禅大典”,直接将泰山神化,让泰山作为朝野旅游胜地火了几千年。之后的汉武帝,在位50多年,巡游30多次。而其后的隋炀帝出于对秦皇汉武的倾慕,巡游成瘾,“靡有定居”,在位十二年,居京不足一年,而到处巡游却占了十一年。他曾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后人甚至将开凿大运河这样的大事看作是他方便出游的大手笔。而之后的乾隆帝“六下江南”,到处题字、写诗以及遭遇“夏雨荷”,更是在正史和外传中广为流传。
在那样交通不便的年代,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是帝王或者王侯将相的特权。徐福和郑和扬帆出海,张骞则两次出使西域,九死一生,打通了“丝绸之路”。
而司马迁、徐霞客、李时珍虽不奉皇命,却自奉天命,他们的学术游之高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李时珍,到各地搜集标本,才成中医巨著《本草纲目》。司马迁在父亲的指点下,放下手中的经典,足迹遍布当时西汉版图疆域。他20岁出游,“纵观山川形势,考察风光、访问古迹,采集传说”,终成《史记》。而徐霞客也从20多岁出游,30多年遍及16(一说19个)省山水。据说在徐霞客的游历中,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第四次出游时他湘江遇盗跳水脱险。即便两手空空,他也不肯回头,拿了身上的衣物换粮食坚持,还留下了随地死随地埋的豪言。他每天跋山涉水,晚上还要挑灯著书,先后写了2000多万字的地理考察记录,仅存的40万字《徐霞客游记》不过五十分之一。
和今人旅游最为接近的则是古代文人们推崇的“山水游”。李白同学一不高兴就要“散发弄扁舟”,高兴了也“一生好入名山游”。刘伶虽贤,乘鹿车携酒出游,“死便埋我”。他们游出了境界、游出了水平,天涯知己,山水清音。最为超脱的是王子猷,“夜雪初霁,月色清朗,乘小船诣友,经宿方至门前,却兴尽而,何必相见?”
山水、知己与远方,说白了,都是手段,让我们看见自己、证明自己。每个人走过的万水千山、经历的坎坷波折,都是风景,都是试炼。所以,孙悟空筋斗云就能干完的事儿,要翻山越岭、除妖降魔才算数。山水何曾藏妖怪,有时不过是降服心魔的背景而已。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可以改换内心的天地,甚至真实的世界。
攻略3000年
每次出游,都会有攻略若干满屏。古人的攻略也不遑多让。某种意义上“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就是李白给后人写的攻略。而雇个馄饨挑子进行近郊游,就是沈复告诉后人的绝招。散文家张岱在《游山小启》里详细写了旅游所要准备的东西,比如:小船、坐毡、茶点、杯盏、筷子、香炉、柴火、米饭,簋、壶、小菜。还有的雅人在器具之外另带歌姬乐人,所以今人带个露营神器放点音乐助兴也没什么牛的,人家古人自带的是乐队。而谢安出行随身带着一两百个跟班的,地方官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强盗来了,绝对不是演义。
古人也有“行衣”,也有“路菜”,都是旅游文化的绝妙注脚,也成为这个民族文明的一部分。《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宝玉去探望黛玉,穿了一双棠木屐。这本来是谢灵运发明的登山鞋,后人却渐渐当做雨鞋。我们现在出去玩,喜欢背个登山包,古人也有“游具”,比如提盒和提炉。提盒里有多个格子,可装几个碟子筷子壶杯酒菜等物,还凿有棱条以透气; “提炉”也很实用,有铜炉固定着可煮茶的茶壶、可炖汤温酒的锅。这可比今人的焖烧杯豪华多了。
最经典的背包应该是玄奘西游的标配。在《大唐玄奘》里,黄晓明扮演玄奘法师就搞了一个这样的造型。高过头顶,上面插一把伞,前面挂一盏灯。它的名字叫经箧”或“经笈”,是盛经书用的。当然也可以装别的。实际上,这个道具可不是僧人专用,在住宿不便的古代,没有马匹或挑担子的徒弟跟随,书生或其他行业者有也会使用。至少自带行李比较环保,不用担心五星级宾馆是否洗了床单的问题。
对于古人而言,这些设备虽然重要,但远不及诗情和笔墨的排位。在这一点上,他们虽然没有手机和电脑,但写作勤奋,遇到有庙宇和楼阁的地方,就和今人找到WIFI一样高兴,赶紧上传诗文。如果一直没网,就效法李贺,偶有多得,即投入随行的锦囊中。所以,最怕的就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只好凭君传语报平安。
“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对中国文人而言,在路上,是一种人生理想状态,辞亲远游也好,被贬远谪也罢,凄风苦雨、好山好水都是好诗情,都孕育千古绝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旅馆无良伴,凝情悄自然”,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他们的朋友圈文学,我们今天依然在效仿。带着这样的诗情上路,人人都在云端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