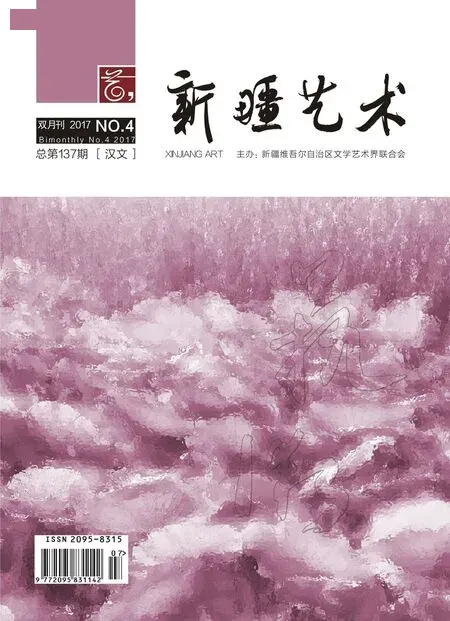无声的喧嚣
——捍卫世界之重的莫言
□ 王献玥
莫言的小说通常给人一种紧凑的节奏感和巨大的信息量。进一步深入小说的故事情节,又能够让人感受到莫言的叙事伦理。莫言将残酷、痛苦、暴力、粗鄙等毫无保留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是在用这种沉重的叙事方式承载生命真实的重量,给人以伦理的冲击,叩击人的灵魂。本文从哑巴、沉默者、失语者和内心自白者四个部分入手,探讨这些人物所表现的莫言作品的“无声的喧嚣”,在无声和喧嚣中寻找生命的沉重,进而探究莫言作品所承载的人性之重。

“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鬃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①这是莫言在一次访谈时说的一段话。“鲸鱼”、“深海”、“孤独”、“沉重”、“波浪翻滚”、“血水浩荡”都让人感受到一种重量,而“呼吸”、“交配”、“生产”等又将这种重量上升到生命的高度。那些生长在土地上的生命的真实生存状态是带有大地的重量的,对这些生命的关注,使莫言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带有着一种生命的重量,表达着他的叙事伦理。“莫言的讲述激起了我们的伦理反应,我们由此感觉,在我们的世界里,生命依然是一个破败的存在,而这种挫伤感,会唤醒我们对一种可能生活的想象,对一种人性光辉的向往。”②莫言善于在客观的叙事中注入一种伦理叙事,让读者在悄无声息的转换中感受到一种伦理冲击。他用冷静辛辣的笔调刻画着生命的苦难遭际,将一种不堪的生命破败景象无情地抛到读者面前,让读者从想象的美好中警醒,正视这个真实而又残酷的世界,正视人的生命之重量。生命越是破败,作者的叙述笔调越是冷静,我们的挫伤感便越强烈,对生命的本质便看得越透彻,对人性的思考便越深入。这种精彩的反差叙事正是被莫言运用到对“无声的世界”的书写中,通过对特殊生命体的描写,向读者灌输着“无声胜有声”的沉重感。
哑巴
莫言的小说中有很多哑巴。哑巴是一个沉默无声的存在,他们不能说话,表达自己的方式只有肢体语言和写字。这种缺少了对话描写的人物通常在小说中较难把握,但莫言所擅长的似乎恰恰是这样的描写。于是,哑巴在莫言的笔下充满了生命活力。他们根植乡土,时而粗鲁莽撞、时而安静可爱、时而勇敢无畏、时而善良感性。在莫言笔下,哑巴承载的是命运悲苦下的生命重量,他们承受着更多的苦难,拥有比其他人更有重量的人生。因为那些有缺陷的身体挡不住内心的澎湃,无声的命运安排挡不住复杂多样的人生选择。
“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扦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③《红高粱》中,哑巴一出场便带着沉重的生命底色。在“哑”这一天生的生理缺陷之外,“在高粱地里吃过‘扦饼’”,这生于农村的身份认定给哑巴蒙上了第一层沉重的生命底色。莫言没有过多地介绍哑巴的生活条件,但这根植农村的角色本身就带有着农村广袤土地的重量。接着,“草莽英雄”又赋予了哑巴第二层沉重的生命底色,那是国家民族的危难现实所带来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双重沉重让《红高粱》中的哑巴一开始便成为了苦难的化身。然而这沉重并未到此结束,比苦难更沉重的是死亡,而牺牲大抵是最沉重的一种死亡吧。“这时,后边那辆车上的鬼子把机枪压低,打出了不知多少发子弹,爷爷的队员像木桩一样倒在鬼子的尸体上。哑巴一屁股坐在汽车顶棚上,胸膛上有几股血蹿出来。”④那个在处决余大牙时会犹豫的温情感性的哑巴;那个在杀鬼子时奋不顾身、勇猛无畏的哑巴;那个在危急时刻把“我”父亲和“我”奶奶拉下河堤的善良勇敢的哑巴,最终躲不过牺牲的命运安排。苦难是哑巴一生的主题:一出生便面临的苦难、后来作为危难民族一份子所面临的苦难以及最后杀鬼子时中弹牺牲的苦难构成了哑巴的一生。莫言没有写哑巴小时候的家庭环境,也没有写哑巴的父母,更没有提及他是否有妻子儿女,连对哑巴身体上的残疾的描写都一笔带过。但这冷静简单的笔调却胜过千言万语。
如果说《红高粱》中哑巴的生命重量更多地来源于外在的生存环境,那么《白狗秋千架》中哑巴丈夫的生命重量则更多地来源于“哑巴”这种身份本身。他也生在农村,但没有那么多的民族、生存负担,也没有《红高粱》中的哑巴英雄那样勇敢、高尚,他只是过着普普通通的哑巴生活。然而,当一切外在的沉重设定都被除去后,他赤裸裸的普通生活依然让人感受到一种沉重,有时甚至比哑巴英雄的生命重量更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不得不让人将注意力转移到生命本身。刚见到“我”时,哑巴是粗鲁莽撞的,显示出一种轻蔑和敌意,在暖姑介绍后,哑巴的态度极度转变,变得十分热情友好,有巴结讨好之意。这种强烈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哑巴简单淳朴的性格,更暴露了哑巴的自卑心理。因为自卑,所以偏激,而这自卑与偏激都是因为哑巴这个特殊的身份。哑巴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份,“哑”的命运是他无法逃脱的,而这又决定着他后天的遭际。“独眼嫁哑巴,弯刀对着瓢切菜,按说也并不委屈着哪一个”⑤,哑巴面对的无疑是正常人的歧视与冷遇。如果说暖姑因为后天的事故变成独眼而不得不承受生活之苦的话,那哑巴则是毫无选择地从一出生就注定承受这苦痛。暖姑可怜,哑巴更可怜。没有家仇国恨的苦难环境,生命本身却更加沉重,这何尝不是作者在引导我们关注苦难生命本身。

莫言先生
沉默者
莫言小说中有另外一类人物虽然不是哑巴,但却极少说话。他们是广袤土地上的沉默者,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流涌动。他们有着敏锐的感觉,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是这样,《枯河》中的小虎也是这样。他们用无声喧嚣展现着世界的残酷、人性的沉重。
“姑娘还悄悄地问小石匠黑孩是不是哑巴。小石匠说绝对不是,这孩子可灵性哩,他四五岁时说起话来就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嘣咯嘣脆。可是后来,话越来越少,动不动就像尊小石像一样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寻思着什么。你看看他那双眼睛吧,黑洞洞的,一眼看不到底。”透过那黑洞洞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黑孩紧闭的心门。孩子本该是天真无邪、活泼好动的,而莫言笔下的黑孩却如此与众不同。从四五岁开始,黑孩便沉默不语了,无人能猜透他的心思。对于聪明的黑孩,这是有意识的沉默不语,也是故意的不让人猜透。他把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埋藏在心里,这无疑是一种对世界的不信任、一种对自我的保护。“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⑥黑孩的出场是这样一段让人心生怜惜的描写。季节已经是秋天,黑孩的穿著竟如此单薄,疤点竟布满整个小腿,这是一个有怎样遭际的孩子?“‘黑孩儿,你这小狗日的还活着?’队长看着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⑦原来,这是一个该去见阎王的孩子,黑孩能活到现在已然是个奇迹。这样悲苦却如此坚强的孩子,其平静的表面下,一定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极其敏锐的内心感触,生活的苦难可以让他变得沉默,但不能让他停止内心的渴望。当黑孩不顾一切去寻找那夜他看到的金色红萝卜时,他一定是赋予了那红萝卜神奇的想象。那金色的红萝卜或许代表着人类的一切欲望,吃的欲望、爱的欲望、占有的欲望等等,而这些,都只在黑孩眼前划过,稍纵即逝,无论怎样苦苦寻找也始终毫无结果。黑孩这无声的喧嚣背后承载的是他无爱的悲苦童年,也是他超乎常人的顽强生命力,是坠入大地的生的沉重。
如果说黑孩是对世界有认知的沉默者,那么小虎则是对世界无认知的沉默者。
“他总是迷迷瞪瞪的,村里人都说他少个心眼。”⑧小虎不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孩子,他总是晕晕乎乎的,认不清楚这个世界。他从树上掉下来砸到小珍子,小珍子危在旦夕,可他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世界里只有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却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原因和联系。人们都说傻子是最快乐的,然而小虎真的快乐吗?“直到明天早晨他像只青蛙一样蜷缩在河底的红薯蔓中长眠不醒时,村里的人们围成团看着他,多数人不知道他的岁数,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⑨村子里没有多少人关心他、注意他,而他的父母和哥哥也都是在他莫名其妙地犯错之后打骂他而已。在他死前,占据他头脑大部分记忆的都只是不知原因的打骂。在他愤怒的骂出“狗屎”的时候,他心中充满的只有敌意,在他眼中,一切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哥哥,都像那只浑身虎纹斑驳的猫一样,有着可怕的磷光闪烁的眼睛,威风凛凛地逼视着他。
无论是有认知的聪明黑孩,还是无认知的傻乎乎小虎,都面临着同样悲苦的人生。他们幼小的年纪,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生之苦。他们的苦不只是家庭给予的,更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因素压在对这个世界还似懂非懂的弱小孩童身上,捱得过的便能顽强地活下来,与残酷的命运做斗争;捱不过的就只能死去,用布满伤痕的屁股对着人们荒漠般冷漠的脸。
失语者
在莫言的笔下,还有一类人同样在无声的喧嚣中痛苦地挣扎,那就是《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西门闹被迫轮回为动物,变成失语者,在驴、牛、猪、狗、猴的畜生道轮回,在目睹五十多年的历史大变迁后,在人性的一点点消逝中放弃了仇恨,在痛苦的挣扎后选择了追求内心的平静。
五十年的遭际,有身为牲畜所受的劳役之苦,有依然保存人的记忆却身为动物的失语之苦,有被自己儿子打骂的伦理之苦,有纵观历史变迁下人的异化的苍凉之苦……西门闹体验的是为人和为畜的双重痛苦,承受的是历史、社会和家庭的三重磨难。与西门闹五十年无声世界形成对比的,是喧嚣、狂躁的社会,是异化、疯狂的人们,是一个沉重的当代世界。
西门闹本是家大业大的地主,在打倒地主的狂潮中被枪毙,开启了自己的六世轮回之旅。因为没有喝孟婆汤,所以他带着上一世西门闹的记忆走向了西门驴的一生,又带着西门闹和西门驴的记忆走向西门牛,一直到变成先天不足的大头婴儿蓝千岁。在这六世轮回的五十多年中,除了最后的蓝千岁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以外,其他的五世都是不能说话的动物。有着几世的记忆和人的思考力,却不能说话,这五十多年的失语者的遭遇,对于西门闹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刚转世为驴时西门闹想要大喊:“我不是驴!我是人!我是西门闹!”⑩可他哪里还能说出人话:“但我的喉咙像依然被那两个蓝脸鬼卒拤住似的,虽竭尽全力,可发不出声音。我绝望,我恐惧,我恼怒,我口吐白沫,我眼睛泌出粘稠的泪珠。”[11]作为失语者,西门驴有苦说不出,有冤申不了,有仇报不得,只能跟着苦难的主人默默地受苦,最后被饥饿的难民吃掉而死,结束痛苦的驴生。接下来的西门牛依然如此,看着自己儿女所做的事情,只能默默心痛,最后被自己的儿子活活烧死。西门猪、西门狗、西门猴,同样在历史的巨变、社会的变异、人们的狂热中降生,受尽苦难。从驴到牛到猪到狗到猴的过程,是西门闹人性渐渐模糊的过程,他渐渐开始忘却自己为人时的亲人,忘却自己所遭受的侮辱,忘却自己的要报的深仇大恨。仿佛看淡了世事一般,放下了一切,走上了一条佛家的色空之道。或许为人为畜之所以会遭受苦难,皆是因为人畜的欲望与执着,总是无法放下所牵挂之事。然而,无论是在阎王的欺骗与折磨下屈服、放下仇恨的西门闹,还是在五十多年的遭遇中看破红尘、六根清净的西门闹,真的能够不再受苦痛的折磨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大头婴儿、血友病注定了西门闹第六世的悲惨。至此,西门闹真正的生命之重,不是身体上所承受的苦,而是被压抑为一个失语者的经历。有冤申不得、有苦说不得、有仇报不得,这被社会、被历史、被狂躁的民众所折磨的失语者才是这世间真正的沉重。因为失语,西门闹才受尽折磨;因为失语,西门闹才渐渐由失望变为麻木;因为失语,西门闹才寄托精神于虚无。当他慢慢接受并习惯自己是失语者这个事实时,苦难依旧存在,安宁依旧遥遥无期。这才是最沉重最可悲的人生。
内心自白者
在莫言的这个无声的世界中,还有另一类特殊的人,他们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无声世界。他们像说书人一样不停地自白,仿佛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然而在我看来,他们看似不停地诉说,却只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看似说了一切,却只是一种无声的内心自白。《檀香刑》就是在描写这样一个无声却喧嚣的世界,刑场正是这种无声的喧嚣的最佳表现舞台。那是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是一出残酷肆虐的哑剧,是一个正义凛然的法场,也是一个承载着令人惊异的人性之重的地方。
《檀香刑》中有几次刑场的描写,每次都描写得十分细致,宏大萧肃的场面让人不禁屏气凝神。小虫子的“阎王闩”、库丁的腰斩、钱雄飞和绝代名妓的凌迟、戊戌六君子的砍头、孙丙的檀香刑……这一出出“庄严”的哑剧中,施刑者、受刑者、看客轮番登场担任着主角,人物身份从贵为天子的皇帝到命如草芥的百姓,从野心勃勃的篡权者到盛气凌人的外国列强,从唯命是从的大臣到阿谀逢迎的奴才,他们一个个粉墨登场,演得兴致勃勃。当权者的得意与推崇,施刑者的爱岗与敬业,受刑者的呻吟与惨叫,看客的恐惧与满足……在法律与正义的外衣下,隐藏着一个人性善恶的杂汇场。“师傅说他执行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12]人作为异于神的生物,必然有善恶两面,《四书·大学章句序》中尚且说“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13]人性中的恶本性早已是人类的共识。所以,恶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披上了正义外衣的恶,那被光明正大地合理化了的恶。赵甲成为一名优秀的刽子手的过程便是不断说服自己是正义的化身的过程。行刑前,他们在脸上涂鸡血的行为,是去人性的做法,努力让自己相信那些酷刑的合理性。最后,在不断地合理化的恶的指使下,刑场上的赵甲眼中不再有活着的人,有的只是冰冷的肌肉和骨骼。最后甚至认为做出漂亮的活就是对受刑者最大的尊敬。这种人性的异化是社会制度、掌权者等多方面压迫的结果,赵甲人性中的“恶”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被光明正大。如果说赵甲是因为职业因素而被异化,那作为看客的百姓,便是自愿地接受这异化,就像赵甲师傅所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14]。“师傅说凌迟美丽妓女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15]刽子手把自己当作表演者的时候,看客们真的也把自己当成了观众,而这种观看的热情比冷漠更可怕。“你如果活儿干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你活活咬死,北京城的看客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16]作品中的这些伦理叙事,让我们看到看客们“虚伪的同情心”和“邪恶的审美心”,让人在反思看客行为的同时也在反思人性,反思我们自己。这样的看客心理,鲁迅早已在作品中剖析批判,如今莫言再度提出,可见看客现象并非一时一事的现象,而是人性中难以剔除的一部分。就像同情心、审美心人人都有一样,虚伪和邪恶原来也是组成人必不可少的部分。
刑场是一个无声的世界,而那表面的波澜不惊下面又蕴含着多少邪恶的波涛汹涌呢?一个刑场,交杂着无数人的悲喜、成败,交织着人性中所有的善恶、美丑。在这里,生与死已无足轻重,真正沉重的是作为人本身所拥有的复杂人性。
结语
莫言作品中所讨论的生命的轻重不禁让人想到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然而莫言所关注的“重”与米兰·昆德拉所探讨的“重”是不同的。昆德拉的“重”更多的是哲学层面的对于个人存在的思考,探讨的是人生“轻”、“重”选择的问题,这是在生存有了足够保障的基础上展开的思考;而莫言小说的人物大多还没有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多数是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他们有些是没人关心的可怜孩童、有些是身体有缺陷的残疾人、有些是一生都在经历苦难的母亲、有些是因为阶级身份问题而备受折磨的无辜之人。这些人的人生是不可选择的,他们除了面对别无他法。当最基本的活着都是一种挣扎时,又怎会有心思考存在的问题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莫言所关注的“重”比昆德拉所关注的“重”更接近大地,也更接近生命真实的形态。在莫言所描写的所有苦难大众中,无声是弱者的基本表现。因为他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只能用无声来面对,默默承受命运带来的一切。莫言所展现的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沉重感为小说中的人物蒙上一层沉重的生命底色,增加了作品的生命重量,启发着人们对人本身生命重量的思考,让文学作品在无声的喧嚣中默默捍卫着世界之重。
注释:
①张清华、曹霞编《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2013年,第88页。
②谢有顺《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文艺争鸣》,2013年2月,第97-98页。
③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7页。
④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59页。
⑤莫言《白狗秋千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253页。
⑥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2页。
⑦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2页。
⑧莫言《白狗秋千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156页。
⑨莫言《白狗秋千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153页。
⑩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2页。
[11]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2页。
[12]莫言《檀香刑》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11年3月,第220页。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1页。
[14]莫言《檀香刑》,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11年3月,第220页。
[15]莫言《檀香刑》,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11年3月,第219页。
[16]莫言《檀香刑》,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11年3月,第219—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