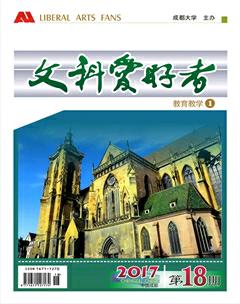凌晨四点
王伊琳
凌晨四点是这个世界的生日。
放眼望去是一片黑暗,月光是唯一的蜡烛,摆在中央。而那些房屋里未灭的灯盏,则是有些庆生者挥舞着的荧光棒。在小孩子的眼里,世界的生日是孤独、无趣的,没有狂欢的派对,没有精心包装的礼物,也没有令人垂涎的大蛋糕。世界的凌晨四点是他们睡熟了的时候,偶尔的呓语与微笑仿佛把他们带去了另一个童话世界,那里四季光亮,万物都是美好的模样。
世界理解这一群可爱的小生灵,但她不认同。她觉得她的生日过得比谁都美好,她想告诉这些熟睡的小生灵,可她怎么忍心扰醒他们的美梦,于是她悄悄地,把这些话编进了他们的梦里。
她说。
星星点点的灯光中的一盏照亮了一间书房,是一间极为简陋却齐全的书房,两米高的红木书架里排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靠窗是一台不大的书桌,旁边摆着一瓶不知名的花草,角落里还放着一张老式折叠床。灯光不强可也没有飘忽不定,和房屋的主人一样,像个心不在焉的庆贺者,干着自己的事情。房屋的主人白天是个失语者,她黯然在周围对80后作家的唏嘘;夜晚是个失眠者,属于她的所有唏嘘都被她重新嵌入了文字当中,沉甸甸的,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拆开,读给你们听:
“他们说的孤独是没有人陪,
可孤独于我是没有人理解。
我在一个怪圈里,一个属于80后作家的怪圈。
其实,当时代意识还未完全被唯美主义吞噬的时候,
它还不是一个怪圈,只是一个冷色调的论坛。
随手写的几段话与那里面沉闷的气息显得十分融洽。
直到人们开始强调当今时代精神,
直到我们渐渐被灌入了商业价值,
我们看似自然地开始为每篇作品设计happy ending。
我们努力用正能量感化读者,再让自己在虚伪中沉沦。
我喜欢这世界,可我不喜欢这生活。”
你看,她赠予我的,你听,她喜欢我。
你们这些新时代的小生灵,是很难读到这样的文字的,和你们的梦境一样:小红帽战胜了大野狼救出了外婆,灰姑娘最终穿上了水晶高跟鞋,灰太狼永远吃不到喜羊羊……只是千篇一律的结局却和狼外婆一样,或许哪天你们接任了“80后女作家”就能看清里面扭曲的面目和骇人的神态了。
别皱眉了,再睡会儿吧。我再看看那位不知疲倦的庆贺者,她没有奋笔疾书的激情,那金色的钢笔尖在寂静中婆娑起舞。她十分善待眼前的纸张,那些无情揭露文化屈辱,强烈谴责种族歧视和战争的纸张,就像曾经她善待非洲儿童一样,宛若一汪清泉浇灌那些干涸的眼眸。尽管等到天亮了,那些纸张就会被当作“糟粕”丢进废纸篓,就像当年她一离开,所有目光变得空洞。
凌晨四点,她用难得肆意的笔墨,当作赠予我的礼物。
上头的莫斯科已经结束了一晚的灯红酒绿,克里姆林宫如往常一样微笑着看着过往的人们;太平洋那边的“山姆大叔”正期待着子民们的晚餐;而我这广袤的土地上也被晨曦光顾。我的生日快接近尾声了,因此又扰了你们的美梦,真是深感抱歉。
我很庆幸,有人赶上了我生日的尾巴,他们的行色匆匆,恰似在赶忙为我奉上最后的贺礼。只是那匆匆的神态,不是难民争抢进界的迫切,也不是“大表叔”下台时快步离开的惶恐,这样说吧,他们比早他们几个时辰在指针上行走的人要少一份不安,对于生活的不安。那些早几个时辰的“夜间动物”大都是“壁虎”,会看准没关牢的窗户往里窜,但你们只用紧紧地关上窗这扰人的东西就进不来了,只可怜它们隔天饿了肚子,又见不着生活的模样了。再者说来,他们比晚他们几个时辰在指针上行走的人要少一份急切,可能因为东方未见全白的天色搭上千篇一律的早起让他们的脸上更显昏沉与疲倦。总之,他们不紧不慢的匆忙让我觉得坦然和真实。
整点的钟声如约地响了起来。你们的梦还在继续,或许一觉醒来你们就长大了,然后发现周遭都变了。别担心,你们可以在凌晨四点来找我,来找找失去的东西,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即使那里可能再也没有机智的喜羊羊或者幸运的小红帽,又或者一只恰好合脚的水晶高跟鞋,但我可以領你们看见一些永远也不会离开的东西,在你们心底的最深处,相信那些东西会给我这个寿星一个面子,让我领它们与你们制造一场“偶遇”,然后你们可以选择做一个只亮着荧光棒却与内心交谈的“冒牌”庆贺者,亦或者做一个拥抱平淡不紧不慢的行走者,至少没那么矫情就对了,毕竟我的生日绝不是一个面具派对。
凌晨四点是这个世界的生日,可一个小时后钟声响了,梦也醒了。
[作者简介]成都市外国语学校高二(10)班学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