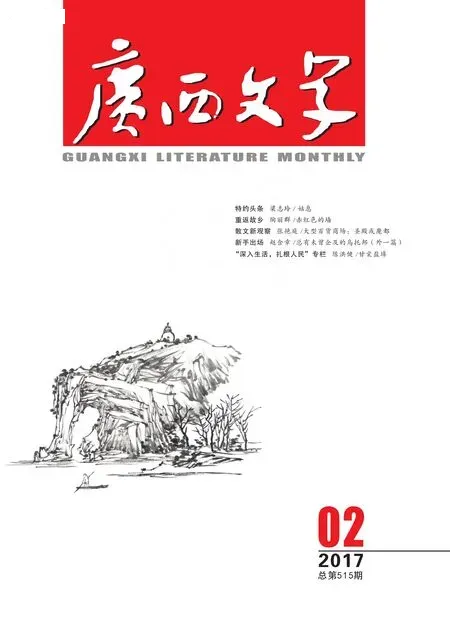赤红色的墙
陶丽群/著
当我开始学会以审视的目光打量埋着我出生胎衣的村庄时,满眼尽是赤红色,熟透的橘子皮的颜色。赤红色的院墙,赤红色的屋墙,赤红色的牛栏鸡舍、猪圈鸭房,赤红色的村道,起风时,飘扬起来的淡淡的赤红色尘埃糊了我满眼,抹着抹着,便抹出一手背泪水。村庄挂在田阳县城通往本县那坡镇的国道上,属于县城郊区,地势坦荡。冬天,茂密的甘蔗砍伐掉后,在那条国道上往来的车马人流,一眼便望见阳光下如陷在火焰中的村庄。全村百来户人家,黑瓦屋顶和其上飘着的袅袅白色炊烟,只是这赤红色的陪衬,愈发使她赤红如霞。因此而得名:墙红屯,一个自然村屯。1978年,她像一道符咒,在我出生那一刻便理直气壮烙印在我的生命中。
我们家在这个名为墙红的村子里生活的历史其实极为短暂,因此不能冠之为“家族”。家里故去的祖先,直到现在,他们的尸骨依旧埋在某座山的皱褶里,大部分直系亲属也依然生活在母亲的出生地。母亲的父亲在县城谋了公职,她的母亲以两次上吊要挟,终于迫使她父亲通过一些关系把妻儿从山里迁到如今的村庄。母亲和她的妹妹来到这个村庄时,已经十五岁了。她只有姐妹俩,作为老大,按照习俗招婿上门,她的父母,我便称之为爷爷奶奶,不能叫外公外婆。我父亲碰巧也是从山区出来上门的,我们一家三代人,其实只有我这一代才算得上是真正生长在这个叫墙红的村子里,算是这个村的人。短浅的根基使我们一家在这个村子犹如一棵根须还没深扎的树,躯干脆弱,枝叶蜷缩。
很快,时光便会在我的生命里刻画下第四十个年轮了,算不算是过了半辈子?不得而知,因为无法预知明天将会怎么担待我的生命。对于出生之地,犹如对于给予我生命的母亲,在我的有生之年,必须要给她一个说法,比如感恩,比如她无意中带给我的疼痛。
这赤红色的墙……
逃 离
其实从来也没真正远离过村庄,即便是现在,坐在电脑前写下这些关于她的文字时,只要站起来,坐上五十分钟的车,便可见到那些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面孔。出生之地算是肥美之地,与田阳县城毗邻,不论上百色还是下南宁,交通极为便利。地势平坦开阔,脾气温和的右江就在村庄面前舒缓流淌,除非雨季暴涨,极少有污浊时候。村里人均一亩五分良田,盛产甘蔗和水稻。只要是本分种地人家,舍得力气和汗水,吃饱穿暖之余还可发家致富。儿童时期村里人的住房,绝大部分是赤红色泥土打的土坯建造起来的红土房,黑瓦片盖的顶。如若要区分个贫富差距,无非就是谁的赤红色院墙垒得高大,屋子门板更厚实,所谓的高墙大院,除此,在格局和颜色一模一样的房子跟前,没法辨别得更仔细了。
农村人其实没有关门闭院的习惯。院墙垒得再高大,竹片编制的院门除非夜晚睡觉,总是时刻敞开着的。村人从门外路过,院里的家什一览无余,如若这家有一辆手扶拖拉机,那就更愿敞开院门了,那是当时农家一件极了不起的家产,代表家底丰厚。院门的开关,在我家另有一番意味。爷爷把妻女搬迁到墙红屯,一双女儿成家后,奶奶便随他进城了。留在墙红屯居住的,其实只有我们一家四口,父母和我们姐弟俩。父亲是个胆小谨慎得近乎卑微的山区人,我们家的竹片院门被他编织得严密无比,并且时刻拢合院门。小时候我们姐弟俩每天听到他最多的叮嘱就是:记得合拢院门!不是关,是合拢。关是拒绝、戒备,含有暗暗的敌意。拢则温和得多,包含不拒绝也不主动的意味。邻人来问个事情讨个说法,一推就进来了。不来人时,合拢的竹院门则起到抵挡院墙外热闹嘈杂的目的。外面狗吠大起,或者打架拌嘴骤来,我和弟弟对着院门奔去,眼看手快要触及院门,身后一声不容置疑的暴喝:给我回来!于是那两扇其实毫无抵挡之力的竹片门,便在我们面前暗含怒火,推开足以让你吃上和瞧热闹相比极为划不来的一顿揍。记忆中,在我们还威慑于父亲威严管教的年纪里,他极少允许我们推开院门到村里玩耍。他总是用山里人特有的灵巧手艺给我们造出各种奇怪而好玩的木头玩具,把我们尽可能留在他的视线之内,留在院门之内,他觉得相对安全的地方。他担心我们的年少轻狂冲撞了真正的当地人孩子,他得罪不起村里任何人。那扇竹片院门合拢上,院里院外就是两个世界。久之,这门便成了一种隐秘的、晦涩的精神特质不落痕迹地布道在我幼稚的生命中。
院门内的世界是单调的,那些木头打造的玩具,可以当作玩伴的鸡鸭猫狗,以及父母长期小心翼翼地憋心生活积攒出来的脾气而引发的争吵,让我们姐弟不厌其烦。奇怪的是,我们对院门之外的世界似乎也并不太渴望。我们在一群孩子中,会特别显眼,言行举止,哪怕被欺负时的大哭,都显出一种近乎傻瓜般的安静,哭得很有规矩。

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子,村人称“千房”
母亲曾经努力融入这个赤红色的村庄。十五岁之前,她一直生活在以玉米为主食的穷山区里,熟悉在旱地上点种玉米,间苗除草,对于在水田里插秧苗,十五岁之后第一次接触这农活。然而早晚两季水稻伺候下来,她居然变成了村里的插秧神手。插秧收割一向是农村最繁忙和重要的农活,特别是农历七月,收割和插秧都要抢在这个月份完成,我们叫“双抢”。一到这时候,村子就空了。除了少不更事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村人全都到田地里去。特别是插秧,要和节气抢时间,节气一过,插下去的秧苗长不好,叶子枯黄难以返青,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那时候,耙过待插的水田蓄满了水,望过去一片白茫茫的平展,田埂也被泥巴抹得光溜溜的,杂草被埋在泥巴之下。孩子和老人通常被打发去待插秧的田块捡拾田螺。这种东西啃秧苗厉害,繁殖又特别快,不捡拾掉,插下去的秧苗不出两天便被啃得七零八落,这块秧田算是毁了。老人和孩子们腰间绑着背篓,搜寻田水之下的田螺。通常一块五分大的水田能捡拾两三背篓,在田头挖个坑,把田螺倒进去,碎砖头一通噼里啪啦砸得血肉模糊,盖上泥巴埋掉。养鸭子的人家则带回去喂鸭子。一季秧苗插完,村人就开始忙着卖肥嫩的鸭子了。插秧时节最辛苦的是女人们。她们得半夜两三点起床,点着火把或打着手电到秧田去拔出白天需要插的秧苗。这活儿非常辛苦,你得带把凳子坐在秧苗田里,一把一把从烂泥巴里拔出秧苗,再就着田水把秧苗根上的泥巴冲干净,拿晒干的稻秆绑扎结实,甩到田埂上滤干水。我们家正好挨着出村的路边,我刚睡下没多久,窗前便开始有络绎不绝的脚步走过,伴随明明灭灭的火光,全是早起拔秧苗的女人。那时候上学还有农忙假,母亲不允许我在床上养懒骨头,一把掀开被子,湿冷的毛巾抹到脸上给我洗脸,睡意便全被赶跑了。
三月份插的是早稻。早起拔秧苗时,田野还一片漆黑,早春的风是冷的,有时还裹挟如针尖般扑在脸上的牛毛细雨。田野空旷,但并不安静,火光磷火般四处闪烁,晨风中传来一些零碎细语。我拎着两把凳子跟着挑空担子的母亲,走在湿滑的田沿路上。走着走着,瞌睡来了,摔了一跤,瞌睡又摔跑了……

村头的庙宇
天色微茫时,忙活大半夜的女人们已经把一天插秧所需的秧苗拔好,整齐码在自家田埂上。母亲每日必须拔一百把秧苗,可以插上七分田,而一个老练的插秧能手,顶多也就插个五分。早春的天色尚未尽晚,母亲就把秧苗插完了,这是她最盼望的时刻,她已经累得腰酸腿疼,还是毫不犹豫蹚进邻人眼看黑了天也无法插完的秧田里帮忙。这是母亲得到片刻和本村女人交流的机会,她带着山区腔调的话语在寒风中七零八落。父母说话的山区腔调常常遭村人笑话。但她还是说个不停,像一个被话语憋坏的人。那些女人在瑟瑟晚风中夸赞她插秧的手艺好,母亲以为以此能融入这个新环境,然而干完活上田洗脚,别人早就远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她站在寒风料峭的田野上,脸上带着迷路般的表情。
我知道那种滋味。我们家院墙有一处特别低矮,那是我和弟弟常年踩在凳子上趴在上面磨蹭出来的。父亲把我们拴在他的视线之内,我们趴在墙头,看院墙之外的村庄,我们的目光跟随村庄的热闹跳跃,内心灌满被疏离的硬生生的伤。
母亲开始带我们逃离。墙红的农活忙完后,她撇下满仓的粮食和满院的鸡鸭,拉扯两个孩子,步履匆忙走在出村的赤红色泥土路上。我们先坐班车到那坡镇,然后再爬三个半小时山路去一个叫玉安的山区村庄,那里居住着母亲的祖父母,以及她小时候的伙伴。那是真正的山路,座座陡峭的高山,一条只落得下脚掌的台阶路忽上忽下。一路上弟弟总要被揍两三回,嘹亮的哭声在庞大的群山里跌跌撞撞。他走不动,需要背。
母亲回到玉安,把我们姐弟俩扔给她的祖父母,便迫不及待地跑去找她的伙伴们了。我们常常一整天见不到她,她急匆匆回来吃饭,又急匆匆去串门,仿佛忙一件重要的事情。每次回到这个高山环抱的连茅坑都没有的村庄,母亲就变成一个快活而脾气温和的人。

进村的水泥路
我和弟弟依旧孤单,母亲的生养之地于我们而言更为陌生,这里的人连说话的调子都和我们不一样,经年赤脚的娃娃们简直把我们当成稀罕物来瞧热闹。山里一日三餐均是炖猫豆送玉米粥,晚饭一碗不稀不稠的玉米粥下去,通常半夜就尿床了。没有电,水要到很远的一个山洞去挑回来,洗菜的水就接着洗脚,然后倒去喂牛。夜晚,躺在静悄悄的群山下,突然想到父亲,他在家里一定更孤单吧?
孤单,变成一种病,侵袭我们一家人。母亲无数次带着我们逃离赤红色的屯子,又无数次返回。逃离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它和赤红的颜色一样,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潜伏在我的血液中。
记 忆
1999年,师范毕业后,生命的际遇把我带到那坡县,成为一所乡下中学的英语老师。这个坐落在狭长山谷里的边陲小县其风貌和风情完全不同于田阳县。田阳平展酷热,山的模糊轮廓遥在天际,春秋模糊,树木常绿,很难从大自然的容颜上辨别四季更迭。人的性情大概也因为常年的高温而干脆得近乎简单粗暴。那坡县四季分明,开门即山,冬穿棉夏穿单有板有眼轮换,其人看起来也比平原地区本分婉转得多。那坡县距田阳县差不多三百公里,那时只有四级路,沿途要经过两个山区县,无数个挂在公路边的村屯。假如碰上阴雨天,从田阳县坐班车前往那坡县,在积水坑洼的四级路上从晨曦微亮走到暮色苍茫是常有的事情。
我舒了一口气。赤红的颜色,假如我不高兴,可以一整年不必见了。那时我十八岁,9月份离开田阳县时,我记得离十九岁还有七个多月。1999年,墙红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红土坯房了,村里开始建起一种俗称“千房”的红烧砖瓦房,把它叫“千房”,是因为这种房子造价并不足万,花个七八千算起得上很讲究了。屋墙依然是赤红色的,红烧砖头嘛,但质地看起来要比红土坯房坚固美观得多。一排红砖房子挨过去,高低面积也差不多大,格局似乎也没什么改变,但土坯和砖头,这是质的变化,往好处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开始富足了。村民们在屋后的池塘种上一池塘莲,整个夏季,毗邻的几户人家得以共享荷香福泽。没有池塘的种几株竹子,房子便有一角落阴凉,茂密的竹叶散发淡淡清香,这家人在热浪逼人的夏季午后便得了几分清凉。红墙黑瓦,竹莲围绕,给这块生养之地一个客观评定,她从来都不是一个亏待子民的刻薄之地,男人女人不经意就长了一米八的个头,与母亲间歇性般逃离回去那个叫玉安的村庄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她当然也有农村村庄共有的恶习,牲畜随处乱跑乱拉,一场雨水下来,村路的泥泞里浸泡牲畜们的粪便,污水横流臭气袭人。路过的人诅咒放养牲畜的人家,被主人家听了去,口角遂起。也许是连日雨天不劳作,积攒的力气无处发泄,发生口角的人正好都脾性暴烈,口舌之战很快演变成为一场赤膊格斗,雨天的阴沉气氛变得紧张热闹起来……这是绝大部分中国乡村的品行,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假如她没给我难以言表的伤害,也许我会像绝大部分农家女,在四季更迭中渐渐长成一个父母操心嫁妆的女青年,在某个良辰吉日和对上了八字的另一半结个志同道合的婚,度过一个农妇平淡无奇的一生。
然而我离开了。从一个连土坡都难得一见的平原富庶之地来到被群山紧抱的国家级贫困山区县份,又从县城坐了将近六个小时的车来到一个边防乡镇,那里目之所及都是将人衬托得无比渺小的高山,大部分是石山,极少长树。去的时候已将近中秋,稀稀拉拉点种在斜坡上的玉米早就掰了棒子,剩下干枯的秆子在秋风中抖索。
人心却出奇地好。
“妹,你们家那里有山吗?”
“没有山的,很平展。”
“吃的什么?”
“大米,一年我们种两次水稻。”
“你家……离县城挺远吧?”
“不远,踩个单车半小时就到了。”
“是这样呀……”
我辗转来到百都中学时,学校已经开课将近一个月。初一三个新生班级还没上过一节英语课,连县城中学都缺英语老师,更别说穷乡僻壤的中学了……下课后,我来到街上买菜,通常被街上的妇女们围住反复问这几句话。对答之后,她们就普遍对我产生一种愧疚之情,好像欠了我天大的人情,买菜一向得到那把最大最结实的。她们会把你拉到家里,给你烤熟的芋头和黄心红薯。假如她们的孩子正好是我的学生,远远看见我迎面走来,她们便停下,侧身避让到边上,脸上堆着笑容等你路过,想打个招呼,又是一副难为情的羞涩模样。路是土路,很宽敞,其实没有避让的必要。她们谦逊的表情常常使我想到母亲。
生养之地给我一种精神上的伤害,百都这个地方,则彻底地在物质上折磨我。我毕业那时,已经没有国家安排工作的说法,得以谋就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些县份贫穷边远,工资待遇极低,多数毕业生不愿来,来也只不过是落得一个代课老师的身份待遇。1999年11月,我领到人生的第一笔工资,一百七十二块零九毛钱,还要扣除电费。我平静地在工资单上签下我的名字,从教政治课兼学校出纳的张老师手里接过我需要一周上二十三节英语课、一节音乐课,还不算晚自习带班所换来的报酬。张老师人很好,有点儿胖,他看着我手里这点钱,总是很歉意地笑。
校长一直很忧虑,担心某一天早上我会突然不辞而别。那时候,就算到饭店端茶倒水当个服务员,报酬都比当代课老师高。他和几位学校领导商量后,免除了我的电费。其实每月的电费从未超过十块钱,一间远离洗浴房和厕所的宿舍,只悬挂一只四十瓦的电灯泡。假如没有晚自修需要带班,我通常在十点前就把备课和批改作业的工作完成了,几乎和学生在十点四十同时熄灯就寝。
那真是静得让人不安的夜晚,学校在镇子之外的一座山脚下,熄灯后万籁俱寂,山间吹过的夜风和石头缝里的虫鸣清晰可辨。窗子外巨大的芭蕉叶子黑黝黝的,几乎伸进我的窗口,芭蕉叶的青涩气味弥漫在夜晚清凉的空气中……

昔日猪狗横行的村道,如今连鸡鸭都圈养了,再也不用担心一脚踩了猪狗屎……

村道铺了水泥,很干净
我通常会在入睡之前盘算所剩的生活费,还可以买几斤米,鸡蛋必须一天吃一个,洗发水和洗衣粉要省一点用……肉是没有了,有钱也买不到。远离县城的百都乡五天才遇一次街天,只有这天,居住在各座大山里的山民出来赶街,人多,街上的猪肉贩子才敢从县城贩来猪肉卖,价格要比县城贵不少。集市早早人满为患,不到十一点,猪肉早就售空。这成为很多老师省钱的借口,买不到了,我也得以避免了这样的尴尬……于是继续煎豆腐炖青菜。百都街上的豆腐真是好吃,纯正的黄豆磨制出来的,在锅里怎么翻炒都不会散渣,带着一股浓浓的黄豆香味。我通常会买上两片巴掌大、两根手指厚的豆腐,少量的油煎得略微发黄,放进一碗水,煮得水发白后放一把青菜炖着。老师们叫豆腐炖菜。午餐吃的米饭豆腐炖菜,晚餐也吃的豆腐炖菜,加一个鸡蛋,日复一日。十九岁的青春年华,一件白色和一件淡蓝色的T恤,两条学生时代就穿的牛仔裤,打发掉两个夏季。
县城是不去的,晕车,往返需要二十二块车费,我觉得后者才是我最大的顾虑。
最担心的是工资发不出,这是贫困山区的通病。
尽管物质生活极度匮乏,那时候却感到出奇的轻松,我觉得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了。一个羽毛已掉光的羽毛球,我和学生们每天傍晚都打得汗流浃背。偶尔上一趟县城参加培训,找不到稍微体面一点的衣服,我才知道自己的青春如此清贫。走在县城的大街上,那些悬挂靓丽裙衫服装店的玻璃橱窗,把身上常穿的那件T恤映衬得寒酸无比,上面还有几处淡淡墨迹。这几处墨迹,算不算是我青春岁月的一笔财富?
在百都中学执教一年,我没回过家。除了积攒不下钱,从来没有要回那个赤红色村子的想法。在某个诸如节日,学生放假回家过节时,空荡荡的校园以及节日的气氛会让我被一种空茫包围,赤红色的村子才得以乘虚而入,短暂划过我的记忆。我会想起母亲常带我去烧香的村头那座庙宇,那也是一样的墙体赤红,供着几尊看起来面目狰狞的神。母亲在那里祈求过许多福,我每次总是索然无味站在一边看她,在她的要求下烧纸淋酒。她那些祈求,我从小听到大,从来就没得到过回应。她依然融不进这个村子。百都漫山遍野黑黢黢的石头,还会让我想起墙红金色的秋天,房前屋后一片平展金色稻田,熟透的稻子垂下沉甸甸的稻穗,散发令人神迷的清香,整个村子被稻香包裹住了。假如放下我的戒备之心,我会发现村里的人这时候变得很温软,走路的脚步、说话的声调、看人的眼神,都因为家园外饱满的稻穗而变得温软。
我还会记起几张曾给我善意笑容的脸。
一阵凉爽的山风吹过,墙红就被吹散了。这个村子像浮萍一样,未曾在我的生命里扎下根,也许我们彼此都没在对方心里扎下根吧。
一年后我又调到那坡县的平孟镇中学任教。那所坐落在中越边境线上的中学,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墙壁被对方的炮弹打出很多弹孔。这个镇子比百都乡稍近县城,然而县城依然和我没多大关系。我的工资从一百七十二块钱涨到两百二十块,而平孟镇的白菜在2000年时,卖到三块钱一斤,清贫的日子一如既往。但这个镇子,却给了我别样的滋味。镇子上所贩卖的西红柿、西葫芦、甜辣椒、南瓜,以及芒果和西瓜,全是从田阳县拉过来的。田阳一年四季酷热,盛产瓜果蔬菜,在广西是出了名的,尤其芒果。多年后,田阳被称为中国芒果之乡,每年都有专列拉着芒果运往北上广。那几个镇子上卖菜的女人,甚至会讲几句田阳土话,我走过她们的菜摊前,她们会操着走调的田阳土话招呼我,隐隐约约的,心里竟觉得她们是这异乡里的亲人,倍感亲切。
2002年,那坡县委宣传部公开招聘记者,凭着在报刊上发过些散文的写作底子,带上一份简单无比的简历去竞聘了。试用期半年后,记者没聘上,县里倒看到我发了不少散文的写作基础,给了一个体制内的编制,安排到县文化局。工资不仅一下子提高了,还调上了县城。
辛苦积攒三个月的工资后,我回家了。其实也并不是想那个村子,而是因为工作需要把户口搬迁过来。
别了三年之后回来的村庄,已经没有土坯房了,家底厚的人家甚至把刚建没几年的“千房”推倒,建起两层楼房,学城里人在外墙贴上光滑的白色瓷砖,院墙也拆掉了,无遮无拦的院子显出开阔的气势。
那时“农转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转了就成城市人了,至于在城市吃什么怎么生活,农村人并不多想,“城里人”是一顶闪闪发光的帽子,戴上便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当生性胆小的父亲捏着户口本和写好的申请把我领进村主任家里,要求盖个章给我办理“农转非”时,我记得村主任伸手和父亲握了个手,父亲黧黑的脸孔霎时涨得通红。村主任在申请书上盖了猩红的章后,一路往家走,父亲一直在抹眼泪。他走路是一种含胸佝背饱含谦卑、给人怕事、畏缩感觉的姿势,这种不端正的走路姿势长期落在他的脊骨上,腰背再也直不起了。迁了户口,身份证也需要重新办理,新身份证上印着我在那坡县的地址,那个赤红色的村子,退出了证明我身份的角色。假如我不愿意提起,她只能待在我故意隐匿的不愿提及的角落里,像一种从根子上的剥离,毫不犹豫的,没有丝毫眷恋。
调上县城后,去百色参加学习培训的机会多了起来。从那坡县往百色的路上,有一段路从墙红屯的背面经过,公路和村子之间隔一片平展的稻田。班车一路颠簸,总是在临近傍晚时经过那段路。在村子的正背面,有一条小土路横穿稻田,连接村子和公路,村里人去百色,通常走这条小路穿过田野,到公路边搭车。我在班车上看见掩映在一丛丛茂密竹子之间的村子,屋顶上缭绕袅袅的晚炊烟火。看见田野上的村人在田间劳作,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车子一晃而过,带着我路过村子。从百色到田阳县城,需要五十分钟,家就在这段路程之间,行程更短,回去很便捷。我在百色学习,也仅仅只是学习,路过那个村人习惯搭车的路口,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我和村子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毫不犹豫擦肩而过。有很多年,我有一种感觉,假如父母故去,我估计不会再回那个村子了。在我眼里,她始终像一扇密闭之门,拒我于门外。我偶尔会愿意回忆起一些关于她的事情,绝大部分时候,我们彼此似乎两看相厌,相互漠视。
回 归
2011年,我回到百色工作,离村庄更近了。偶尔回一趟家,是因为父母年老身体有恙,来去匆匆,还是逃离的脚步。村里所有的“千房”已被喷了涂料的两层楼房取代,这种荣耀一时的房子,在我们村的历史极为短暂,前后不到十年。赤红色的泥土路也托“村村通”政策的福,全铺上了水泥,下雨天再也没有臭气熏天的污水横流。一场大雨下来,路面被洗刷得更干净。变化的还不仅这些,如今收割再也不用人工挥舞镰刀,收割机一天就可收割上百亩,直接脱粒装麻袋运回来晾晒。收割机还装了犁头,收割同时就把田犁好了,耕牛慢慢退出农村人的生活,不再饲养,院子里的牛圈被拆掉,农家院显得更干净了。插秧也不必三更半夜赶活,全部采用旱地育秧盘,一般在家里就可以自行培育。到了插秧时,把秧苗从育秧盘里拔出来,挑到田里,站在田埂上往水田里扔就行。小时候经历过的农忙“双抢”火热场面一去不复返。这个和县城毗邻的村子,村民和城里人基本上已没多大区别,电脑、私家车成为再平常不过的家私。
母亲买了些首饰戴上,粗短的手指箍一个金戒指,还戴了耳环,她很满足。她还会和村里几个比她稍微年长的老妇人赶集。不知道谁带了头,村里每年农历十二月中旬都会在新修建的庙宇前举办庙会。每户人家出一百块钱,集资买来酒菜聚餐。这个庙会后来又渐渐演变成村里的“女儿节”。这天村里所有嫁出去或外出工作的女儿都会回来,在庙里拜祭后,和村人在庙前的晒谷场吃一顿丰盛的露天晚餐,比过年还热闹。庙会实际上变成了一家团圆的特别节日。嫁出去的女儿们每年只在农历七月十四和大年初二回娘家吃团圆饭,但这天家里的母亲或嫁进来的媳妇也是要回娘家的,实际上也并不能团圆,唯有庙会这天,一家人能圆圆满满坐在一起。
母亲期期艾艾给我打电话:你回来吗?
我总是拒绝。她知道我的心思,从来不勉强我,她其实是盼望我回去的。
我在另外一座城市眺望村庄。村庄依然在那里,始终没变。我转了几个地方生活,回到一个能和她遥遥相望的城市。我们像两个相互对峙的固执的人。
我形容枯槁,整日恹恹无神,不仅对村庄,还对许多事情和人无动于衷。自从2008年开始,一场生活的突变对我打击非常大,焦虑像一种隐患折磨着我,最后导致睡眠离我而去。熬了很多中药调理,不仅没好,把胃也给喝坏了。由睡眠不足到败坏胃口,最后连水果都不愿意吃,整天感觉不到饿,含几颗奶糖就打发掉一天。整个人憔悴得看起来像患上了大恶疾。那些没有睡眠的夜晚,我像一台清醒的座钟,忠实地度过每一秒。白天则陷入一种类似发低烧的昏沉,这种昏沉使我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也无法把我带进片刻的睡眠中。极度疲劳使我变得敏感起来,常常无端沮丧和哭泣。失眠如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困扰着我。直到2013年,我再也无法坚持工作了,整个人像一部被拆散的机器,无法再正常运行。没经过父母同意,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
父母吃了一惊,这件事情变成我们家一件大事,他们担心我以后的生活,更担心我扔掉体面的“国家”工作后,会不会又被村里人瞧不起?他们惧怕那些日子。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没有睡眠,会因为在他们看来微不足道的睡不好觉而辞掉旱涝保收的体面工作。但当他们看到我瘦骨嶙峋的憔悴模样时,还是不忍心多责怪。母亲极力劝我回家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了。没有过多的想法,在哪里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都是带着昏沉的清醒。那段时间,母亲每天傍晚都会带我去村头的庙宇烧香。她跪在神像前,双唇轻微而快速移动,我听不清她念叨什么。
这座富丽堂皇的村庙前,是一个大池塘。多年前的那些夏天午后,附近人家总会把牛赶下池塘,让牛在清凉的池塘里消暑。池塘并不深,牛趴下后,正好能没过整个身子,露出一池塘的牛头。孩子们便会骑在沉入水中的牛背上嬉水。偶尔有被蚂蟥叮咬的孩子,连蹦带跳爬上岸,一堆孩子大呼小叫尾随而来。孩子们并不怕这种恶心的血吸虫,他们会把蚂蟥扯下来,用一根坚硬的细木条从蚂蟥的嘴里穿进去,穿过蚂蟥的肚子,一直到细木条从尾巴钻出来,把蚂蟥里朝外翻个个,蚂蟥吸下去一肚子的血便喷了一地。据说这种无骨动物不会死,剁碎之后遇到水,那些片断便会变成许多条蚂蟥重新活过来……我们姐弟俩从没参加过这些对孩子来说极为刺激的游戏。不爱读书的弟弟刚到办身份证的年纪,立刻领了身份证,常年离家在外谋生,我不知道这个村子给他的感觉是否和我一样……如今的池塘被深挖了,种上莲藕。我满目倦态盯着盛开的一塘荷花,一晃,便三十四岁,成家和立业,什么都没完成。

如今的楼房
母亲给我熬了一种汤水,她说能治疗我的毛病。汤色呈一种混沌样子,她在里面加了点儿红糖,我闻了闻,只有红糖轻微的香甜味,也没看到任何药渣,也许被她扔掉了。我慢慢喝着,也没有药的苦。我并没抱什么希望,这些方子无非是母亲从哪个村妇那里听来的偏方,反正不会喝死人。
一日三次,就这样喝着。一天午后,我和母亲在屋后的菜园里剥甘蓝菜叶子,她要剁碎了喂鸭子。快到八月十五了,要催肥养的十几只鸭子,能卖个好价钱。母亲的神情很安详。她年轻的时候,脾气是很暴躁的,父亲常常被她责骂得哑口无言。这么多年了,她终于能以安详的面容和村庄相对。
而我呢?
父亲的懒人床搁在屋檐下的阴凉里,我在地里蹲得有些脚麻了,便到懒人床上躺下来。不料一觉过去直到夜幕降临。睁开眼看见母亲坐在旁边的小矮凳上,摇着扇子为我驱赶傍晚的蚊子。
你做梦了,说了好几次话,我都听不清楚。母亲对我说,随后起身进厨房做晚饭了。我着了魔般僵在懒人床上,不知道这一觉的机缘从何而来。站起来时,整个人松软得都有点儿头重脚轻了,是一种久违的、温软的舒适。
我整整喝了一个月母亲熬的药汤,每次上床躺下来,带着无比虔诚的心等待睡眠来临。很快,我便沉入了睡眠中了,只是睡,连个梦都没做,我们那里叫睡死人觉,睡得像死过去的人。睡眠成了我那段时间主要做的事情,动不动就睡意袭来,躺下就无法叫醒。睡午觉常常让我错过晚饭,接着睡到第二天早上,似乎要把这几年所缺的睡眠全补回来。我盯着那碗母亲熬的、加了红糖的药汤,没看出什么特别,连一点药味都没有。我问她是什么药熬的,很神奇。
“哪里是什么药,我就是在菜园里抓了点儿泥土,加水煮开,沉底后倒上面那层清水,加了糖给你喝了,村里的泥土。”她叹了口气说。
…………
我在家待了一个半月,重新回到生活的城市中。少年时代的村庄生活,我再也回不去了。我不适应,或者说不愿意过乡村的生活,城市生活有很大的压力,我还是选择留在城市里。睡眠仍时好时坏,总的来说,比以前好了很多,体力和精力如枯木复苏般慢慢恢复回来。我也不再惧怕失眠了,只要连续两天没有睡意,我便回到村庄,喝几碗泥巴水。这几碗带着泥土腥味的泥巴水似乎变成了我生命的加油站。其实我也不知道失而复得的睡眠和村庄的泥土有何种玄妙关系,也许根本就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我和村庄一直相互疏离,甚至排斥,找不到通向彼此的路。失眠是不是村庄对我的一场预谋?
一把泥土,把时刻想逃离的骨肉重新拉回她的怀抱中。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养之地大概都有这样无可抗拒的魔力吧。不惑之年很快来临,村庄终于给了我一点启示,我常常毫无来由地跳上班车,朝村庄一路回去,在清晨、午后,抑或霞光满天的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