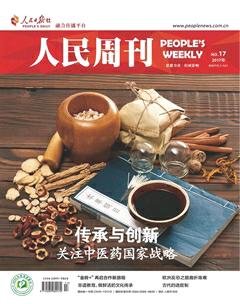我记忆中的季羡林先生
梁志刚
1962年,我在河北一个县城上高中,读到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满燕园》。文章中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书声琅琅、春光常驻。我被深深吸引了,心底萌生了进燕园求学的憧憬,同时牢牢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季羡林。
没有名教授“派头”
两年后,我如愿考进北大。在东语系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当时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他和我想象中的模样大不相同,瘦高身材,五十出头年纪,慈眉善目;穿着既非西装革履,也非潇洒长衫,而是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没有什么惊人之語,只是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而我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说明我们的机会难得,担子很重。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总之,没有一点我所想象的名教授“派头”。
当时,季羡林给梵文巴利文专业60级同学教课,与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哪位同学没有脸盆,可以领一个。因为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久,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是打赤脚走进校园的,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了,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但心里暖暖的。
二是那年“十一”,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舍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季先生叫一群刚从乡下来的大孩子到自己家里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据此,我认定季先生是好人,好领导,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求学是我的福分。
1969年秋天,他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
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我毕业以后回母校进修,季先生给我们开了两门课:英语和印度概况。
季先生十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印度学是他的主要专长,教我们确实是牛刀杀鸡。可是,他备课一丝不苟。英语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个单词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含义也有差异。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他请教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外教。在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单词的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所以要从上下文的意思注意词义辨析。同学们一目了然,戏称为“季羡林大饼”。
季先生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捞干货”为我们讲授了两年的英语基本教材,还向我们推荐了可以用一辈子的工具书《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
印度学内容浩如烟海,当时没有教材,季先生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一清二楚,表现出非凡功力。
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听季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季先生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就散文《春归燕园》。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季先生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979年夏天,季先生应新疆大学之邀西行考察讲学,同行的还有任继愈、黄心川两位先生。他们在新疆的日程安排特别满,先生让工作人员特地通知我去新疆大学一晤。
这一晤就是一整天。
几年没见,我发现季先生仿佛年轻了十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没有整块时间和我谈话,就令我陪在身边,参加座谈、考察,利用活动间隙,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
得知我搜集中亚历史资料遇到困难,季先生利用鉴定善本古籍的机会,向新疆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在军区作调研工作,如果他需要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季先生第二次到新疆是1985年,主持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他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进而概括为东西文化两大体系,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
连日的紧张会务,季先生累病了。休会时间,他没有去天池游览,而是留在昆仑宾馆接见在新疆工作的昔日学生。听学长黄文焕介绍,会上争论很激烈。有学者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季羡林针锋相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并在会上达成了共识。
近读曼菱新作方知,主张“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这是季先生的志向,也是他对新一代学人的殷切期望。
好钢要使在刀刃上
1986年,部队确定让我转业,我写信报告了季先生。先生回信说,关于工作安排,要多作几种准备,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后来有人告诉我,季先生为了我能够返校,或者能够归队,四处奔走,从学校找到市里人事部门,碰了不少钉子。我听了诚惶诚恐,小子何德何能,蒙先生如此厚爱!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归队,被分配在档案部门工作。但能从遥远的边疆回来,可以经常见到敬爱的季先生,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一年春节回校给先生拜年,遇到几位颇有成就的当年同窗好友,不禁自惭形秽,感到愧对恩师。先生安慰我说:“好钢使在刀刃上。事务性工作总得有人做,都当专家,专家岂不要饿死了?”
我不敢以好钢自喻,但季先生的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我安下心来,干过党务,搞过后勤,甘当绿叶。我认为,不管能否在先生旗下做事,只要认真学习和践行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就算没有辱没师门。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爱人和孩子也非常爱戴和仰慕季先生。他们跟我去先生家中拜访,先生笑脸相迎,拿出点心、水果热情招待,告别时亲自送出大门。有段时间我爱人身体不好,先生总挂记着,每有新作出版,先生在赐赠时总是先写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吃石榴,还特意把山东老家捎来的石榴留给她吃。小孩子不懂事,忽然想起什么问题,想向季爷爷请教,也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跑去就敲季爷爷的门,老先生不但不嫌烦,还夸他们“肯动脑筋,有出息”。季先生对下一代都慈爱有加,寄予厚望。
季先生晚年经常考虑关乎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思维敏捷而深邃。他提出“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辟阐述了和谐的三个层次,并写诗“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表达了十几亿中国人民内心的企盼。
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季先生晚年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孤独凄清,失去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身不由己。他本人却保持难得的清醒。
曼菱告诉我,1999年在北大勺园为季先生庆祝米寿的宴会上,来宾致祝词以后,寿星致答词:“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当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著文坚辞三顶桂冠;他还郑重申明:“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读这些文字,当时的理解是谦虚,现在看来,是季先生对神化的反抗,是他对实事求是的坚守。先生一生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将之奉为良知并身体力行。他数十年如一日,起得比鸡还早,呕心沥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世人楷模。可是先生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英雄业绩。“麟凤”也好,平凡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非凡与平凡于一身的人。能够得到先生数十年的教诲,是我人生之幸。在我这个老学生心中,季老是我永远的先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