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记忆
夏晓虹
北京大学人文学院
我的高考记忆
夏晓虹
北京大学人文学院

上图:作者1981年春于北京大学南门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多半经历复杂,如果按照过去填表的要求,“本人身份”一栏恐怕无法单纯写作“学生”。实际上,除了没有资格当兵外,工、农两行我都干过。而无论哪个时段,上学读书都是我的梦想。
1969年去吉林插队后,我曾经非常盼望能够获得推荐入学的机会。特别是,先后当过大队妇女主任的两位同校女生,接连被推荐上了北京医学院与北方交通大学,更让我燃起了希望。我觉得下一年应该轮到我了,因为我已是这个北京集体户中唯一的女生。为此,我甚至很投机地写了平生仅有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应该说,大队党支部水平相当高,肯定洞穿了我的心思,并没有让我“得逞”。不过,很快,我也调整了方向,改为办理病退回到北京。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是北京皮毛三厂刚刚学徒期满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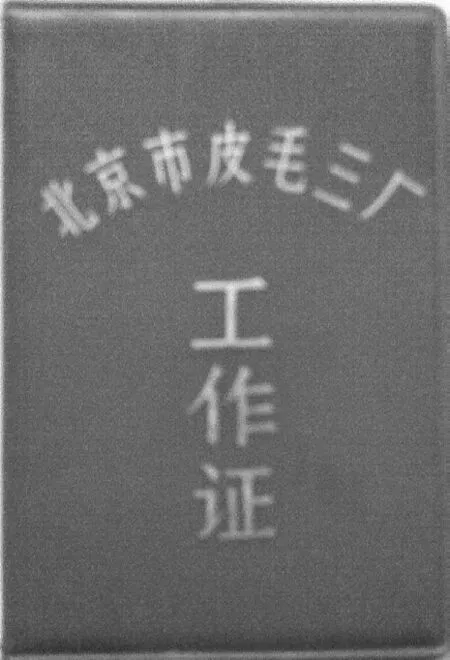
作者在皮毛三厂时的工作证
记忆往往不见得准确。1998年北大校庆时,我写过一篇《我的走读生活》,其中简略涉及了高考情况。那时没有网络资源,故仅凭记忆,我将复习时间提前到了夏天。实则,按照现在可以方便查到的资料: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方才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奠定了“统一考试”的决策基础;10月12日,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下发;全国人民则是通过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才普遍得知此事。
按照这个时间表,12月10日北京开始高考,中间的复习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个月零二十天。当然,那年头也有各种小道消息流传,提前测知高考恢复也未必全无可能。但无论如何,《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的权威声音,在当年习惯于忠实执行不断变化的中央指示的各级组织那里,还是得到了雷厉风行的落实。对考生而言,最大的优惠政策是,我所在的工厂不仅不阻拦报考,而且还提供了最少十天到两周的带薪复习时间。似乎我们能考上大学,对于皮毛三厂来说也是荣耀。
记不清厂领导是否有过这样的鼓励,反正我熟悉的有向学之心的青年工人报名者总有七八人。而这样的福利仅此一次。第二年我妹妹复习考试时,就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当然,北京的工厂在1977年是否曾经普遍施行过这一政策,我也不能确定;可以肯定的是,皮毛三厂的假期对我人生道路的改变意义重大,令我至今感激不已。
话说我家兄妹三人,均间隔两岁,正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遭遇“文革”,此时也都以简陋的初中毕业学历,激起了参加高考的兴致。只是,我妹妹那年来不及准备,比我晚一年才如愿以偿。我和哥哥则开始一同复习。虽然我们的报考目标不同,他瞄准外语学院,我向往的是历史与中文学科,但复习的主要内容还是相同的。加上同院一位邻居宓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铁道史研究专家)的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来往密切,三人常在一起温习功课。
而“文革”发生时,我在景山学校读六年级。虽然该校在全国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实验,五年即小学毕业,1966年6月,我已在初中部。不过,与正规的中学教育相比,我们还没有开过物理和化学课,数学也只学到了代数的三元一次方程。以这般浅陋的知识参加高考,显然只能投报文科院校。而各门考试的科目已经预先知道,文科有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四门,报考外语院校者再加试所选语种。我哥哥虽比我在中学多读了两年书,可惜他对数理化完全没有兴趣,严重偏科。我们也都很清楚,语文和历史大抵靠平日的积累,突击没有用,地理可以稍微补补课,复习的重点于是落在数学。
说到数学,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强项。起码我在景山学校读书的年代,一直以数学成绩突出而为老师、同学知晓。每次班级推选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我都是当然的选手,并屡屡获奖。但这些“光辉”的业绩都属于小学的算术时代,进入中学课程,我在学校习得的代数不过是起步而已。
幸好,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并未因下乡插队而中断。集体户里的同学萧霞,父亲是“文革”前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家里有不少战士出版社翻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记得她带到乡下的这套数学课本是绿色封面,当时我们觉得这是最耐读的书。收工回来无事或者不出工的日子,我们就一本一本地看起来。自修教材的好处是,所有的习题在最后都附有答案。因此,从《代数》开始,我们相继学完了《三角》《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我的解题能力也得到了萧霞含蓄的称赞,记得她后来给我的信中提到,我们一起做过题,她觉得我的智力够用。
1977年高考复习,时间紧迫。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温习曾经自学过而多半已遗忘的代数、三角和几何,还要补习未曾接触的解析几何,确非易事。这里有无数的公式要熟记,无限的习题要演算。我于是发明了一种自认为相当有效的简便方法,即将大量初级水平、用于巩固知识的习题丢弃,在每组练习中,只挑选最后一两道最难的题目去做,如果能够解出,不仅足以锻炼智力,也可以记住相应公式。凭此招数,我居然完成了全部数学科目的学习。
那时,我每天的乐趣就是和邻家女孩对答案,讲说解题过程,然后就是互相吹捧。她与我有同好,都喜欢挑战难题。我们在数学上的互助,也颇有一种棋逢对手的知己感。而每次的演算虽然煞费苦心,一旦豁然贯通,那种精神上的兴奋与满足,很让人陶醉。由于过度思索,必定血压上升,所以虽在初冬夜晚,我们仍然头脑发热,以致留下了夏日温课汗流浃背的错误记忆。遗憾的是,以其才智,这次高考她竟然未被录取,我一直为她抱屈。
考试的日子很快到来。现在已经记不起我是在哪个考场答题的,想在网上找一份当年各科考试的题目也未能尽如人愿,仍然只好依赖不那么可信的记忆,去拼凑我的考试现场。
关于政治课的试题,我已经没有留下任何印象。那些紧跟时势的题目,很容易用当年广播、报刊中不断重复的话语搪塞过去。而时过境迁,这些东西在大脑的存储空间中早已被消磁或覆盖,本不足为奇。
史地课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忆。不过,以我们那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视野,对第三世界小国穷国的名称与首都倒是格外熟悉。复习时,只需在地图上确定各自的位置,以便答得出邻近国家。
印象最深的还是语文卷,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试题。记得其中一则引用了鲁迅先生关于“中国的脊梁”的说法,要求回答这里喻指的是哪些人。我那时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著作,凭感觉推测应该是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便把这句话放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胡乱作了发挥。这道题我显然没有猜中。

作者复习时所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占分最多的是作文,有80分,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使用“战斗”这个词语,很有些“文革”遗风。不过,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政治风云几经流转,“四人帮”被抓与邓小平重新主政,其间都很有“战斗”的意味。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的命运也将随同国家的命运发生巨大的转变。只是,当时我们“身在此山中”,尚没有那么敏锐的意识。至于本人实际的“战斗”,只是整日和皮毛厮混,落笔时难免举步维艰。虽然用了些写作的老套子,前后呼应,从国家大事说到个体人生,但把两者勉强牵连在一起,总觉太过悬殊。并且,“战斗”一词始终无法落到实处,行文空泛,我自己已是十二分的不满意。归来,向同住一院的舒芜先生汇报,他倒是安慰我,说“写得还不错,等着好消息吧”。直到后来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一位老高三学生的同题作文,竟然以复习期间妻子的生产串联成文,而百转千回,仍和“战斗”的时代挂上钩,这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高明”。
既然作文不能出彩,为了给判卷老师留下点好印象,其时正热衷于旧体诗写作的我,也在卷末顺便誊录了专为此次高考新成的七绝两首。原诗今已寻觅不见,惟隐约记得,其中嘲讽了范进中举的癫狂,似乎自信考试的结果不会影响我的远大前程。这样的“言志”,自然属于典型的口是心非。日后,每当在研究生考试阅卷时看到类似的诗词,都会羞愧地想起当年自己拙劣的表现,而对该生心存同情。

1973年10月,在吉林三岔河欢送周珊珊(后排右一)入学北京医学院,后排中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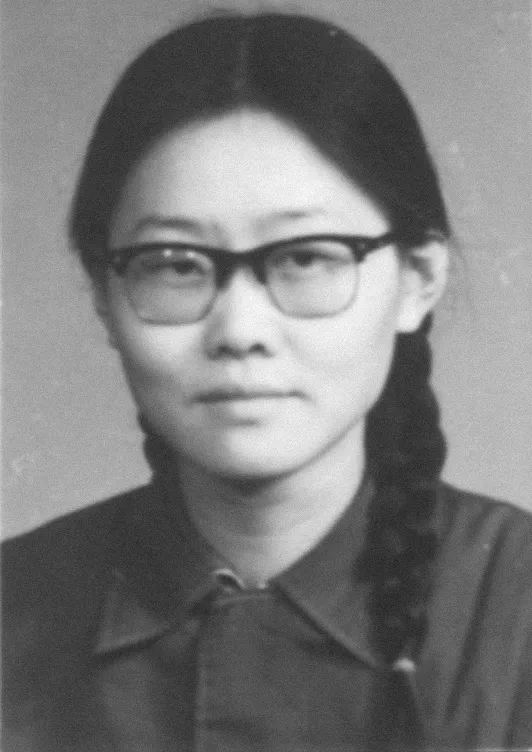
作者1978年3月入学时贴在学籍表上的照片
最后要说到的是我费力最多的数学。语文因为完全没有复习,最终得了78分,也算正常。本来期望数学能拿90分以上,没想到好像只得了88分。其实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的这个最高成绩属于数学还是史地。扣分的原因是,倒数第二题应该用解析几何的做法,但我慌忙中忘记了公式,很麻烦地用平面几何的方法推算出来,虽然思路别致,终因费时过多,以致最后一题仅开了个头,就到了交卷时分。而且来不及验算,有道题多出的增根没有发现,又被扣去几分。不过,平均下来,四门考试总算过了80分。
实际上,获知这些分数时,我已知道未被任何一所志愿中填报的大学录取。那时倒不是“艺高人胆大”,纯粹是不知天高地厚。受到一同报考的年轻工友激励——有位大姐竟然三个志愿分别填报了北大三个系——我当年也标的甚高。我钟情的学科是中国史,偏偏北大当年历史系只有考古与世界通史两个专业招生,前者要出野外,太辛苦,后者我又没兴趣。只好退一步,选择了中文系,好歹还有古代文学可以和史学沾边(古文献专业当时在北京没有公布招生)。接下来的第二、三志愿,仍然回归我的所爱,分别是北师大和南开的历史系。填写南开大学时,我着实下了很大决心,好不容易重新获得的北京户口,实在不甘愿放弃。其实,问题的关键首先在南开大学是否要我,但这个前提始终未曾出现。
起初,我哥哥曾被家人寄予很大希望,他居然通过了日语笔试,得到了参加北京外语学院口试的通知。我哥哥的日语先是跟着广播学,后来由父亲领去见他的老领导楼适夷,算是拜过师。不过,楼伯伯1930年代留学日本,到指导我哥哥时,自称已开不了口,只能指点读书。可就是凭借这点哑巴日语,时年26岁的哥哥竟能混入后生小子群中,一道参与面试,在我看来已相当了不起,尽管年龄与口语均处于劣势,让他绝无胜出的可能。
至于我的大学之路,简言之,即是好事多磨,最终峰回路转。本来以为已经无望,第二波考试制度改革施放的“扩大招生”新政却再度惠及众多考生,我也有幸以第一志愿补取。比正常入校的同学晚了一个月,1978年3月初,我终于走进了北大校门,从此不再离开。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的工厂还有两位朋友也与我一同扩招上了大学。其中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刘记不清是去了北京钢铁学院还是理工大学,入学后,我们还来往了一段时间。另外一位面容姣好的小张则考入第二外国语学院,她同我一样留校任教。大约十年后,我们在友谊宾馆主楼的露天咖啡座曾经偶遇。记得当时她告诉我,她和先生已经准备移居美国。她身边的那位男士温存儒雅,也是二外教师。明白这应该是最后一面,我祝他们好运。
入学后,我还回过一次工厂,看望师傅和年轻的工友。其中一位女师傅问我上学有没有钱,当得知我因为插过队,才有每月十几元的生活费,她不禁真诚地为我惋惜。我离开皮毛厂时已是二级工,月薪40元,这在当年比其他工厂待遇高,难怪师傅们不理解。倒是车间里一位平日淘气叛逆、却与我私交甚好的男生小毕一改常态,显得异常严肃。送我出来时,他直言相告:“其他考上大学的人都没有回来过,以后你也不必再来了。”我理解他善意的提醒,从此不再去打扰他们。如今,小毕和其他当年在一起的工友应该早已退休;而我生命中一年零四个月的托身之地北京市皮毛三厂不知是否还安在。祝福我的工厂和朋友!

作者近照
2017年8月1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责任编辑/崔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