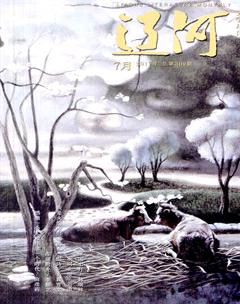车间时光
李新立
时光的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一些事物随之消失,但似乎仍然停靠在记忆的入口。蓦然回首,许多旧事雨点般洒落。
1995年初春,万物正在复苏。上午八时,阳光充足,心情没有觉得不好,我们七八个男工,先去人事部门报到,然后由一位不认识的秘书领着,去了生产调度室。从文件上知道,我们分到新的岗位上班,这多少有些新鲜和兴奋。生产调度室里,六七张桌子前都坐了穿着工作服的师傅,据说他们是各车间的主任。按理,主任们就是我的上级,生性胆怯的我,不由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
我们经过主任们再次分配,就有了自己的归属。我的车间主任,年龄稍大,方脸,头发灰白,说话声音低沉。他打量下我,说:“你这身板,恐怕耐活不了几天,那岗位连脏带苦,你得有个思想准备。”他在前面走着,我像头瘦弱的小牛,快步跟着。又到了库房保管室,主任简单地填写了份领料单,保管便交给我一把大铁锨、一双手套、一顶防尘帽和一只防尘口罩。主任仍然在前面走着,我扛着铁锨,把防尘帽和口罩提在手中,一路晃荡着来到了生产车间。车间是高大的窑楼,机械声填满耳朵,主任朝上喊了几声,便有粉尘落入他的眼睛。正好,过来一位瘦长者,主任说他是我的班长,今后就归他管了。班长又把我领到窑下,指着链运输送带,强调了下岗位的重要性和操作要点,吩咐了几句上下班时间,随即转身上了窑楼。一九九六年春暖乍寒的一天,我所在的小厂被该公司兼并,初次体味到了失业的惧怕,还算好,约莫半个多小时里,转来倒去,跑了不少路,但很快认识了自己的上级,进入了新岗位,内心多少有些安慰,甚至几许温暖。
宿舍在西边综合楼的二楼上。下班时,有人提醒我去总务要一把房门钥匙,便找了过去。总务笑嘻嘻地说:“新来的?”说着话,从一堆钥匙中找了把黄色的,心里怀疑它是否能打开房门时,发现上面贴着一片胶布,赶紧捏在手中走了。从表皮的磨损程度看,使用过它的人已经不少。宿舍的樓道里,污水是新洒出的,泛起的灰白色泡沫正在破碎,洋溢着洗衣粉与香皂的味道。顺墙壁立着的铁锨上,挂着汗渍未干的工作服和落有灰尘的防尘帽。打开右手第一间房门,高低床几乎与人撞个满怀。这是四人住宿,三张床位上已经躺着人,那个上面空着的床就是我的了。宿舍内一张小桌,一件衣柜,剩余的空间不多。毛巾搭在床头上,脸盆和脚盆塞在床下。地面上很湿,洗过一般。我差不多明白,上下班的同事都懒得去公共澡堂,喜欢在狭小的空间里擦拭身体上的灰尘和汗渍。正是春夏交替,窗户没有全部关闭,只拉了窗帘,但自窗口吹进来的清风,仍然对室内潮湿发霉的气味似乎无可奈何。他们三个,扯着呼嚕,我往床上扔东西时,竟然没有被惊醒。
这意味着,新的生活开始了。
窑楼高过三十米,如果加上伸向半空的烟囱,估计不止四十米,抬头仰望,这个硕大的钢铁与水泥的结合体,似乎悬浮在头顶之上。当然,我很少看它,刚进入生产区域时,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上空弥漫着肉眼难以看到的颗粒,趁抬头的机会,这细小的家伙就会奔入眼角,那种灼热、酸痒,实在叫人难耐。一条约五十厘米宽的链式输送带,以三十度的倾斜度,插到窑下。我们一组四人,主要转运从窑楼卸出来的料块。我们头戴防尘帽,嘴堵防尘罩,除了眼睛,一张脸基本全被隐藏。那些块状的结晶体,从干度以上的高温燃炉内跑了出来,还带着炙人的热气。它们受咖吗射线的的指挥,排卸得极有规律,每隔一小会,卸料器“昂——”地叫一声,从溜糟上“哗——”地流下一堆料块,“昂——”地叫一声,“哗——”地流下一堆料块。那个链板输送机,好像一个人,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保持不卑不亢的速度,将料块运上来,正好溜到我们放好的架子车上。等架子车装满了,挪到一边去,赶紧换上另一辆,然后推着装了料块的架子车,“丢丢丢”地一阵小跑,转倒在附近的堆场上。无处不去的风,此时显得十分廉价,随时为料块们降温。
和我同在一个小组的两位同事,四十岁左右,都姓韩,是从一个分厂抽调来的,我去时,他们已经在岗两月之久。显然,二位同事十分熟悉这个岗位的工作。或许觉得是体力劳动,技术含量太低的缘故,他们从未给我讲过操作要领,倒是我眼看着他们的劳动步骤,知道怎样使用架子车和铁锨才能更为轻松一些。共事半月之后,到了发放工资的日子,同事们都好像去了主任那儿签名领钱,我心想时间太短可能没有,或者累积到下月,便没有去。几天后,一同兼并上来,并被分配到另一小组的兄弟问我领到了多少工资,我反问他:“有吗?”牠说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我好面子,怕被笑话,不敢去问主任,就问我的这两位同事:“不知道我这月有工资没有。”两位都没有吱声,就没有再问。心想,如果有,馍馍不吃还在笼子里放着,不急。
又是几天后,倒过班回宿舍的路上,碰见车间主任,擦身而过时,他突然回头喊住我,说:“见你不来领工资,就捎给你小组的小韩了。”我实在张不开口向韩师傅索要几百元钱,也不明白他俩为啥不把我的工资交给我。我的宿舍下铺的兄弟,也是和我一起被兼并过来的,知道这事后,骂我没有出息,使我十分惭愧,半月后,我那两位同事提着个黑塑料袋,强行塞到了我怀里,我看看,是五十元一条的烟,外加我的工资。他俩说,实在不好意思,代领工资后给忘记了。看他俩一脸歉疚和不安,我明白是我下铺的兄弟向他们开了口,我顿时不好意思了起来。正好口袋里没有香烟了,就收了下来,说:“辛苦两位哥了。”将烟钱还给了他们。此后,我的这两位同事还告诉我一个偷懒的秘密:大夜班是最容易疲倦的时间段,可以去窑楼的操作间,趁师傅们不注意,将咖吗射线控制仪调一下,可延长窑下卸料间缓时间,减少卸料次数。这个办法我从未使用过,也不知真假。而他俩,不久就返回了原企业,不久,这家企业被解散。
劳累,使大家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着。
这种机械且有规律的劳动,使人的大脑处于凝滞状态,不容多想,就从春天进入了夏天。
春天的沙尘天气,在窑下岗位,最能看见它的威力。风像一群乱窜的疯子,进入高大的车间与车间、设施与设施间,找不到顺畅的出路时,四处盲目冲撞。这时候,劳动防护用品显示出了它们的脆弱,眼睛和脖子是最容易遭受侵犯的地方,砂土、灰尘常常耗费许多精力,才能清洗干净。而夏天,尽管炎热的天气加上窑下料块的温度,让人产生总想躲避到荫凉处的欲望,但少了沙尘的侵袭,应当说是好多了,如果有一场雷雨,那更是上天最好的赐予。晚秋时节,上夜班是苦差事,尤其是上大夜班,要从深夜十二时上到第二天早晨八时,瞌睡不说,还会受到冬天般寒风的侵扰,特别是在凌晨时分。这时,我会违犯纪律,偷偷睡一会儿。那些倒在堆场上的物料,虽然硌人,但很是温暖,躺在上面,没有多想,不讲究睡姿,就很快沉沉入睡,把隆隆的机械声甩到世界之外,即便是细细的夜风在身上取暖,也不会醒来。身体升腾而起,一种快意从神经中抽出,但这不是做梦,不用睁眼就会知道,另一车间驾驭装载机的师傅,转载堆场上的物料时,把那只大铲伸在了我的身下,故意将我轻轻掂起。我一点不讨厌这样的玩笑。endprint
不知是不喜欢还是不敢妄动,我很少随意脱岗窜岗,通常往返于家、宿舍、岗位之间。当然,也有例外,夜班寂寞难耐,偶尔遇到窑面操作不正常时,窑下的链运机一般会停下来。抽身爬上窑楼,听师傅们说东道西。深夜的恐惧,来源于人们喜欢在恐惧时说鬼事。师傅们说,厂区的西北边,原来有一排宿舍,修建这些房子时,下面挖出来的不少白骨和“麻钱”,想必是个很大的坟地,但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从陪葬品看,可能是平民的坟地了。师傅们还说,厂里有一座房子,人住在里面,半夜时分,总感觉床在动弹。我不以为然,偏偏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对对对,是是是,我在那房子里住过的。”此后,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经过那间宿舍时,不禁头皮发麻,还说,那座旧窑楼,八十年代初发生过喷窑事故,火光弥漫了整个窑面,人无处可躲,一个职工从窑上掉了下去,没有抢救过来。我不知道什么叫喷窑,又不敢多问,一直把这事当做迷,而在窑下作业时,又不由自主地想,他是不是落在了我脚下的这个位置?瞬间,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仿佛横陈在眼前。
我多次在班后爬上高高的窑楼,眺望远处。
新疆至上海的公路是国内最长的国道干线。路边有许多县城、村落,也有许多工厂,包括冒烟的工厂。东北边有座叫“烽台”的山(我原以为山上至少有一处烽火台,但没有,与古代的烽火台不沾亲带故),山上有三棵松树,据说是宋时的,这山就与周边的山与众不同了起来。与众不同的还有,山上有座三将军祠。祠不大,不过是间简陋的小屋,陈列着三个牌位。很明显,祠的规模与三位将军的身份极为不符,后来知道,原来的祠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便想,这三棵松树,一棵代表刘铕,一棵代表吴蚧,另一棵便是吴璘了,山叫“烽台”,也有了稍合理的道理。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山上包裹着一层淡蓝色的烟雾,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我站着的这座窑楼产生的。也好,有了这“雾”,山在霞光中,有了些神秘,我曾经打定主意要和古人完成一次对话,但一直没有深入下去过。我的这个行为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总有人走出来,说:“你在做啥呢?”我说:“我在看山呢。”他也朝山看上一眼:“山有啥好看的呢,不如缓着去。”我便歇息去了。
岗位是枯燥乏味的。时间长了,内心深处对日复一日的工作产生了厌烦,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有时,盼望着设施不太正常,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闲下来的机会。这样机会还是有的,尽管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但车间有要求,不能回到宿舍去。曾记得另一车间,一员工趁这样的间隙回到了宿舍,开机后不见他上岗,派人去找,宿舍门关着,一股橡胶味从门缝里透了出来,赶紧撞开房门,发现他已经死亡。原因就那么简单,他偷偷用电炉子烧水喝茶时,不小心触电,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纪律有它的道理,那只剑,就悬在不听话的人头顶之上。那么,我可以在厂区走走看看。六十亩大的生产区,到处充满陌生的诱惑。朝西,几百米,到了三车间。三车间四层高,不敢进去,站在车间门口朝里张望,一楼偌大的空间里,好像只摆了一件钢家伙,它缓慢地转动着,洒到身体上的水,很快蒸发,热雾升起,不多停留,很快散尽。后来知道它叫球磨机,不去车间还真不知道它吼声均匀、高亢。再朝西,一排平房,干净漂亮,不像其它车间灰头土脸。透过玻璃窗户,看到三五位穿着白色长褂的女工晃动,持着检验器皿的样子煞是好看。想进去,见门口写着“非工作人员勿入”的字样,立刻停下了脚步。
很少与车间同事交流闲谈,也不太和本组同事说话,我们之间只是劳动的默契和机械,一个动作就会明白意思。只是按时到岗,准时回家。若实在劳累,匆匆洗一把,上床休息,本想眯一会儿,却酣然大睡。有时,突然就有说话的冲动。比如,白天人多,往往将来来去去的同事、领导忽略。晚上则大不一样,人少,路灯亮起来,气氛显得孤单枯燥。如果想说话,无非是打发冷清,或者清除睡意。守着链运的地方,东西贯通,除了窑下出来的热浪,就是由西刮向东边的风。风窜了进来,被东边的墙壁一挡,又折了回来,经常其中包裹着灰尘,细尘直奔衣领,颗粒稍大的,甩打在脸颊上。每遇这种情形,我会选择堆场躲避,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过问。这时,会从幽暗处闪出一个人,直奔过来。灯光下,看清他手里提了一根铁棍,腋下夹着本子,他将铁棍用力插到料堆中去,看看铁棍上的刻度,记在本子上,马上转身离去。有次,我从料堆上翻了起来,问:“你这是做啥?”他说,在测算小时产量,每天抽样四五次。他看不清我的脸,我戴了防尘帽和防尘口罩,熟识的人只能从声音上分辨。此后好多次,我总会问他:“是多少?”他会告诉我一个大约数。还问过他年龄和学历,二十五六岁,某专业院校毕业。便心中生出些许羡慕和感慨。两月过后,抽样的人换了一个胖得可爱的老头,他看着我,好像熟人似的,呵呵地笑着,让人想起胖佛陀。肯定是我开口问了,他告诉我,上次的那位调走了。后来,调走的那位成了我的主管。
从来没有想过,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被调走。
有次,趁链运缓慢转动的间隙,去离我最近的库底转料岗位去,发现这里有只暖水瓶,心里一阵暗喜。由于岗位燥热,补充水份似乎成了我们的劳动习惯,我带到岗位的一杯水远远不够身体所需,一直想把水壶拿过来,一是觉得麻烦,二是担心被打碎。附近有水壶,实在叫人高兴,便折身回去取了水杯。我还在倒水时,从角落处闪出一人,女的,包裹着工作服,看不清模样。她允许我倒水,还简短地聊了几句。就知道她的丈夫也在公司内,秃顶,微胖,可惜我当时不曾见过他(认识他不几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她说,她见过我,前天培训时我坐她前面。第二天培训时,有人喊我的名字,从声音里知道是她,仔细打量,她的头发稀少,脸膛上有酸碱腐蚀过的痕迹,算不上漂亮,但觉得她端庄善良。她说,老师讲的速度太快,她跟不上作笔记,希望课后把我的笔记借她。第二天还我笔记时,她说我的字写得真好,肯定有文化,不会在车间干长久的,总会有一天被调走。
业务培训是新员工的必修课,而这次属于综合培训学习。西边综合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里,铁架子支了一张涂黑了的木板。化验室的技术员,一连讲了七天,我在本子上也认真记了二十多页。我本来化学学得不好,那些符号和元素记得歪歪扭扭,至今没有弄清三氧化二铁、氧化钙、三率值、饱和比。几个月后,说是要进行考试,考试内容都是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大多数人笔记做得马虎,所以我占了不少便宜。考试现场并不像高考那样严格,既便是放开抄,也有很多人找不到答案。因此,我的一份卷子成了传抄的范本。传至我手里时,已经面目全非,只好重抄了一份。
而重抄的这一份,可能是令同事们羡慕的一份答卷。国庆过后,我从车间调离。
时间摇晃间,数年过去。2012年春风浩荡时,我再次走到窑楼之下。此时,听不见机器轰鸣,没有灰尘漂浮,四周安静得冰冷。抬头仰望,天空明净,日光刺眼。这是我最后一次徘徊于曾经劳动过的车间,谁都知道,我试图依赖一生的公司,已经从企业名录中被抹掉。
是的,我再次想起曾經奋斗过的同事们,恍惚看见那些岗位上晃动的身影。我——念叨着他们的姓名,却不知道他们奔波在何方。这时,一切是那么的让我眷恋,那么的让我温暖,而又那么的让我心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