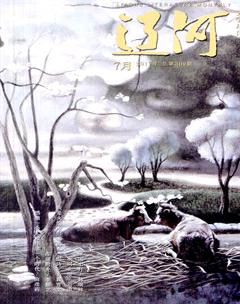荡漾的夜晚
隋言
我把小狗妮妞装进一个干净得没有一丝浊泥的蛇皮袋子里。它黑而油亮的皮毛光泽已经褪尽,四条腿僵硬得像几根粗硬的枯柳,紧闭着的两只眼睛和呲牙咧嘴的样子,显示出它死前痛苦万分的情状。我想把它埋在这个苍蝇岛上,我害怕它孤孤单单没有陪伴,想来想去总觉得苍蝇岛是个不错的地方。
苍蝇岛密匝匝地丛生着一堆一堆的苦了拉巴几的芦苇,葳蕤着一段不可理喻的时光的碎片,像一段苦不堪言的旅程。这回它迎来一件令人多少伤感的东西,我想,今后的岁月,它一定能够有一点别样的气息了。
一想到小狗妮妞的生前可人的点点滴滴故事,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丝丝的怜悯与隐痛。我认为动物的死也要有个去处,它们的灵魂不能游离于天地之间,这是谁也更改不了的定律。但是,妮妞的死却不该是这种死法,这太过于残酷与悲催,我的心情能像这银白绵长的河水,此起彼伏,终日倾泻,却难觅归期。
它是一只漂亮聪明的小狗。耳尖温柔地耷拉着,粗粗的嘴巴给人一种憨直敦厚的感觉。它陪伴了我多年,像影子一样缠着我,若一股温暖的气息。前段时间,许是找不到我迷路了的缘故,竟然一去不回。我简直急疯了,害怕它在大街上流浪,害怕它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流浪狗。那街上流淌不尽的车流都成了一道铁栅栏了,它哪能穿得过去?一不小心,它就彻底地完了。
直到后来,小狗才回到我的屋子里,静卧在我蜗居的斗室一角。可之前,它已经在这座城市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死去了。
在苍蝇岛的南面,迎着闪烁着银羽般月光的地方,我弯下腰,蹲伏下身子,将双手抠进温软潮润的细沙里,左一下右一下使劲刨挖着,一个小坑很快出现了。这是我给小狗制造的坟冢,是它的逍遥之地,我要把小狗掩埋在这里:我可怜而又可爱的妮妞,这是你的世界,这里并不孤单,也不冷清,我把你葬到苍蝇岛上,是想给你找到一个家的方向,这水就是你奔走的脚步,那流水的轻喘就是你酣畅的吠叫,那银羽般的月光就是你凝视我的目光。你好好在这里永存下去,你不会寂寞,一有空闲我就会来看你。请相信我,我会把你装在心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一个念想,我一看见苍蝇岛,我的思念肯定会开出一树茂密的花朵。
能说什么呢,我的心里像荆棘触碰了一下,疼痛地哆嗦了起来。我知道,日子从此可能就要像这月光进入一片白汪汪的世界了。趁着这个夜晚小狗气味还在,我要留下点什么,一定要留下点什么。可是,这能是我最后的执着与不舍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站起身,扑了扑手中潮润米粒一般大小的细沙,朦朦地看着脚旁小狗的坟茔,心里陡地再次泛起一股生硬腥咸的酸涩,一步一步地向苍蝇岛我的来路走去。
我刚起步,一个体态娇俏的人,背剪着手向我迎过来,黑黑的影子峭楞楞像只忧郁老迈的苍鹭。我的心里陡地一惊。此刻,苍蝇岛上已经没有第三个人,本来这里夜晚少有人迹,何况这么晚了。
你想把它放在哪儿?你要它跟你一辈子吗?这是我的地盘。
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从无杂质的空气中轻轻地穿过,倏然间,一下子连尾音又被河水带走了。
我停下了脚步,定睛看着她的步态与身形。
我感觉这个女人很是奇怪:怎么这里出来一个人,好像还是个年龄不小的女人。这么晚了,谁家的女人跑到这里疯疯癫癫地说梦话?好霸道的侵占,这么大的苍蝇岛是她的地盘?白痴,神经病,疯子!
我下意识地跟在她的后面,走到苍蝇岛的另一端。女人站定的一瞬间,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有一种掉进深井里去的感觉。我打了一个激灵,银色的月光下,我认出她就是我在医院门口见到过的那个女人,不错,就是她,可是,她在这里做什么?她为什么来到这里?我的心里倏地一抖,像热水流过皮肤,忽然间,留下一片波动的温暖。我抬起右手,慢慢地举起来,轻抚了一下躁动不安的胸脯,谢天谢地,真的是她?是她吗?一定是她吗?没错,是她。
她转身离开的影子被罩上一片苍郁斑驳的银白,像银鼠炫耀自己的光泽。
我坦诚,我是被她攫住了,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个神秘的符号在她的眼里晃晃荡荡。
我转而想想,这好像不太可能,甚至有些荒唐,荒唐吗?别人能来苍蝇岛消遣,她为什么不能来?别人可以在晚上逗留苍蝇岛,她为什么不能?可她为什么把苍蝇岛占为已有?我心里开始进行诡秘地寻找。
我承认,我是个享受主义者。不喜欢金钱却喜欢玩乐,兜里没有大把大把的钞票,是个人见人不爱的穷光蛋。也没有强健魅人的体魄,却爱往人堆里凑热闹,更爱一个人捧着一本发黄泛着时间皱褶的旧书,醉在晨风里摇头晃脑啃读一番,样子绝对滑稽可笑。也爱与潘雅这样的红颜知己,就着一口脆生生的花生米,或者一根清香甜脆的细黄瓜,吹上几瓶泛着白沫的啤酒,满嘴胡言乱语,穷吹乱侃。
这些都是我的生活中经历的东西,唯独爱情不太懂,傻里傻气不明白。潘雅闲时,没少拿我开涮,嘲笑我是个没有爱情却有真情的小男人,想打一辈子光棍的懒汉。
你不能把狗埋在这里,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孩子的家,他不在了,我要给他找个窝。
女人像一群贪食的蚊蚋突然遇见鲜血,发出一声细弱却狂乱的叫声,再次乱糟糟地响起。说不上什么时候,女人又出现了,却是在我的背后。
我要给小狗找一个灵魂的归宿,就像你说的一样,给它找个家,一个美丽的家,这个你不懂。
家?你说找个家?
对,找个家。
兄弟,你想把它放在哪儿?你要跟它一辈子?
你说我要跟它一辈子?不,这個小狗跟不了我一辈子,它死了,真的死了。正因为它死了,我才要给它找一个家,不然,我就没法快快乐乐地活下去。你不知道,我的小狗死了,我的一颗心差不多也要完蛋了,但我不能因为一条狗就这么沉沦下去,我还年轻,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我想来想去,把小狗埋葬起来会更好些,我的心灵也就获得了一种温暖。苍蝇岛是个好地方,这里人多嘈杂,小狗不会孤单,这个岛上一定是它灵魂安息的地方。大姐,你有点隐士的味道?endprint
隐士?我像吗?隐士与一个男人在一个小岛上鬼混?兄弟,我看你才真是个神经病,你这么年轻怎么就神经病了?我不明白。她哈哈大笑,这笑声像被一层层盐水卤过多天,咸唧唧地发涩。
我是个神经病?她才是神经病呢,这个苍蝇岛怎么就成了她的家?你的孩子死了?我该相信你说的话?也许是吧。她说我是个神经病,我认为这是一个荒唐的玩笑!简直是一个天方夜谭似的玩笑。她说我是神经病,我才不是呢,我是来埋葬我的小狗妮妞,你来这里干什么?是你迷恋苍蝇岛的夜色,这美丽的月光?她说孩子死了,就是那个她在医院抱着的孩子?她没说谎?
你不让我把它埋在这里,那我的小狗就没有家了,他的灵魂就没地方可去了。
我不管你的狗有没有灵魂,我可是有灵魂的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存在。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存在,他死了,确实死了,我不骗你。
可在这个月光白得傻憨憨的夜晚,多少让我想入非非,但又不敢过多去想。我怎么看这个娇俏的女人都像个精灵:月光下有着姣好的面容,一袭黑色衣服,头上围着一个黑色的围巾。假如是在白天,她的衣服许是浅蓝色,或者是深灰的颜色。月光下,我只能认定她的衣服就是黑色,青飕飕的有飘然欲仙的神韵。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出现再次让我进入一个纷纷扰扰的内心。
也许我的感觉是正确的,她就是我在医院见到的那个女人。她真像个精灵。我的心里踟蹰不定,惊异的目光随着女人来回移动,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我不会打扰你,这是我的一次贸然造访。那次在医院,是的,在医院的大门口,那天晚上也像現在一样,月光冷清清像一枚枚银羽一样静静地飘落。你……我真不好意思……我是个小气的人,是个糟糕的人,不,说得好听一点,是个谨慎的人,是个不想上当受骗的人,怕人纠缠,更怕人欺骗,所以,我宁愿躲得远远地看着你,也不愿意靠近你,给你一点点帮助。哦,我想起来了,你一定是那个人了,请原谅我刚才对你的不敬,说句老实话,刚才,就是刚才,我还对你怀着一股愤恨之情,我觉得你是一个霸道的女人,一个好好的苍蝇岛怎么就成了你的地盘?可是,我明白了,你要给孩子找到一个灵魂的归宿,就像我给我的小狗妮妞安个家一样。但我又不懂,你怎么来到了这里?
我想起曾经在医院的门口见到她的一幕,心里一阵刺痛,眼里酸涩地充盈着泪水,转过身,想走。
兄弟,你真要给它找个家吗?有家的感觉真好。我给孩子找个家,就是让他有这种感觉。
我走了……请原谅我的过失!
你真要走吗?为什么不好好留在这里?兄弟,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家,这家到底是什么?你能告诉我?
真不骗你,你是……你是医院……你是医院门口……我……对不起……实在对不不起……我不该……我不该那样对待你。你认不出来我了。我的眼里潮湿起来。
女人慢慢地向前挪着步,一点一点向我靠近。
突然,女人张开双臂扑了过来,把我手中的小狗夺在自己的手上,抱进怀里,转着圈地小跑起来。
白花花的月光洒落她一身,瞬间,又似一片片羽毛轻轻地飘落下来。她抱着小狗,焦躁地来回走着。
我惊悚地向后退了一步,眼前溅起女人迷幻的光斑,雾糟糟地袭来。
苍蝇岛是她的地盘?她神智不清?她太不可思议了。
女人扭转身,蹲下来,背对着我抽搐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地颤抖。
孩子……你的难过就是妈妈的罪过,你让妈妈怎么办?让我去跪大街吗?
女人面对着月光,把小狗轻轻地放在地上,一遍遍地用手梳理它的羽毛,又轻轻地拍了数下,一下一下挖着细沙。
她一下一下向小狗身上扬着细沙,动作粗疏得要命,诡异般地生动异常。
我看见她眼角的泪花被月光一晃,晶亮柔软如星子。
我无语地呆呆站在那里,胸脯塞进砖块般难受,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像个迷蒙无期的雨幕。
这里没有城里熙攘般的喧嚣,只是渺阴寺就在迷迷蒙蒙的不远处。我曾多次去过渺阴寺讨问自己的命运,有位大耳朵僧人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命犯桃花,恐怕得有女人指点你的性格缺陷,但不用担心有女人会对你纠缠不休。”
在这个掩埋小狗的夜晚,难道她是拯救我情感欠缺的女人?
我有点发呆,抹了一下泪滴,不知所措,两手不知所以地来回搓着。我不敢去想象她就是我在医院门口见到过的那个女人,但她确确实实地站在我的面前,而且毫无疑问地就是那个女人。
女人依旧那么一下一下地两手用力挖着细沙,往小狗的身上一层一层地抛撒。一会儿的功夫,小狗就不见了。
她突然站起身,把后背硬硬地留给了我。
女人嘟囔了一声,轻飘飘地走了,娇俏的身影被一丛丛月光下色呈墨绿的芦苇淹没得无踪无影。
我又钻进这个嚷熙的城市,在太阳的光芒下看着来来往往穿梭的人群。
我回家了,躺在软床上,吃了一点东西。我进入了一个幻想,把苍蝇岛上的女人作为我的幻想对象。
这是我的生活习惯之一,我有时非常喜欢这么做。
我的心里堵得慌,想起在医院门口见到过的一个情形,于是心里往死里认定“岛上女人”就是那个女人,而且准确无误地作出了判断。我暗笑自己,也开始一遍遍否定自己,甚至不止一次。我心里一遍遍地开始追问:我是变了,真的变了。我的内心如此残酷,又如此卑劣,我该怎样赎回我罪孽深重的一幕场景。
那是去年冬天发生的事了。
在一个医院的门口,我正要赶公交车,看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单位的楼下就是公交站点,对面就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大街上没有了多少行人,刺骨的冷风飕飕地刮过,早已打透了我的棉衣。几辆出租车在医院的大门口兜圈子揽活儿。公交车是最后一班车了,干等也不来,急得我直跺脚,围着原地直画圈圈。有时苦于囊中羞涩,没有急迫紧要的事,我从不打车回家。偏巧,那晚,感觉医院的门口处的街灯不够明亮,抬头仰视天空,西边倒是有一抹缺月,瑟缩着身子,寒战战地看着人世。不知什么时候,一个柔软的声音扎进我的耳朵。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耳朵,扭回头,却发现一个女人正站在左侧看着我。她的眼睛很漂亮,尽管眼神呆滞,傻里傻气,不够明亮的月光下,依然能看出几分秀气。她看人的神情却像是笑吟吟的样子。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生怕别人抢去似的,紧紧贴着她的身体。她的孩子五六岁的样子。她一只手搂紧孩子,另一只手羞怯怯地伸向我,口里喃喃着说着什么。endprint
兄弟,我一看到你,就感觉你是个好人,帮帮忙吧,我和孩子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孩子病了,我的钱花光了,连住宿的钱都没有了。
我于是暗想,骗子不少呢,有多少人摆出一副可怜的姿势上街乞讨,随后要到钱就下馆子大吃二喝。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内心甚至鄙夷起来。我扭过头继续等公交车,对这个女人毫不理会。我稍微扭动了一下身子,眼睛的余光却发现女人的手还在空中伸展着,最后慢慢地落了下去。许是抱孩子累了的缘故,她把孩子托起,头压在她的肩上,又迎在我的前面,那只手又抬起来依然一动不动地伸向我。公交车终于来了,我急切地向车走去,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发现女人的手在空中慢慢地落下,两手托住孩子的屁股,孩子的头埋在她的怀里,她把脸贴向了孩子的头。
我回家了。月亮银白,是个缺月,月光白惨惨的亮得怕人。我没有开灯,取出一个杯子刚要倒出热水痛饮一番,心里却七上八下忐忑不宁。我抓起刚刚褪下的羽绒服,急匆匆地向街心走去。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催促司机师傅快点开车。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出租车就到了医院门口。我左绕右转,始终没有找到抱着孩子的女人。
街上早已没有了行人,月亮亮了许多,无声无语地向西天滑落。瘦硬的风干巴巴地直往衣服里钻。我的心里涌起了浓浓的惆怅和自责,为自己的冷漠与无情。这惆怅告诉我,这经历的感受会让我痛上一阵子。
转天,我又在医院的门前转了一圈,恰巧看到了那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我的眼前一亮,急忙走上去搭讪。掏钱。许是她认不出来是前天晚上我拒绝了她,依然眼睛呆滞而温温地看着我。只是眼角多了两滴泪花,嚅动着嘴唇想说什么,到底没有说出,就抱着孩子走开了。我看到她一步一步沉重的背影,我想上前说上几句,又顺手将手插进口袋里掏钱,话到嘴边,却听到女人的身后飘过来一句话:我的孩子死了。
我没有打开灯,而是点上了一根差不多有胳膊粗的大蜡烛,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大大方方地供了起来。
我的心里之空洞,像一粒尘埃落进大风里,无声无息,没有归期。我拿出一瓶高度白酒来,倒出一小杯,放在蜡烛前,用蜡烛黄温温的火点着,又倒出一小杯留给了自己。看着蓝汪汪的酒火上下跳跃着,我捏紧酒杯的手慢慢有了温暖,心里一点点沉静下来,并无比欣慰地自语:生活太过于美妙与神奇,让我体会到了爱恋与挂牵。
我得感谢潘雅,是她送给我的蜡烛,她说那是渺阴寺里点过的蜡烛,开过光,是沾了仙气的灵物,凡是心里有想不开的地方,拿出来点上个把小时后,脑袋就灵光了,心里也不混杂了,我给潘雅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昨天晚上在苍蝇岛遇到“女人”了,她帮我掩埋了小狗妮妞。
转天,我又搭乘着那个呼呼冒着黑烟的小轮船去了苍蝇岛,不过,是在白天,不是月白星稀的晚上。
我在掩埋小狗妮妞的旁边,把鞋子脱掉,坐了下来,把脚伸进细软的沙子下面,任由清风呼呼啦啦一阵阵吹着因睡眠不足略显臃肿的脸,看着悠悠的河水一刻不停地流走。每次来到苍蝇岛,我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这次我格外注意了一下不远处的渺阴寺,它就在一片雾蒙蒙的水汽里。听得见晨钟的声音一下一下软绵绵地踏波而来,不由得心里隨着这钟声一下一下发紧。我想:我的确是变了,变得胆小了,拘谨里布满了密匝匝恐惧的棘刺,扎得我好难受。我要死了,我的确是一个不可原谅不可宽恕的罪人。我恐怖的棘刺里混杂着懵懂和好奇,盲目和理性,这既不是快乐的,也不是忧愁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有一种东西在牵引着我,魂牵梦绕般左右着我的灵魂,使我再次悄无声息地来到岛上,是为了那个女人吗?我无法确定自己的内心。
我该做些什么?我要找到她吗?我要对她说些什么吗?她还在这个岛上吗?我还能见到她吗?我不知所措。
我坐在那里,双手抱膝。背身有个凉亭,叫渺阴亭,周围一圈小凳子,上面已经坐满了人。我无意留心这些来来往往的过客,却一遍遍地回想起了过去。
老实说,过去是个心酸的词汇,里面的注解苍郁得可怜又可悲,是因为过去的杂乱无序吗?是因为过去的失意惆怅吗?不是,也许又是。但我会铭记一个深深的烙印,比如说,那个抱着孩子伸手向我乞讨的女人,我一回忆就会有许多疼痛的东西,里面藏着一大堆黯淡的碎片,像一根根银针闪烁着光亮。
明灿灿的阳光流泻一身。我的后背被重重地拍了一下,头上随后被扣上了一顶鸭舌帽,回头一看,是铁姐潘雅。她依旧是那个不拘小节的样子,嚼着口香糖,一副墨镜软塌塌地挂在鼻梁上。
想什么呢?是不是到这里来找艳遇来了?看见“岛上女人”了吗?不要悲观。悲观的男人有一股酸气,让你身边的女人甚是不爽。这是诗意的哲学,是人性最美丽的一种遮掩。
我想,我的眼神里一定是飘忽着不自信,向着远方绵长奔腾不息的河水。
“岛上女人”?你怎么也惦记上“岛上女人”了?与你非亲非故,我不想让你提到她。
潘雅扶了一下墨镜:什么也没想?不会是到岛上来闲逛的吧?你这个家伙我能看到五脏六腑,一有心事就喜欢钻牛犄角,我可没看到你来过几回苍蝇岛。你不想让我触及这个人物,恰能证明你对她内心的澎湃之情。任何人要做一件事都不是没有来由,这是因果的一种对应。我知道,你这次来到苍蝇岛,你的小狗不是决定的因素,你对这个曾经的生灵只是一种怀念,但我相信你对那位女人却是赤裸裸的牵挂。我在你的身上能够看到现实主义者的影子,而非浪漫主义者让人生厌的作秀。
潘雅目视着远方,一脸肃然的神情。
你的脸擦得这么白倒是让我想起“岛上女人”了,有月亮的晚上看到她和你一样的白淨,很漂亮。我没话找话地回道。
我深切地知道你惦记着“岛上女人”,她长得一定很漂亮。不过,这不是你来苍蝇岛寻找她的借口和理由。我知道,这个世界有那么一种心情最为珍贵,就像你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情,它不是在唯我的世界里绽放色彩,却是在人性的光芒里助燃闪光。
潘雅转而拍了我肩膀一下。
从今往后可能不会再见到她了。endprint
嗬,失落了?我想,好心能惊天动地,善意能让你成神仙。走吧,我们去渺阴亭喝冷饮,给你消消火,心里窝着一团火活得不会开心。赶走猴子才净心,拔出萝卜地皮宽。潘雅斜了我一眼。
我收回细沙里的双脚,随着潘雅懒洋洋地走近渺阴亭。我像潘雅说的那样,我真的放心不下“岛上女人”,我觉得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很小,十分敏感,也十分脆弱。假如生活欺骗了我,我是不是得向命运低头?我真的惦记着“岛上女人”?她还在苍蝇岛上?
我一时间好像忘记了自己是谁,要去哪里。我的心思慢慢放空了,形成一个无所依附的空洞,慌落落地深不见底。河水和远处建筑物的影子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地燃烧,波动的纹路一下一下地向着远方传递。我感觉自己变了,这不是过去的记忆辜负了我。我的心里裂开了一道缝,俨然成了不是几天就可以弥合的一眼深井。
我漫无心思地跟在潘雅的后面,渺阴亭已近在咫尺。我有一种空落落心无归期大梦难合的感觉,一丛丛芦苇的绿意恬静地涂抹着开裂的伤口。
我们刚落坐,有人却在旁边突然大声叫嚷起来:那个女人又来了。
顺着这个人手指的方向,不少人的眼光向着站在苍蝇岛边缘的一个女人投去。还有几个人唧唧喳喳边说边抓起身边的物件回避着。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女人已经来到了他们近前,从他们身边一擦身就过去了,径直朝向渺阴亭旁边一棵高大的桃树走去,动作伶俐得像只猫。她围绕着树干左转右转,又双手合十对着桃树作揖叩首。
女人穿着上下都是灰色的衣裤,站立在那里,脸上现出生动迷人的浅笑。只不过两眼呆呆地无神,一只手向着我和潘雅的方向平伸着,嗫嚅了一下嘴唇。一双埋在眼窝里的眼睛似乎颇为熟悉地瞅了我一眼。突然又一转身,奔向岛边的小铁皮船跑去,留下一个娇俏的影子在空中飘逸着灰色。
潘雅从背包里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根,点着,烟雾就笼罩着她被脂粉淹没了的老干干的脸。她用中指很绅士地弹了一下烟灰,眼睛看定渺阴寺的方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这个女人经常在苍蝇岛上逗留。她是一个死了孩子的母亲。大概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她刚刚五岁的孩子在医院里被检查出了白血病。她的丈夫扔下她们母子,在外面找了女人。她平日依靠捡废品生活,家里根本没有积蓄,她只能东挪西借凑点钱给孩子治病,最后还是没有保住孩子的性命,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死掉了。有人说,她一连多天一直抱着孩子在街上走,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淡漠了。两年后,有人在渺阴寺发现了她,她把孩子埋在了苍蝇岛上的细沙里,从那时起,有人就说她精神受到了刺激。
这是我的地盘,孩子,你有家了。瞧瞧,我学得像不像。她的身后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笑声。
我追了过去。
女人小跑了几步,跳进水中,想抓住那条铁皮船的边沿,船却故意开走了。又传来一阵歹毒的骂声。
这家伙可能真他妈的疯了!
她一个闪身,趔趄了一下。双臂在空中挥舞着,渐渐地,整个身子像一个飘带,悠悠地没进水里,不见了踪影。
我像受了重击,颓然坐了下去,又忽地跃起,跳进水里……潘雅也跟着跳进水中。
一个月过去了,我和潘雅再次来到苍蝇岛。在距离我们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就是小狗妮妞的坟头,上面倒是生出几株嫩嫩的绿草,还有一株摇曳的小黄花。没错,是带着香气长得蛮沧桑的那种小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