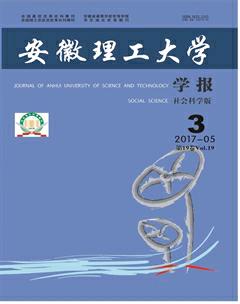宿命与救赎
钟珍萍
摘要:死亡是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主要意象,对死亡的理解是其小说中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桥梁。从中国佛教思想来看,死亡是一种宿命;而从西方基督教思想来看,死亡是一种救赎。在《接骨师之女》中,借助母女的冲突和和解过程中死亡意象的描述,谭恩美将两种宗教文化思想中的死亡观融合在一起探讨人性中的善与恶,显示了她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接纳,彰显了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巨大价值。
关键词:死亡意象;《接骨师之女》;宿命;救赎;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I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7)03008404
Abstract: Death is the significant image in Amy Tans novel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death is the important bridge connecting different figures in her novels. Death is a destiny in Chinese religious thinking, and a salvation in Christianity. In describing the process of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the novel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my Tan explores good and evil hidden in human na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view of death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and Chinese religious thinking, which fully proves her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her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Death image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Fate; Salv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自古,死亡是中外哲學和宗教领域永恒的主题,也是文学创作领域中的重要关注点。死亡也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五部长篇小说无一例外都着力描述的意象,《接骨师之女》被誉为“她几本书中最好的作品”[1],对死亡意象的描写更颇具张力。在这部小说中,露丝充当“通灵者”的角色,主要描写和塑造了三代女人——外祖母宝姨、母亲茹灵和女儿如意(露丝)复杂而细腻的情感关系。在小说叙述中,她以时空交错的手法,借人鬼互说的方式,勾勒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的各种人伦风景,展示了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冲突和融合。
目前学界对谭恩美的评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把她纳入美国华裔(族裔)文学的重要力量进行跨文化考察;二是用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叙述特色、伦理文化等对她的作品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死亡意象是谭恩美小说的主要主题,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死亡主题是揭示女性悲惨命运的有效手段,是愚昧而神秘的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强权政治下弱势文化的一种书写,但较少研究者从宗教的角度去探讨谭恩美小说中死亡意象的作用。本文以《接骨师之女》为例,结合谭恩美的生平经历,试图探索中西方宗教思想对作者死亡意象艺术处理的影响,并探讨作家死亡观的形成背景和在作品中的折射作用,更好地理解作家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一、中西宗教交融的死亡意象
死亡意象不仅仅是狭义上生命的终结,更包括和死亡相关的一系列意象,如魂灵、通灵者、人鬼互说等[2]。死亡意象是美国华裔作家,特别是汤婷婷和谭恩美,或详或略加以运用的意象。从《女勇士》中的群鬼乱舞,到《接骨师之女》的魂灵沟通,再到《百种隐秘感觉》中人与鬼的对话,鬼魂以及相关的死亡意象,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展现作家写作意图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华裔作家栖居美国,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创作时又融入了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因此在死亡意象的运用上,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西宗教的交融和汇通。中西宗教混合背景下的死亡意象既包括作者对中国佛教等宗教思想的理解,也暗含基督教思想的浸润,呈现出一种宿命与救赎并重的色彩,认为人的死亡本质上难逃因果报应的循环,却希冀通过理解和宽容达到精神上的救赎。在《接骨师之女》这部小说中,带有中西宗教交融特色的死亡意象是推动母女关系发展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两对母女(露丝和茹灵、茹灵与宝姨)之间的冲突、对抗和和解都是与此分不开的。
成长在中国的母亲茹灵与出生在美国的女儿露丝关系一向紧张,她们的矛盾在茹灵频繁地以死来威胁、对魂灵的敬畏和依赖中不断升级。露丝年轻时以激烈的行为反抗母亲的管教和威胁:她在日记里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强烈不满和憎恨,这也让偷看日记的茹灵差点自杀;滑梯事件升级了两人的矛盾,母女关系陷入无法缓和的状态。当茹灵日益老去,她的老年健忘症让露丝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这时,露丝读到了茹灵早年写下的回忆录,了解了母亲的坎坷身世以及外祖母宝姨的悲惨命运。露丝重新认识了母亲,最后和母亲和解。
小说中这对母女的关系通过自杀和死亡层层演化,而另一对母女宝姨和茹灵所有交织的爱恨也是在宝姨自杀后才得到化解:茹灵通过宝姨留下的信件了解母亲的身世,在生活中通过露丝这个通灵者和宝姨鬼魂进行对话,对死去的母亲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和顺服。而露丝也对这个外婆有了全新的理解,小说的末尾写到:“露丝和外祖母肩并肩地开始写作,文字自然地流淌。她们变成了同一个人。”[3]238通过鬼魂,借助茹灵通灵者的作用,谭恩美完成了这种打通时空和阴阳的死亡书写,将母女关系推进到相对融洽而和睦的关系。小说中她对死亡意象的运用,不难发现她对死亡的理解,既有来自中国宗教思想的影响,也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底子。endprint
二、死亡即宿命—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
小说中宝姨的形象是露丝在茹灵的回忆录和平时的生活点滴中勾勒出来的,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两次自杀:生长在接骨世家,独立而刚烈,得知未婚夫和父亲的死都和张老板有关时,她选择了自杀;她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茹灵,茹灵却一心想嫁给她仇人张老板的儿子,宝姨阻拦不成,只好用死来抗争。宝姨死后,婚约解除了,正如宝姨信上所说,父辈的毒咒也缠上了茹灵,缠上了杨家,杨家店铺被烧,家道开始没落。
而茹灵自小也耳濡目染各种关于生死和鬼魂的传说和故事——老奶奶口中梦中的“沪森”,以及村民口中 “穷途末路”是“阴曹地府”的说法,让她心生恐惧,有了对死亡的认知。宝姨的自杀,让她对死亡产生恐惧;在育婴堂,她也目睹了战争带来的死亡,她第一任丈夫的死亡更是让她深信她命数里逃离不开祖先的诅咒,是一种因果报应。因为宝姨的父亲——死去的接骨师大夫曾托梦给宝姨,说:
“你手里这些骨头并非龙骨,而是我们家人的骨头,就是那位被压死在猴嘴洞的先人。我们偷了他的骨头,他咒我们,所以我们全家差不多都送了命,你妈,你哥哥,我,还有你未婚夫,都是被祖宗咒的。况且,并非说人死了就算完了。自打我来到阴间,老祖宗的阴魂还老是糾缠着我。”
“把骨头还回去。除非把骨头物归原主,不然他决不会放过我们的。下一个就是你,我们家将来的子孙后代也脱不了咒怨。自己的先人找你报仇,最最要命。”
“要是我们把骨头卖了,毒咒就会重新找上我们,鬼魂会把我们连同我们这把小骨头都抓走。……告诉你吧,不把我们全家人都折腾死,鬼魂就没完。什么时候我们家人死绝了,才算完。”[3]169-170
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和宿命论的观点和谭恩美的经历分不开的。《接骨师之女》是她个人色彩极浓的作品,她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投射了她外婆、她母亲和她个人的经历。她在随笔集《我的缪斯》中提到,宝姨的原型是她的姨婆,母亲鬼神、命运观念对她的耳濡目染是作品中宝姨对露丝的影响,而且好朋友埃里克、编辑费思的死都是她小说的灵感源泉,她还把它们看作是其创作的“缪斯”。“真的是亲朋好友的鬼魂归来,成为创作的缪斯吗?……鬼魂显现正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充满爱的情绪超越平庸的生命体验,在生活中绵延不绝。”[4]190她相信虽然母亲和好友已去世,但她们的灵魂仍在指引她完成创作;而谭恩美遭受的父亲和兄长早逝等不幸,也让她对中国宗教思想中的宿命论深信不疑。
小说中对宿命论的描述还可以从谭恩美母亲的行为中找到根源,“母亲信奉中国的宿命论,她经常把死亡挂在嘴边,死亡成为一种警告或是在劫难逃的事实。……母亲坚信我有一种超凡的天赋,能够看到鬼魂。……为了对抗厄运,母亲开始求助于来自她生活中的鬼魂,她向外婆的画像祈祷,请风水先生检查房屋。……狗儿的吠叫、放错位置的东西,某一个名字被提起时门忽然关上,诸如此类,这些在母亲看来都预示着鬼魂的出现。她相信,现实世界的无常变幻,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都可以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4]3-25
可见,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刻画和事件描述都来源于谭恩美创作思想中的中国宗教元素。因果报应论和宿命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就有不少关于因果报应的论述,《尚书.汤诰》有“天道福善祸淫”一说,而《周易·坤·文言》也谈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这种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报应观也就自然地成为佛教中的核心思想。《涅盘经》中讲:“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俗语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说明这个道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乏有因果报应的名篇,“三言”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其中的一则;而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名为描写宫廷斗争,也是充满了因果报应的寓意。《接骨师之女》中遭受祖先的诅咒而接连死亡也是作者因果报应思想的一个例证,属于“生报”,因偷了祖先的骨头,做了恶,不仅是接骨师全家会死,而且骨头不还回去的话,连累到了子孙后代,直到断绝后代。
虽然宿命论不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特有产物,但在中国的古代就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孟子·万章》上篇也谈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这些都说明了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天命有关,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改变。它潜在的含义扯上一点神秘主义,比如上天,人们无论怎样努力都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宿命是这种因果报应论的延伸,即佛教中的“宿命与轮回”。宝姨家人的接连死亡,未婚夫的死亡、宝姨的死亡、茹灵第一任丈夫的死亡、茹灵公公的死亡等,这一连串的死亡显得离奇而偶然,却又好像冥冥之中注定的。宝姨父亲的托梦,让这些人的死亡找到一个极好的理由,那就是因为有罪,受了祖先的诅咒,这个噩梦会一直持续下去。
结合谭恩美個人经历,《接骨师之女》以她外婆、她母亲和她自己的故事为原型展开叙述,就不难理解书里书外她对死亡宿命的恐惧和母女间爱恨交织的情感,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宿命论思想在她作品里的集中体现。她的其他长篇小说也有类似的死亡意象,如《喜福会》中吞鸦片年糕自杀的许安梅妈妈、《灶神之妻》中温妮年幼夭折的孩子以及《百种神秘感觉》中相信“恶有恶报”的婉的母亲。谭恩美在讲述这些人物的死亡故事时,都在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的思想。
三、死亡即救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但是,谭恩美的写作不仅仅是只受母亲宿命论的影响,她还受到了她父亲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她在《我生命的“克里夫笔记”》这篇文章里说到:“我看到自己由父母孕育而生。父母的基因结合成了一个兼具宿命论和信仰的混血儿。”[4]24 Nathan Faries[5]也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基督教元素是谭恩美小说中的重要因素。而赵健秀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称,谭恩美是个伪华人,她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是伪造的,“她把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相对立是伪装的,是她的基督教偏见造成的。”[6]虽然这句严厉的批评把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文化打上了“伪”的标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话揭示了作为第二代移民谭恩美的宗教背景,即,她是生活在基督教影响下的。endprint
基督教的影响渗透在她成长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她的父亲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要求孩子们餐前祷告,还给他们布道,并让他们上“诵经班”。谭恩美在接受《纽约时报》“枕边书”栏目采访,被问到哪本书对她影响最大时,她的回答是《圣经》。她每天都在听《圣经》,甚至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经文,“《圣经》的那种重复的节奏从童年起便已刻在我写作的脑海里了”。在采访中她还承认她写作灵感“受到哥特式意象的歪曲”,但通常都是与宗教的“罪与恶”有关。这些都间接地折射了基督教的思想和《圣经》等相关文本对她写作产生的影响[7],只是她作品中的东方故事题材隐晦地掩盖了她思想中的基督教色彩,《接骨师之女》中的死亡意象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宝姨用刚烈的自杀成功地阻止了执意要嫁给张老板儿子的茹灵,但茹灵的妹妹却嫁给了成天吸食鸦片的张福男,嫁进了那个“永远都在弄钱买鸦片”的“苦难之屋”。这样的情节安排让我们想起了《圣经》中的“替罪羊”形象。在《圣经·创世纪》和《圣经·利未记》中都有“替罪羊”的故事,原意为“给人类替罪”,后引申为“代人受罪”。西方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替罪羊”的经典形象,如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的唐泰斯,福克纳《八月之光》中的主人公克里斯默斯和霍桑《红字》里的海斯特·白兰;而谭恩美其他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替罪羊”形象,如《灶神之妻》中代替花生嫁给文福的温妮、《喜福会》中代替龚琳达嫁给洪天余的女仆和《百种神秘感觉》中用自己的生命完成对奥利维亚救赎的婉,都表达了作家对人性中罪与牺牲的思考。
谭恩美在叙述罪与恶的同时,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去救赎,让小说中的人物学会理解和宽恕,体现出一种基督教式的爱和通融。宝姨的死把茹灵从注定会失败的婚姻中挽救出来,茹灵进入了育婴堂,那里住着善良的修女们,她们用耶稣的爱保护着这些孤儿;战争中开京、老董和小赵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这些学生们的安全,修女们认为他们死后上了天堂,这让茹灵虽恐惧战争但已日益坚强。而在茹灵接下来的生活中,宝姨一直以一种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形象存在着,只要她遇到困难或难以选择时,她总是向宝姨的鬼魂求助;特别是到了美国后,她借助沙盘,把露丝当作通灵者,是否搬家、买哪支股票等这些小事都和宝姨的鬼魂沟通,跨越了空间障碍,实现了人鬼互说。最后,作家用基督教牺牲式的爱为母女间的宽容和解搭建了一座桥梁。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中国宗教文化中特有的因果报应、宿命论和鬼魂说的多次运用以及作家潜意识中的基督教救赎思想,让故事的叙述打破了现在和过去、在场和不在场、生者和死者的二元对立和界限,促进了两对母女的沟通和理解,实现了精神上的互通和感化。同时,东西方宗教思想的融合,让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更为突出,这也佐证了作家在接受Bookreporter采访时所说的: “我没有单一的宗教信仰,我相信宗教都有共通之处。我最不喜欢信一个教就必须自始至终地虔诚,相信一切有关的都是真理。我爱给自己提问,从自身找到信仰。” [8]这种东方叙事中夹杂着基督教式关于罪与恶和救赎的思想,体现了谭恩美不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之上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审视和批判,更不是伪中国文化的展示和基督教偏见下的产物,而是体现她所理解的“宗教共通之处”,吸纳了中西方宗教思想对死亡的理解,消除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从人的本性去探究罪恶和善良,更体现了人类在对待生命时的本真态度和饱含希望的坚定信仰。
参考文献:
[1]Edwards, Jami. Review of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EB/OL].(2002-09-22)[2016-06-01].http: //www.bookreporter.com/reviews/0804114986.asp.
[2]郑欣.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分析—以《接骨师之女》为例[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3:9-10.
[3]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 张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38,169-170.
[4]谭恩美.我的缪斯[M]. 卢劲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5]Nathan Faries. The Inscrutably Chinese Church [M]. MD:Lexington Books, 2010:114.
[6]徐颖果. 我不是为灭绝中国文化而写作的—美籍华裔作家赵健秀访谈录[EB/OL].(2004-03-04)[2016-06-01].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14759/21866/2373397.html.
[7]王文胜. 重负与神恩—论谭恩美小说中的基督教色彩及其文学价值[J].江苏社会科学,2014(2):174-179.
[8]张璐诗.谭恩美访谈: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EB/OL].(2006-04-14)[2016-06-01].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4/14/content_4423023.htm.
[責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