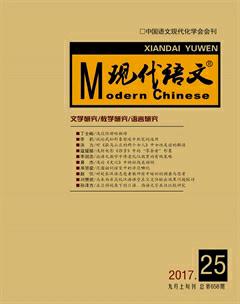从黑人民俗叙事策略看《他们眼望上苍》中的政治意识
吴良红
摘 要:佐拉·尼尔·赫斯顿是美国20世纪前期杰出的黑人小说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通过将黑人民间故事框架、布鲁斯音乐和黑人方言英语融入到叙事策略中,巧妙地形成了作品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学风格,体现了她先进于时代的黑人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了她追寻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和重构黑人文化身份的政治意识。
关键词:《他们眼望上苍》 黑人民俗叙事策略 政治意识
一、引言
佐拉·尼尔·赫斯顿是美国20世纪前期杰出的黑人小说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她一生致力于美国民俗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3部民俗研究作品,4部长篇小说,1部自传和大量的短篇小说。早期评论界对赫斯顿作品毁誉参半,70年代以后评论家们肯定了她在美国黑人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她对20世纪许多著名黑人女作家如格洛丽亚·内勒、沃克和莫里森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西方开始对赫斯顿作品从写作技巧、文化批评、跨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作品的推介、叙述策略、创作特色、女性形象、主题研究和黑人民俗等方面。对于赫斯顿作品中的政治意识,玛丽·海伦·华盛顿认为赫斯顿在种族问题等方面的观点不够明确,似是而非。事实上,赫斯顿通过对南方黑人民间文学进行理性思索,在作品中将黑人民俗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生动地再现南方黑人生活场景,表达了自己对黑人女性追求种族、性别和阶级平等的政治诉求。正如艾丽丝·沃克所说,“佐拉走在她的时代前面”,并“意识到黑人是作为完整、多元、未被简化的人存在”[1](P14),她还认为赫斯顿的作品表现出“种族健康”(racial health)。
二、黑人民间故事叙述框架
小说叙事结构模仿了黑人民间文学口头叙事的传统,即叙事的主要事件是讲述一个故事。这种叙事结构也被称之为框架叙事(frame-narrative pattern)。女主人公珍妮叙事的维度是出于为了满足好朋友费奥比和小镇人的好奇心而在家中跟费奥比讲述自己三段婚姻的故事。在故事叙述中,赫斯顿建构了双层叙事结构:外层叙事层面中故事外的叙述者即作者型叙述者讲述了珍妮对费奥比叙述自身经历的故事;而在内层叙事层面,作为故事人物的珍妮讲述了自身的经历。内层叙述者珍妮在外层叙事的故事中成了人物,珍妮的讲述成为外层故事的主要情节。美国文学评论家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认为,这种叙事框架“适合主题的需要,使珍妮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回顾、驾驭和叙述她成长的经历,而这种能力是洞悉自我的重要标志。[2](P76)
雙层叙事结构中作者型叙事者叙述了黑人女性讲述故事的故事,在增强黑人女性声音可信度的同时,构建了女性声音的权威。赫斯顿采用倒叙的手法开始叙述,女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回到伊顿维尔,此时的珍妮经历了3次婚姻,已经从天真懵懂的小姑娘成长为具有独立黑人女性意识的典范。除此之外,珍妮口才了得,是公认的“天生的演说家”[3](P92)。内层叙事层面的设置给了珍妮展开个人叙述,发出黑人女性声音的机会,但是当珍妮讲述完童年经历后,作者型叙事者悄然接替了珍妮的叙事者地位,继续进行框架故事的讲述,直到小说的最后一章,珍妮的叙述声音才得以部分恢复。作者型叙事者的主导地位提高了黑人女性故事的真实性。在内层珍妮讲述的故事中,作者型叙述者不断进入珍妮的内心世界,以冷静客观的语言展示珍妮的内心活动。作者型叙事者规范的书面语言和未受过正式教育的珍妮的黑人方言土语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拉大了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从而使读者能够客观地看待人物所讲的故事,增强对故事的认同感。在作者型叙事模式中,读者很容易将叙事者等同于作者,当叙述者获得权威时,作者也因此获得了权威。在小说创作的20世纪70年代,黑人女性的声音很容易湮没于这个白人和男性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因此,赫斯顿退而求其次,舍弃了直接利用黑人女性声音进行个人讲述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种族、性别模糊的作者型叙事者的讲述。当读者接受这个在模糊叙述者掩盖下的黑人女性讲述的黑人女性故事时,赫斯顿因此获得了女性的权威。
在内层叙事中,作为叙事者的珍妮对人生、婚姻和两性关系有着清楚的认识,也深知自己在黑人社区离经叛道者的身份。赫斯顿对珍妮的叙事同样做了策略的安排,她选择费奥比作为珍妮故事的受述者,一方面珍妮的故事更容易引起同种族女性的共鸣,另一方面,费奥比作为故事未来传输者的身份处在珍妮和社区邻居之间,给了社区邻居客观理性思考的机会,从而促使他们接受理解珍妮。此外,受述者费奥比在小说第一章出现,随着内层叙事的展开,受述者开始隐身,直到内层叙事结束,受述者才再次出现。受述者的隐身使读者在潜意识中成为故事的受述者,作者因此达到争取更多故事受述者的目的。黑人作家普遍面临不同种族读者接受的问题,他们如果想要赢得白人读者,往往要迎合白人的阅读兴趣和审美要求,但是达到这一目的又会面临得罪黑人读者的困境。赫斯顿正是通过将受述者隐身的策略吸引了不同读者,最终达到成功地向不同种族读者传达黑人女性声音的目的。
赫斯顿正是利用黑人民俗叙事框架的构建,以权威、自信的方式传达了黑人女性的声音,成为黑人女性自我价值观的赋权者。“女性的叙述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技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社会权利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4](P117)黑人女性声音的构建表达了赫斯顿反对种族、性别压迫的黑人女性主义意识,极大彰显了其作品的政治性。
三、布鲁斯音乐叙事
布鲁斯音乐最早起源于美国黑人在田间劳作时的歌唱,主要记录黑人痛苦的经历,其风格伤感忧郁,本质上是一种种族的音乐形式。许多黑人作家将这一美国黑人独创的艺术形式应用于文本作品的行文和叙事。美国黑人评论家休斯顿·贝克创建了布鲁斯方言理论并将“布鲁斯旋律作为一种有力的符号系统,作为黑人方言传递的文化信息,并借用这一符号系统使之成为文本分析与解读的独特方式。”[5](P211)随着黑人音乐的发展,布鲁斯音乐和其他音乐形式的政治影响力日趋扩大,雪莉·安·威廉斯曾经指出,黑人女性成长历程就是“从受伤害的人到成为有自由思想的布鲁斯歌唱者的过程。”[6](P130)赫斯顿更是将布鲁斯音乐作为一种叙事手法,传达了黑人女性自我身份认同和寻求美国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的政治意识。endprint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布鲁斯音乐伤感忧郁的风格恰如其分地展示了小说幽怨感伤的叙事语调。布鲁斯音乐通常节奏缓慢,叙述者不紧不慢地将主人公对生活的悲叹、对爱情的渴望和寻求自我的迷惘娓娓道来,整个叙述层层递进,强化了珍妮精神层面的悲剧色彩。跟同时期的黑人女性相比,珍妮的物质生活非常富裕,一直是身边女性羡慕的对象,然而她的精神世界却一直处在荒芜状态。内心模糊的女性主义意识和黑人女性面临的残酷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珍妮对自我身份认同和美国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追求一直处于失语和迷惘状态。珍妮仅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从未真正弄清楚到底想要什么。
从幼年时期开始,珍妮懵懂地感知到自己对某种美好生活的向往,想做“一棵开花的梨树”,或者“随便什么开花的树”[3](P13)的愿望几乎伴随了她的整个理想生活。首先,有限的认知能力限制了珍妮用准确的语言表达愿望的能力。从文中对珍妮少年时代有限的描述可以推断珍妮在黑人学校上了几年学,而她的直接引语中明显的语法和表达错误显示出珍妮所受的教育程度并不高,她的文化水平远远不足以描述她内心的渴望,相反,和普通黑人女性一样,大自然和生活经验给了她一些暗示,她隐约感觉到开花的梨树给她带来了愉悦感,珍妮只能将抽象的理想物化为实实在在的物体——开花的树。其次,黑人女性的边缘地位导致珍妮无法冲出种族和性别的樊篱。她在前两次婚姻中明显处于劣势,如果说在第一次婚姻中珍妮还试图通过争吵来强调自己的女性地位,而第二次婚姻中,珍妮仅剩下自我麻痹,她“看着自己的影子料理着店务,拜倒在乔迪面前,而真正的她一直坐在阴凉的树下”[3](P83)。到了第三次婚姻,从表面来看,丈夫甜点心给了珍妮极大的尊重和自由,事实上甜点心对珍妮的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富有、美丽的珍妮满足了他男性的虚荣心,因此他在家里和外人面前从不掩饰对珍妮的爱意。甜点心潜意识中的男权思想促使他认为偷偷拿走妻子的巨款并无任何不妥之处,更无需在意当自己消失一天一夜时,新婚妻子在陌生的城镇会经历怎样的痛苦煎熬。后来甜点心通过打珍妮一顿来证明自己一家之主身份更是说明珍妮始终未能真正获得女性自主权。最后,对男性的依赖注定珍妮无法切实实现黑人女性身份。虽然珍妮一直没有完全放弃抗争之心,却从未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并一再将赌注放在男性身上。即便是她自认为与甜点心在一起的两年美好时光也充满狂欢化色彩,狂欢的背后注定是虚无。最终甜点心死于自己的刚愎自用,失去男性支撑的珍妮只能孤身回到伊頓维尔。珍妮的3次婚姻悲剧对应了布鲁斯音乐哀婉幽怨的曲调,悲剧的重复也是布鲁斯音乐中曲式重复的体现,珍妮的每一次经历带领读者从布鲁斯表层逐渐走到深层,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珍妮和现实中的赫斯顿一样,一直没有放弃追求自我价值,但在她们生活的社会这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只能成为进步女性思想困惑的根源。布鲁斯音乐忧郁的曲调和重复的曲式渲染了主人公珍妮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失败的悲剧,表达了赫斯顿对黑人女性出路问题的思考。同时,赫斯顿也巧妙地运用非裔文学独特的音乐叙事风格表达了希望通过凸显黑人民俗文化来重构黑人文化身份的政治愿望。
四、黑人方言英语
在欧洲白人对非洲黑人长达数百年文化剥夺的历史中,美国黑人被迫放弃非洲本土语言,使用强加给他们的外来语,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的语言:黑人方言英语。在种族化的社会语境中,黑人方言英语一直处于被贬低的地位,往往被认为用词不标准,语法不规范。在白人至上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中,一些黑人作家甚至耻于用黑人方言英语进行创作。作为人类学家和黑人民俗专家,赫斯顿认为黑人方言英语是美国黑人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黑人方言英语独特的语法规则、典型的词汇和修辞含义对美国文学、历史、艺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学家威廉拉博夫认为,黑人方言英语是“一种健康的、活的语言形式”,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各种语言符号”。[7](P89)黑人方言英语大量出现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的人物对话之间,不仅成为交流的媒介,也起到黑人文化身份构建者的作用。赫斯顿在美国南方农村长期采风,精准地把握住黑人方言英语中的诗意与乐感,突出了黑人方言不同形式的修辞特征,在作品中成功地再现了黑人语言和文化之美。小说中的黑人方言英语主要通过其特有的句法、词法和修辞特征体现出“黑人性”。
黑人方言英语与标准美国英语在词法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单词拼写差异和词语拼写中的省略现象。黑人方言英语中的人称代词、动词、名词、形容词、介词和定冠词与标准美国英语中对应的单词存在一定的拼写差异,如黑人方言中的“Ah,kin,whut,ole,wid,De”分别对应标准美国英语中的“I,can,what,old,with,the”。黑人方言英语中还存在词语拼写省略现象。如标准美国英语中的“them,yourself,it isnt,nothing,away”等词在黑人方言中省略为“em,yoself,Taint,nothin,way”。黑人方言的省略体现了黑人语言的口语特征。
黑人方言英语句法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主语和谓语不需要一致。在黑人方言英语中,当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时,动词一般现在时后面不加“s”,相反,当主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时,动词一般现在时往往加“s”;此外,be动词常常省略,不省略时与主语在数上也不一致。
(1)You looks hard tuh beat.[3](P146)
(2)He pick it up because he have to,but he dont tote it.[3](P38)
(3)All de cars in Eatonville is gone. [3](P146)
2.否定形式。黑人方言英语中否定形式主要用“aint,dont,ditn”这三种方式来表达,而且双重否定并不表示否定。endprint
(4)You aint supposed tuh look off,Mis Starks.[3](P147)
(5)Ah didnt aim tuh let on tuh yuhbout it…[3](P159)
(6)Dont let nobody hear you say dat,Janie.[3](P143)
3.句子省略现象。黑人方言英语中,句子经常省略一个字末尾的后鼻音或者一个字的首字母。
(7)Hell,Janie,how you comin?[3](P14)
(8)Ah aint got her to studybout.[3](P67)
除了黑人方言英语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赫斯顿还在小说中展示了黑人英语的修辞功能,以此来体现黑人英语生动形象的本土化特征。
(9)He was a man wid salt in him.(暗喻)[3](P56)
(10)Black-dark(重复描述)[3](P103)
(11)Gentlemanfied man(名词动词化)[3](P49)
(12)Big-bellies(头韵)[3](P76)
赫斯顿在《她们眼望上苍》中抓住黑人方言英语的主要特征,真实生动地还原了黑人本来的生活概貌和黑人语言的内在文本特征。黑人社会语言学家日内瓦斯密斯曼说,“语言在观念、意识形态以及阶级关系形成过程中起着控制性作用。”[8](P117)通过展示黑人方言英语中的黑人性,赫斯顿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黑人女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和建立非裔黑人文化身份的使命感。
五、结语
赫斯顿通过将黑人民间故事框架、布鲁斯音乐和黑人方言英语融入到叙事策略中,巧妙地形成了作品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学风格,体现了赫斯顿先进于时代的黑人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了她追寻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和重构黑人文化身份的决心。黑人文化身份是黑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拥有了黑人文化身份黑人才能建构个人身份,最终获得种族的平等。民俗文化表征是赫斯顿文学作品的生存策略,赫斯顿坚持写作的政治性,把写作作为黑人女性抗击种族和性别压迫的有效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治书写视阈下的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研究”立项课题成果[编号:2016SJD750043],本论文得到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注释:
[1]Walker,Alice:Zora Neale Hurston——A Cautionary Tale and a Partisan View,Robert E.Hemenway.:Zora Neale Hurston:A Literary Biography,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0.
[2]Gates,Henry Louis Jr:“Zora Neale Hurston and the Speakly Text” in The Signifying Monke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3]王家湘译,左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黄必康:《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国外文学,2001年,第2期,第115-119页。
[5]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6]Williams,Shelly Ann. Michael S.Harper&Robert B. Steptoe eds:Blues Roots in Afro-American Poetry,Chant of Saints:A Gathering of Afro-American Literature,Art and Scholarship,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130.
[7]Gates,Henry Louis,Jr: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8]Smitherman,Geneva:What is Africa to Me?Language,Ideology,and African American.,American Speech,1991,(2)117-123.
(吳良红 江苏淮安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2230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