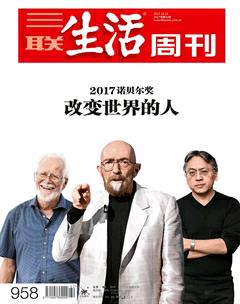沙姆之地,流浪或回归
刘怡
在阿拉伯语中,沙姆指的是北方和左侧;在地理学上,它指的是汉志(Hejaz)以北、地中海东岸曾经为三大哈里发国所统治的新月形领土。
“最小的大国”
汽车驶过迈斯纳(Masnaa)以东的黎巴嫩口岸之后,安蒂黎巴嫩山脉(Anti-Lebanon Mountains)间镶嵌着的居民点和松树林突然消失了。视线两侧的色调骤然变为灰黄,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车辆渐渐屈指可数。巴沙尔·阿萨德总统褪色的画像以及红白黑三色的叙利亚旗帜从高处探出头来,俯瞰着我们。
叙利亚国旗属于典型的20世纪初设计品,水平排列的三个矩形色块是对彼时欧洲国家旗帜的忠实模仿。它的创意来自一位富于艺术气质的伦敦政治家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英国战时内阁中东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今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三国边界的划定者。1916年,当英国政府开始策动阿拉伯各部落发起针对其宗主国土耳其的大起义时,一厢情愿的赛克斯主动为阿拉伯人提供了一份在他看来饱含“阿拉伯民族性”的设计稿:自上而下的黑、绿、白三个水平色块分别代表公元5~13世纪统治过中近东的正统哈里发、法蒂玛、倭马亚三大政教合一王朝,左侧的红色小三角代表领导起义的麦加圣裔哈希姆家族。由于此次起义系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而发动,红白黑绿四原色随后也被尊称为“泛阿拉伯色”。

在拥有109年历史的汉志铁路大马士革始发站内,工作人员站在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画像前观察窗外的机车调试状况
关于单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在1919年被赛克斯亲手终结,但泛阿拉伯色保留了下来,成为埃及、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等十余个中东新国家国旗配色的来源。1952年,革命成功的埃及共和派军官将四原色中的绿色降为点缀,以红白黑三色组成了新的“阿拉伯解放色”,这一做法很快为后来的叙利亚所效仿。1958年,埃叙两国合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三色旗中央缀上了象征两大成员国的两颗绿色五角星。即使这场失败的联姻仅仅持续了三年半,已故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在1980年依旧要求恢复这面“名实不副”的国旗,以重申大马士革当局对阿拉伯各民族联合的承诺。正如颁布于1973年的叙利亚《宪法》中保留至今的第一章第一条:“阿拉伯叙利亚地区是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阿拉伯叙利亚的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在阿拉伯语中,沙姆指的是北方和左侧;在地理学上,它指的是汉志(Hejaz)以北、地中海东岸曾经为三大哈里发国所统治的新月形领土。而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沙姆是一片在最近100年从未获得过统一的疆域:北抵托鲁斯-扎格鲁斯山脉,南到红海,西及塞浦路斯,东到波斯湾,涵盖了今天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全部版图。只有当叙利亚国的边界抵达了这些天然地理关隘,它才称得上是一个整全的实体。在大马士革书店中出售的地图上,甚至连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安提阿)和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大勒塔)也被标记为叙利亚领土:历届叙利亚政府从未承认过1939年土耳其当局在两地举行的归属权公投。
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史泰斗菲利普·希提(Philip Khuri Hitti)把叙利亚称为“地理上最小的大国”。这不单是指沙姆地区可以上溯至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历程,它作为人类最古老城市带的地位,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此地共处、斗争、融合的数千年风云,也是对叙利亚身为现代中东世界政治弄潮儿的褒扬。在大马士革诞生了阿拉伯半岛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阿拉伯叙利亚王国是第一个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的现代阿拉伯国家。出于光复沙姆之地和团结阿拉伯世界的使命感,使得历届叙利亚政府每每主动揽起重任。大马士革街头林立的巴勒斯坦国旗可以作证:这个被群山和沙漠覆盖的小国,却有着了不起的雄心。
“但那些都是过去时了。”外交官之子、新闻记者胡马赫告诉我,“我们曾经视邻国为兄弟,却并未自他们那里收获同等的厚待。”大马士革以贝鲁特的兄长自居,单方面给予黎巴嫩人堪称优厚的交通和贸易便利,后者却只关心何时能告别国土上的叙利亚驻军。2011年之后,当数百万叙利亚难民艰难地穿过山地、抵达黎巴嫩境内时,当地人令他们大失所望。“我们花费了几十年才认清一条简单的真理:国家首先应当致力于改善它自己人民的生活。”胡马赫感慨道,“但太晚了。如今我们每天所做的不过是挣扎着活下去。”
民族主义的浪漫热情使得人们可以暂且忍受家族政治和父死子继,忍受物资短缺以及不定期的供电、供水中断,忍受亲人、朋友的神秘失踪,只要承诺尚有兑现的可能。然而结局却是令人难堪的幻灭:世界舞臺上的游戏规则已经全盘更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比遥遥无期的“民族解放”更能引起共鸣;最终,平衡被“阿拉伯之春”打破,血与火从北到南席卷整个国家,沙姆之地退回到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2017年8月31日,一群叙利亚球迷聚集在一家餐厅内收看“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叙利亚队对阵巴林队的比赛,并为主队的进球喝彩
始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浪漫理想,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在今天的叙利亚领土上,活跃着俄罗斯人、伊朗人、阿富汗人、黎巴嫩人、土耳其人、伊拉克人、沙特人、约旦人和美国人,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势力,以他人的鲜血浇灌自己的私利。叙利亚人曾经真诚地相信,本国的自由只能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为前提才能实现;但在今天,却有更多国家期待沙姆之地的动荡和纷乱继续维持下去。endprint
诸神与恺撒
“试试本地产的拉克酒(Rak~)吧。”瓦利德把一杯散发着茴香味的乳白色液体推到我跟前,“用葡萄酿造,算是传统饮料。”在这位逊尼派穆斯林看来,偶尔和外乡人分享被称为“狮子奶”的拉克酒算不上亵渎宗教,只是源自19世纪末的传统民俗。同一张桌子上还坐着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德鲁兹派穆斯林和一位基督徒女士,轮流吸着一壶水烟。与此同时,清真寺宣礼塔和教堂十字架投下的灯光正在我们前方交会,毫无违和感。
叙利亚人有理由为他们的多元文化观和多元宗教观感到自豪。大马士革作为定居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约4000年前,那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还不曾诞生。当它在《圣经·旧约》的第一卷《创世记》中被初次提及时,已经是阿拉米人(Arameans)治下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邦国家了。闪米特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曾在此与阿拉米王国的军队交战,大卫王和他的后裔数次征服过这里,《阿摩司书》中的耶和华判决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基督徒与穆斯林最初的交集,可以说便和叙利亚有关:在《创世记》中奉耶和华之名向迦南“应许之地”迁徙的亚伯拉罕,同样被《古兰经》尊为伊斯兰教先知之一;他的庶出长子以实玛利和嫡出幼子以撒,分别被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视为彼此的祖先,而以实玛利又与父亲一道在麦加修建了克尔白(天房)。
在安蒂黎巴嫩山脉与沙姆沙漠之间,适合作为定居地的河畔平原屈指可数;更何况身为红海-地中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通衢,大马士革还承担着中近东世界贸易与人流走廊的功能,因之近乎不可替代。波斯人、罗马人和奥斯曼人的入侵都不曾毁灭它,只是给原有的文明与宗教底色加上了新的堆叠物。亚伯拉罕时代的房屋和关于阿拉米王国的记忆一同沉入了2.4米深的地下,使徒保罗踏足过的罗马直道渐渐被两旁伸出的美什拉比亚式飘窗遮挡住轨迹,朱庇特神庙的残垣断壁改建成了哈米迪亚集市,圣约翰大教堂被加盖上了清真寺的圆顶。在夏夜的倭马亚大清真寺中庭,基督徒和穆斯林会并坐乘凉,分享多渣的阿拉伯咖啡;与此同时,在北部重镇阿勒颇的露天市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正在激烈地讨价还价。
军事征服之后的和平共处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统治者有意识调控的结果。奥斯曼帝国延续了四大哈里发时代的宗教保护制度,允许犹太教徒、基督徒以及穆斯林中的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等“异端”分支继续沿用自己的律法。沙姆地区的领土则按照民族、教派分布和交通重要性的差异,设置了阿勒颇、贝鲁特、大马士革三大州(Vilayet)以及祖尔、黎巴嫩山、耶路撒冷三大自治旗(Sanjak)。阿勒颇对应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云集的多民族混居区,祖尔对应贝都因人游牧区以及逊尼派腹地的边缘,大马士革南部云集著德鲁兹派穆斯林,与黎巴嫩接壤的山区和海岸则是阿拉维派的大本营。沙漠、山川和河谷的阻隔妨碍了沙姆之地的人民形成统一共同体的机会,却也使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压迫被稀释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黎明期,基督徒和穆斯林知识精英至少两次并肩作战:第一次是为了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第二次则是要求驱逐法国殖民当局。

2016年5月4日,时任德国外长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右)在柏林会见投奔反对派阵营的叙利亚前总理里亚德·希贾布(左)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期,复兴主义(Baathism)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勃兴改变了整个格局。与工矿企业国有化、农村土地改革以及金融-贸易领域的管制同步。从1979年开始,受兄弟会支持的暴动、暗杀、罢工和反政府示威开始席卷全国,兄弟会武装人员在民众的支持下占领中西部重镇哈马,宣布当地为“解放区”。政府军出动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特种师进行正面弹压,用三个星期时间将哈马古城夷为平地,造成上千名武装人员和众多平民丧生。这一事件之后,甚至连过去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复兴党老党员和西部农民领袖也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历时不到一个月的“哈马事件”,内里已经隐含了2011年诱发叙利亚内战的一切关键要素:阿拉维派对政治现代化和世俗权力的垄断,长期输出泛阿拉伯主义带来的财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造成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分化,政府对旱灾和农业歉收救济不力。唯一的区别在于,在1982年,是老阿萨德介入黎巴嫩教派冲突的主动行为导致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动;而在2011年,来自中东世界其他国家的逊尼派极端分子试图在叙利亚展开反对世俗政权的“圣战”——当恺撒所代表的世俗政权经营的政治-经济秩序濒临瓦解,自会有人转向真主。
“内战爆发之前,我们用沉默回避表态;但在战争开始后,AK-47和火箭弹强迫我们公开站队。”从逊尼派名城霍姆斯逃出的大学生萨利赫告诉我。在恺撒的威权统治下,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和基督徒都不过是权利被剥夺的受压迫者;但来自国外的“圣战者”却要求他们按照教派差异区分敌我,相互展开厮杀。“城外的政府军在向市区开炮,而控制内城的各派反政府武装和民兵没有一天停止过自相残杀。”萨利赫回忆道,“我看到了范德卢特(Frans van der Lugt)神父的尸体。他是一位在霍姆斯居住了30多年的荷兰老人,耶稣会士,自愿留在危城中帮助受困的平民,却被自诩为‘解放者的‘基地组织武装人员杀害。”
逃离与死守
宰牲节前一晚,我在大马士革老城边缘的一家水烟馆和巴勒斯坦商人阿巴斯聊天。阿巴斯是1967年“六月战争”的遗民,从耶路撒冷逃难来此,转眼已是50年光阴。“我的四个儿子分别在荷兰、比利时和美国读完了大学,将来也会留在那里。”他告诉我,“但我本人只能永远留在叙利亚这个寄居地。1948年逃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拿的是英国殖民当局颁发的护照,1995年之后生活在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能申领新的巴勒斯坦国护照,唯有我们这代人被遗忘了。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收容了我的叙利亚有一天竟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endprint
类似阿巴斯这样的巴勒斯坦流亡者,在叙利亚足有50万人之众。相比困坐在黎巴嫩难民营中、无法平等就业和读书的那些同胞,他们在叙利亚的境遇一度要好得多。然而半个世纪之后,叙利亚人却不得不开始向他们的巴勒斯坦食客学习如何当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截止到2017年8月,战前叙利亚的2200多万人口中至少有516.5万已经出走国外,超过四次中东战争造成的巴勒斯坦难民之和。他们大部分会经陆路进入黎巴嫩和土耳其,稍事安顿,随后再寻求转赴经济较为发达的西欧和北美。不过平均每五个人中才有一个能最终踏上欧洲的领土,大部分难民在土耳其和黎巴嫩就会被当地移民局发现,送入临时搭建的帐篷群。没有公民权,没有在当地就业的机会,无法自由迁徙和租赁房屋,所余的仅仅是生存而已。
有两类人会把主动出走视为改变境遇的机会:既得利益集团的边缘人,以及完全的赤贫者。叙利亚外交部前发言人杰哈德·马克迪西(Jihad Makdissi)属于前一类。美国《新闻周刊》中东版编辑雅尼娜·迪·乔瓦尼(Janine di Giovanni)对我描述了她2011年在大马士革见到马克迪西时的情景:“虽然有一个穆斯林式的名字,但杰哈德其实是个基督徒。他在索邦读过书,理性、聪明、深思熟虑。老阿萨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认为有必要改善一下叙利亚政府的国际形象,因此挑选了这位文质彬彬的温和派来装点门面,一干就是14年。”但马克迪西还是在2012年底叛逃到了阿联酋。他在邮件中告诉我:“在叙利亚外交部任职的那些年,我就像是个被强行指定了委托对象的律师,绞尽脑汁为政府做口舌上的辩护。如今我终于可以像个真正的外交官那样说话和行事了。”毕竟,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叙利亚反对派,都会需要这位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高材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和他走上同一条道路的还有叙利亚前总理里亚德·希贾布(Riyad Farid Hijab):2012年夏天,在被任命为总理仅仅一个多月之后,这位复兴党要员带着全家老小逃去了约旦,并很快摇身一变,成为了反对派在日内瓦和谈中的联合组织“高级谈判委员会”(HNC)的头面人物之一。在遭受过冲击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这类长袖善舞的变节者:原本就衣食无忧,而出走能带来更可观的回报。

从沙姆宫旅馆顶层的旋转餐厅俯瞰大马士革市容。画面左侧的白色圆顶建筑为叙利亚人民议会,右上角可见国家银行大楼
战争给予了他们逃离简陋的山区住宅和面容严峻的征兵官员,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意味深长的是,体力和健康状况更佳的青壮年男子成为第一批出逃者:他们被紧急征召入伍的概率更大,因之离开的愿望也更迫切。随后是他们的妻儿和家人,再紧接着是变卖了房屋和家产、将最后一个叙利亚镑也支付给“蛇头”的中年人。在校學生、和父母失散的年轻女性以及多病的老年人被遗弃在了大马士革,使得当地男女比例达到了1比7的悬殊数字。“女同性恋现象在最近几年正变得公开化。”瓦利德告诉我,“即使是留在死城里的姑娘,也会需要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侣。人口学家年复一年地渲染沙姆地区的人口爆炸,他们意识不到,因为这场内战,若干年后叙利亚将不再有新生儿。”
与欧洲通讯社签下一份短期合同的瓦利德属于大马士革最不“主流”的主动死守者——中产阶级。“我的许多老同学、亲密朋友和亲属都已抵达欧洲,但我选择留下。”拉克酒的后劲让这个略显疲惫的年轻人有些激动,“我是新闻学硕士,不愿在德国作为卡车司机或者烤肉小贩度过余生。留在这里依然有随时被征召入伍的风险,但至少维持着表面上的‘体面。我有能力赡养父母和妹妹,会因为工作的专业性受到尊重,而难民的身份将使这种尊重荡然无存。我仍在祈祷和平能尽快到来,但和平之上的内心安宁,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
宿醉造成的头痛过去之后,我参加了倭马亚大清真寺在每年宰牲节的例行晨祷。内战开始之前,清真寺和哈米迪亚集市之间的空地在日出时分就会被数以万计的民众淹没;但在2017年9月1日,寺院中庭只有冷冷清清的一二百位穆斯林现身。那些不曾出现的人,大部分已经在黎巴嫩、土耳其、约旦、西欧和北美找到了他们的下一站,而其中有很多人,也许在余生都不会再归来。
即使你回来,哦,奥德修斯;
即使空间围绕着你合拢来,
领路人在你过去的脸上
或在你友善的恐怖里
烧成了灰烬,
你仍将逗留在一段流浪的历史里,
你仍将逗留在一块未被应许的土地上,
你仍将逗留在一块无法返还的土地上,
即使你回来,
哦,奥德修斯。
——〔叙〕阿多尼斯《一块无法返还的土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