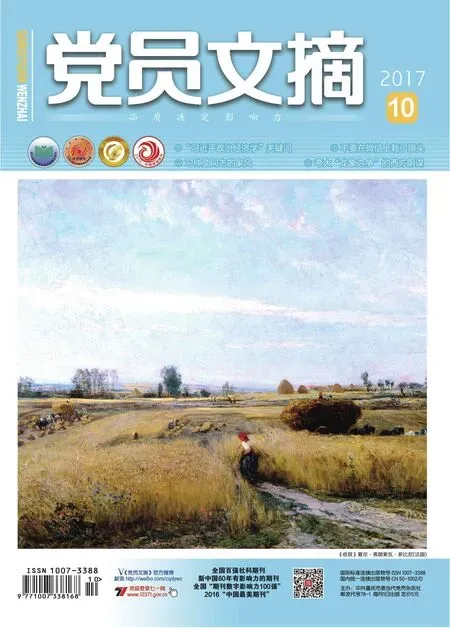“变坏”的老人与我们的时代症候
□李少威
“变坏”的老人与我们的时代症候
□李少威

大移民社会
被“街上有个人”看到和被“村里王大婶”看到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问题老人”现象,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这句断语的流传,并非因为其内含的真理性,而是因为其形式上的简单粗暴符合了群体思维特点。它一棍子扫倒一代人,逻辑上非常过瘾。
当我们说“这一代老人”的时候,对象事实上非常含糊。一般理解,就是那些不再工作但常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老人,他们已经退休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且体力尚好,大部分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10年。
如果他们可以被统称为“一代人”,那么这一代人人生历程的最大特点是跨越了农业中国和工业中国两个大时代。此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1977年不到20%到2016年的57.35%),所以其中大部分人还跨越了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两个空间。
这意味着,如今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大移民社会。
从来路上看,城市里生活着四种人:第一种是世居的本地人,第二种是城市之间交换的人口,第三种是完成了农民进城这一过程的人,第四种是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的人。
后三种,毫无疑义属于移民,而第一种(世居的本地人)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导致生活环境面目全非,以及后三种人的介入带来的文化糅合,在与城市的关系上与移民已经差别不大。
道德是依靠舆论对越轨行为进行制约的,而在一个陌生人社会,舆论的力量大打折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是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处在“匿名”状态,自我约束意识就会削弱——这也是《礼记·中庸》提出“慎独”的原因。
一个家庭里的正经人,在外面偶尔做一回混蛋,谁知道呢?这便是这个大移民社会里一个隐形的心理过程。在这一环境下人其实是抽象的,被“街上有个人”看到和被“村里王大婶”看到完全不是一回事。
时代跨越和社会变迁
对于能够适应技术变化的年轻人群而言,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而对于很多老人而言,则越来越艰难,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不友好。
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广场舞在中国如此风靡?
那些大妈大爷们,原本大多是连站出来说几句话都忸忸怩怩的传统内敛的人,而现在他们早已不惮于乃至热衷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各美其美”的舞姿,他们真的是出于锻炼的目的吗?
深层的动机其实是,他们熟悉的社会瓦解了,瓦解发生之时他们已经过了富于可塑性的年龄,难以和新的现实建立情感联系,而广场舞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熟人社会的共同体体验。
威尔斯在《新马基雅维利》中描述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说:“这是一种猝然发生的进步,一种难以控制的变动,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
这在中国,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一代老人,就是跨越了“猝然发生”的变化,来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不过,为什么“上一代”的老人就没有出现“问题扎堆”的现象呢?比如,2006年“彭宇案”出现之前的老人,社会形象上还是切合传统的,而他们同样经历了时代跨越和社会变迁。
答案在于,一方面他们更少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比如那时还没有广场舞),另一方面当时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不如今天快。
少参与,就少是非,这一点不用解释。
技术进步不仅仅指“坏形象”的传播效率,还对人的生活能力提出了全方位的新挑战。比如支付宝、网购、网约车、共享单车,对于能够适应技术变化的年轻人群而言,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而对于很多老人而言,则越来越艰难,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不友好。
“老人小恶”并不值得宽容,但值得理解。他们在努力摆脱了生存问题之后,却迎头赶上了一个四下惶惑的世界。
有人对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孤独和不愉快”提供了一个分析角度:现代工业社会处理人事的能力跟不上处理技术的能力。人们对技术的操控得心应手,但对如何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越来越生疏。
今天的现实是,相当一部分人非但无法处理人事,而且也无法处理技术——这便是今天的老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符合下面几个要素中的某几个: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龄未能受教育,在青春尚在的时候经历下岗;在年轻时经受长辈的权威却在年老时无法继承这一权威;在青春消逝后被动急剧城市化,在惶惑的技术环境下,成为骗子与谣言的捕猎目标。
在现实面前,这一切都会转换为一种非常可怕的心理体验——强烈的被剥夺感,它会转化为人格上的攻击性。
“技术性孤立”
即便全世界都不理你,你也不会疯狂。因为不是个人被动孤立,而是人主动把环境孤立了。
关于“问题老人”现象,有一种观点听起来非常“进步主义”,它说:自己出问题,不能赖时代。
如果它所指的是“不能用问题来否定时代进步”,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其意思是说“社会问题跟社会没有关系”,那说话者的面容就变得很抽象了。
这不叫“赖”,而是解析,下面进一步解析。
人的孤独存在,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显著区别,客观地看它是中性的,既不积极也不消极,但人是有情感的,从情感出发,孤独存在就是一种病态。而今天,强大的技术让它不再是一种病,而是人的正常又甘愿的存在方式了。
这个强大的技术,是智能手机终端及其后面的一整个支持性技术系统。一开始,是年轻人坐着、躺着、走着、开车、骑自行车都在玩手机,而这几年,老人也被传染,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又颠覆了传统的社会学、心理学认知,“孤独而不愉快”转变为“孤独且愉快”。这一存在方式带来的新局面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发生了主次易位。也就是说,通过移动互联网所进入的那个空间,变得比现实生活空间更加重要了。
过去我们认为,一个人如果被周围环境所孤立,时间长了是会出问题的。但现在,事实出现了反转:即便全世界都不理你,你也不会疯狂。因为不是个人被动孤立,而是人主动把环境孤立了。
这是一种技术导致的自我孤立,但技术让孤立本身变成了一件深具乐趣的事情。同时人们发现,电子化的人际关系比现实的人际关系更容易处理,于是社交工具从现实的辅助变成了现实的替身。
结果是,人们在情感上和生活问题上彼此需要的程度下降了,因而人类的社会结合本能也在退化。不可避免地,人也会变得自私,变得对自身越来越爱惜,但对他者的戒备和敌意却在不断升级。
英国宗教伦理学家约瑟夫·巴勒特说:“一个人在世上可以有所有的自爱,而同时是悲惨的。”“悲惨”,是说缺失了直接的、真实的责任感,而被自身变异所俘虏。
没有责任感的自爱,作用于他人便是敌意。
在某种程度上,一些“问题老人”也是这样“中招”。
一个有社会大背景的问题,在整体层面上却往往无计可施。对“问题老人”,空谈社会教育或重复道德教条都没有意义,而只能寄希望于个体的自我救赎和家庭成员的协助矫正。
(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