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音乐
吴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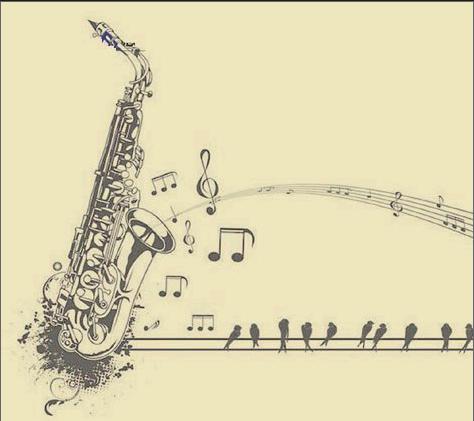
音乐于我是开在人生灰色坚壁之上用于透气透光的一扇窗。
一半是由于我愚钝的资质,一半是由于小时候有限的条件,时至今日我依然只能以一名普通爱好者的身份来享受音乐。但即便是这不完全的享受,也足够令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可贵,足够令我对这世界满怀感激之情。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逼着我去学习钢琴、电子琴、古筝等。这是幸还是不幸呢?我想这是现在很多孩子眼中的幸,却是我这个已届不惑的人眼中的不幸。今生我将注定只能远远地瞻仰音乐女神的芳颜,而无法走到她的面前与她对视,让她感受到我的存在,感受到我胸中充溢着的对她浓烈无比的爱。不过,我时常宽慰自己,茎上的花永远要美过襟上的花,占有并不是爱的最高形式,或许正是这种距离,使我从音乐当中虽感受不到极致的狂野,却也体味到了一缕温暖的慰藉。
我虽然没有学过乐器,但当时家中并不乏懂乐器的人。爷爷会拉二胡,据说过去还会弹钢琴,伯伯多才多艺,手风琴、小提琴、口琴样样精通,演奏起来像模像样。记得小时候有那么几个黄昏,天边烧着绚烂的晚霞,大家早早地吃了晚饭,伯伯被晴朗的天气撩拨得心情大好,便走到窗前,用一只手轻轻地拢在耳朵上,对着窗外亮出了他的男高音。伯伯有时唱《重归苏莲托》,有时唱舒伯特的《小夜曲》,有时也唱《北京赞歌》等中国曲子,都是那些能柔柔地流进夜色里的歌曲。我那时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在他的歌声响起的那一刻,世界陷入了无比的和谐,仿佛就该是那样的夜,就该是那样的人,就该是那样的歌,就该有我这样一个坐在小板凳上托腮聆听的小听众,一切就该以这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在短短的一瞬让世界中心发生位移,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置身在一种销魂蚀骨的曼妙之中。
史铁生在《务虚笔记》里说: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确切的事件经过时光的打磨就会从我们的记忆中逸去,但某些印象会长久而又真实地存留下来。伯伯在窗前唱歌的一幕就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印象之一,现在再回想起来都觉得美好得有些不真实,怀疑是加进了自己情感的渲染。后来看由程乃珊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丁香别墅》,结尾处一对在爱情路上屡遭劫难的大龄男女终于走到了一起,男主角捧起女主角的手,深情款款地说了句:“现在可以唱《冰凉的小手》了。”一样的弄堂房子,一样的夜色,一样的优雅,相似的歌与相似的情怀,我的心弦被拨动了。程乃珊有一支好笔,可以把弄堂里的势利与刻薄都写出美感来,而且她懂得有时候费尽笔墨的描摹还不如只提一首歌名来得传神。每首歌都有它自己的世界,一提名字,那世界就慢慢地洇出来了,远胜万语千言。
音乐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触发想象的媒介。我从小就有着浓厚的幻想气质,独处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乘着一段小小的旋律,我就能踏上迷离的幻想之旅。那些幻想没有很明确的情节,往往只是一个瞬间、一段印象。听德彪西的《梦幻》,我能看见一个略带惊慌的孩子在午后的阳光中漫步在空寂无人的巴洛克风格大宅中,阳光从长长的天鹅绒落地窗帘间顽皮地挤进身来逗引着小孩,令孩子渐渐大胆起来,他踱进了图书室中,成排的书架高到屋顶,要用梯子才能够到高处的书,在那些书里隐藏着一个陌生的世界,神秘而又充满魅力,一如这音乐本身。听福雷的《西西里舞曲》也是一种无人但不空旷的感觉,如同在迷宫里摸索,心中漾着隐隐的焦虑,但那优雅低回的旋律又让这种焦虑不能挥发,直把人拽入感伤的溪流中去。海顿的《小夜曲》展现给我的是一个夏夜的大花园,带着假发的宫女贵妇与平民人家的孩童一起在喷泉与花丛间嬉戏流连,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隔膜似乎都被音乐的美给填平了,每个人都尽力展现着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同样的曲子下回再听,又能触发出新的幻想,直叫人赞叹造化的神奇。
读大学的时候,同宿舍有一位学长酷爱古典音乐,收集了一套国内出的普及版古典大师名作集,每人一盒磁带倒也公平,许多大师就是当时从学长的那套磁带里认识的。我喜欢听旋律优美、甜得发腻的曲子,所以爱莫扎特胜过贝多芬,不过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有太过偏狭的口味,所以也听了一些如科普兰、雅纳切克、斯特拉文斯基、西贝柳斯、威廉斯、布里顿、霍斯特等相对有些冷门的作曲家。
在毕业后的头几年,我一直过着宿舍与办公室两点一线的生活,经常有大段的时间是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所以也有了一些别致的音乐体验。比如我曾经点起香来听古筝,那是一盘古琴名家的古典名曲集,不是普及版的,没有其他乐器的掺和,只有一把古琴孤零零地独奏,一个音弹毕,非得等它在空气中完全散尽,下一个音才会不情不愿地出来。初听时极不适应,毕竟是毛头小伙子的浮躁心性,冷水泡茶般终于品出了味道,从而感受到之前不懂欣赏的枯瘦清雅之美。我也听枪炮与玫瑰或是涅磐乐队的摇滚,歌词听不清,所以无从感受他们的愤怒,纯粹只是凑热闹,但久而久之也渐渐听出感觉来,通过身体力行知道了后天性获得的趣味是怎么回事。这段时间经常买从来没听过的歌手或乐队来听,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口味再广一点。
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爵士乐更多些,曾咬牙买过一百六十元一张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格伦·米勒的正版碟,也去商城听过四百多块钱的爵士音乐会,这些在当时无疑是极为奢侈的举动,但回顾如今,它们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迹绝对是超值的。爵士之美,美在那慢节奏中直抵人心的幽怨与感伤,美在那快节奏中令人忘形的率性与洒脱,至于即兴演奏,则不啻是自由之神化身到了音符里,所以我觉得爵士真是动静皆宜、老少通吃的。
大学毕业两年后,卡拉OK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单位组织了一次活动,让我与之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当别人還被闪动的歌词甩在后面的时候,我初次亮相就成功地演唱了《跑马溜溜的山上》,每个字都能跟上,每个音都能唱准,这给了我莫大的成就感。在那一刹那,我有一种与音乐又近了一层的感觉,那种感觉所带来的欣喜只有一个多年残疾的人初次装上假肢后才能体会得到。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