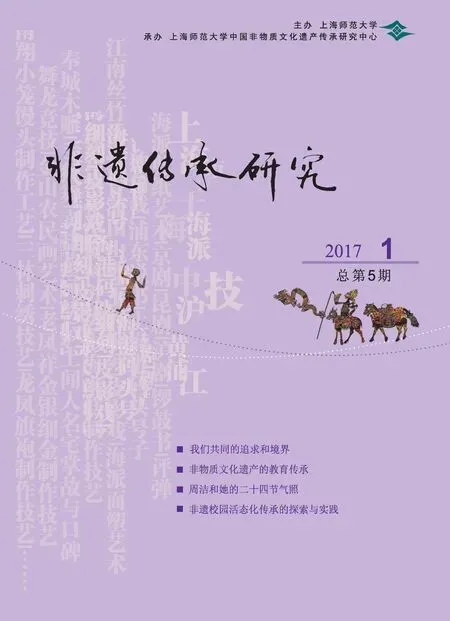采访盖叫天之回忆
秦绿枝 口述 王其康 毛信军 整理
秦绿枝先生撰写的《采访盖叫天》一书近期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5月9日王其康、毛信军在秦绿枝先生寓所拜访秦老,秦老回忆了当年采访盖叫天的点点滴滴。王其康、毛信军整理了秦老的口述,有了一份“回忆本”。本刊摘录了其中一部分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盖叫天为什么同意我写连载采访
人们都赞扬盖叫天的演技,但是也有人对他有点意见。一是他对任何人都不服帖。你讲杨小楼好,他觉得不怎么样,常常把话绕开。但听他谈话又觉得他很风趣。我第一次知道他很健谈还是漫画家丁聪对我说的。丁聪曾经访问过他,后来就告诉我听盖叫天谈话十分有趣。盖叫天在上海确实很有名,但是那时境遇也不怎么好。他和我家住在同一条马路上,就是现在淮海中路后面那条兴安路(旧时叫麦赛尔蒂罗路),向西是雁荡路,我家就住在靠近雁荡路(旧名华龙路)的一条弄堂里,向东是嵩山路,盖叫天就住在近嵩山路的一条弄堂里,就是很有名的宝康里。那一带房子不是很好,唱戏的人家很多,是老式里弄没有抽水马桶的。盖叫天家后门在宝康里,前门面临兴安路。我每次去,他都是睡过午觉后刚刚醒来,都是从客堂间后面那间厢房里走出来的。有一次,我陪侯宝林去他家。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听他谈话确实有趣,就这样一来二去地和盖老有点熟了,于是就萌生了给他写长篇连载的念头。我那时在《亦报》工作,是解放后办的一家小型报,版面上需要这样的稿子。可能盖叫天对我的印象还可以,我一说他就答应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时华东地区的文化部门有两位干部合写了关于盖叫天的一本书,很薄的。两位作者中的一位就是近年刚刚去世有名的戏曲史家、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蒋星煜先生。这本书是颂扬盖叫天的,但盖叫天不满意,因为书中说他是李春来的学生。李春来当年曾经是江南名角,也很红。说盖叫天是李春来的学生也有不少人,但都是传说,没有确切的根据。我估计盖叫天年轻时曾 与李春来同台演出过较长的时期,论辈分李春来要长一辈,可能盖叫天吸取了李春来的一些玩艺,但没有正式举行过拜师的仪式。盖叫天的表演有他自己独特的创造,他当然不承认李春来是他的老师,好像他的成就是从李春来那里全部继承过来的。还有一点,唱戏的与唱戏的之间往往有矛盾,这里面可能有台上排名的问题。还有我的玩艺儿被你在前面的戏先表演过了,等我上了台“彩头”就没有了等等,日子一久,彼此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多。这是公认的事实。所以这两位作者的书出版以后,盖叫天认为写得不对,耿耿于怀。两位作者跑来作解释他也不听。所以我一提出“盖老,我们报上给你写个连载怎样?”他马上就同意了。虽然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出于对京剧的爱好,对盖老的尊敬,笔底下一点也不敢流露出对盖老的不敬。我自知有点不自量力,但连载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盖老不满,说明他对我这个小青年认可了。
从忠实纪录和理解开始采访
记得那时正是大热天,我总是下午去,也总是摸准盖老正好睡了午觉刚刚醒来。我先在客堂里坐着,然后盖老慢慢地从后房走了出来。他们家客堂家具摆得满满的。靠里边正中是长长的案几,前面挨着大的八仙桌,供了好多佛像,究竟是些什么像,我也说不清楚。八仙桌前面又放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放了一个小香炉。烧着檀香末,客人来了盖老总是要再放一些香末进去,顿时有一小股青烟袅袅升起,挟着一股清香。客堂两旁放着老式的太师椅。放香炉的小方桌前面放两张小椅子,面对面,左首一张是主人坐的,客人就坐右首那一张。客人多的话就坐两旁的太师椅。看起来好像很拥挤,但很有格局。盖老家白天大门总是虚掩着的,熟悉的客人只要轻轻一推就进去了。
我也不是天天去,隔两三天去一次。去的时候常有别的客人,画家吴湖帆就是一个,他家住嵩山路,离盖老家很近,他跟盖老关系很好,来了也不拘礼节,随便坐哪里都可以。还有别的客人,多半是京剧界的老人,他们来了,话不多,谈起来都是一些内行的事,我也并不是很懂,有时见我在,他们就不开口,听盖老跟我谈。
我每去一次,凭记忆所得,总可以写三四天的稿子。因为报纸的篇幅小,每篇顶多五六百字,力求简洁,但总有一个中心话题,反响很不错。常有朋友打电话来说:“昨天的一篇写得好。”我坚持一个宗旨:盖老说什么我写什么,忠实地反映他的意思,不自以为是,不自作主张地胡乱引伸。因为我也懂一点京剧,盖老说的那些,我还能理解。他除了讲他演的那些武生戏,也讲别的武生;除了讲武生戏,还讲老生戏,讲花旦的戏。由此及彼,他还要讲京戏的一些动作怎么做才是合乎情理的。比如他讲京剧里的开门手势应该怎样做,这只手在上应该怎么捏,那只手在下应该怎么捏,中间要空着。表示手捏着门闩,左右分开一些,门才开得开来,你要是捏实了就不行了。越是这些小动作,越要考究。又比如他说《打渔杀家》,萧恩去县衙门告状时被打了四十大板,出衙回家时有几句唱,唱到后来有哭音,盖老认为不合理,萧恩是个刚强的英雄好汉,四十板子打不哭他,这是盖老的理解。但别的人还是这么唱,这也许是别人的理解。盖老也是跟我说说,对内行,尤其唱老生的,他是不说的。
采访中与盖叫天建立感情
这样采访了一段短时期,与盖老开始建立起了一点感情。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对盖老越来越敬爱;而在盖老那方面,他可能认为我这个年轻人还“靠实”,不是一个“小滑头”。用“王惟”的笔名在《亦报》连载了五十篇,暂时告一段落。那年(1952年)秋后,上海新闻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亦报》要停刊,一部份人要被吸取到改为公私合营的《新民报(晚刊)》去了。1952年秋后,北京将举行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盖老要去参加,总要个把月才能回上海。见不到他的人,我的“现买现卖”的写作也不得不暂告停止了。
在这次会演上,盖老和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四位大师获得了“表演艺术家”的称号。好像还有一位是王瑶卿,我记不清楚了。还有两位获得“表演艺术家”称号的是袁雪芬和常香玉。袁雪芬是越剧改革的首创者,常香玉是豫剧演员,她带领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所得捐献给国家,买飞机支援抗美援朝,飞机就叫“香玉号”。
盖叫天这次从北京回来,显得非常高兴,精神也比以前更加健旺了。《新民报(晚刊)》改制成功,报道方针以文艺为重点之一,戏曲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占了两个版面,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稿子,于是写盖老的连载又被提了出来,要继续刊登。我去跟盖老一说,他立即同意。我又像以前一样,隔两三天就要去盖老家听他纵谈一次。这样一写又写了六十篇,每篇的字数稍多一些,有七八百字,笔名仍旧用“王惟”。
我写盖老的连载,主要写他的艺术成就。他的历史很少提及,我也不大好问。他有时也跟我讲一点,比如他是河北高阳人,那地方很苦,他家更苦,每天吃“三黄”,即小米、珍珠米、黄豆芽,就是现在的杂粮。学戏很苦,动不动老师的鞭子就要打上来了。他说什么我就记什么,没有去做进一步的考证。
还有,当时中央早就颁布了戏曲改革的方针。这次会演,又有新的精神,比如周扬最后总结性的讲话。我写戏曲的稿子,包括盖老的连载,都要参考这些精神。那时我对这些精神的理解肤浅,写出来的东西难免幼稚,甚至还有点教条,现在看看,是很不好意思的。
这次续写盖叫天的连载,我决定根据他一出戏一出戏的脉络来写。盖叫天有一出戏叫《一箭仇》,内行公认这是盖老的代表作,戏的内容是讲梁山泊攻打曾头市的故事。曾头市是河北大名府属下的一块地主庄园,曾家有地主武装,曾家五个兄弟号称“曾家五虎”,传授他们武艺的教师爷史文恭是名师周侗的学生,与林冲、卢俊义同学。梁山泊第一次攻打曾头市由晁盖带领,被史文恭一箭射中脑门,回去不治而死。梁山泊蓄意报仇,收服了大名府的豪绅卢俊义。先是由卢俊义与林冲一同去拜会史文恭,劝他归顺。史文恭一身傲骨,看不起梁山泊人,一口回绝。我们向来的评价是梁山一伙属于人民起义,凡与之作对的都是反面角色。但盖叫天塑造的史文恭与众不同,他自恃本领高强,看不起梁山强盗行径。盖老演史文恭,表现的就是那种“傲”气。但史文恭第一次与林冲、卢俊义交锋以后,虽不分胜负,却也令史文恭有点胆战心惊,不敢小视。他决定带领曾家武装夜里去偷袭敌营。计划已定,史文恭为返场战斗彻夜不眠,坐立不安。这一仗该怎么打,能不能打得赢?史文恭这时才觉得无绝对的把握。这里有一场个人思想斗争的戏,也可以说是一场个人的独舞。身段动作、踢腿伸手之好看,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既充满了劲力,又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特别是他颌下那架三绺“胡须”(内行称“黑三”),一会儿托,一会儿挑,一会儿理,一会儿全部挂在胸前,一会儿又变成两前一后,或前一后二,真的是变化无穷,得心应手,像通了灵一般,看得台下无不如醉如痴。看盖叫天的戏,是要别有会心的。一不听他的唱,他的嗓子不好;二不要指望他台上会摔打,会翻什么跟斗。就是看他的功架,沉稳有劲,一举一动都有讲究,表现了一种含蓄不尽的美。
在杭州与盖老的交往
我总算跟盖老“混”得很熟了。但除了想好题目去采访,平常我也不大去他家,何况盖老住在杭州的日子比较多。他几次提出让我到杭州玩玩,我是想去,但总定不下时间。上海新闻出版界工会在杭州办了一个休养所,1954年我去休养过一次,游程全部是集体活动,我抽不出空来去盖老家。1955年,我决心把写成的连载《盖叫天演剧五十年》重新整理补充,打算出书,想去杭州看盖老,请他再跟我详细谈谈他的家史、演戏的过程、演出的故事。这个打算需要腾出较长的时间,要向报社请假。如此一再延误,直到1955年深秋还是初冬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终于乘早班车来到了杭州金沙港的“燕南寄庐”。谁知盖老一见我就说:“你来晚了,上海有电话来,有任务,我明天回上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本打算下午就回去,谁知盖老夫人说:“你来了也好,今天下午老爷子要去拜会几个人,向他们辞行,就由你陪着去吧!”我只好留了下来,在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与盖老夫妇又乘火车回了上海。

1956年,我被评为上海市文化界先进工作者,又要我去杭州休养。这次我就跟休养所提出:集体活动我是否可以自由些,有的参加,有的就不参加?休养所同意了。不参加的日子,我就去盖老家。头一次去,我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出他家大门口坐上三轮车,盖老夫人赶出来,硬要塞给我几百元零花钱。我再三推辞,并从身上掏了一叠钞票来说:“我有钱,真的,等用得不够了再来向您开口。”这是托辞,其实是我再穷也不能跟您伸手!作为报纸的记者向采访对象索要好处的事我再穷也不会去做。盖老夫人见我说的确实不是客气话,就收回去了。
又一次我上午去了,坐不多久,上海评弹团演员吴君玉、葛佩芳、高美玲等来拜访盖老了。盖老很高兴,谈了一会儿,照例是老规矩,先请他们去参观丁家山的寿坟,然后去楼外楼吃饭,我全程陪同。吃过饭,吴君玉一行要赶往书场演出,我和盖老就逛西湖。逛的是里西湖,走了一段路,在一张石凳上坐下来,盖老忽然说:“不开会有多好啊!”我笑了。我懂得盖老的意见,他是渴望做一个自由自在完全不受拘束的山野闲人。但他现在也不能不去参加一些会议,去了要换中山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他其实有点不习惯。他到北京去,住在旅馆内,看看很舒服,但他感到活动的范围太小,有点像一只老虎被关在笼子里转来转去的感觉。他在杭州,每天一早就会出去兜圈子,走野路,要走好一会儿,然后回家吃茶吃早点,感到通体舒畅。
他上海的家搬到东湖路后,我也去过,不是常去,去了总要有点可以写写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扬州评话家王少堂去拜访他,我去了;还有一次有几位工艺美术老师傅去拜访他,我一看他家那个场面,整套的瓷器餐具都摆在那里,看样子晚上要大摆宴席,我就悄悄地走了。
我也陪盖老出去消遣过,有一次是逛南市的老街。盖老一直穿长袍,那次我也穿了仅剩的一件丝绵袍,陪他在老城隍庙大门前那条马路上荡了好久,然后到校场街的老饭店去吃饭。这是“老饭店”的旧址,单开间,菜的味道也是这个时候的好。
尊敬也是一种“距离”
与盖老接触,我始终坚持着“尊敬”的态度,他怎么说我都表示理解,表示接受。即使有疑惑,也不说出来,心里有数就是了。“尊敬”也是我保持与盖先生交往的分寸,也可以说是一种“距离”。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为好,太亲密了反而会生出厌倦的情绪来。
有些名演员,总认为自己的玩艺儿好,有的只是人家不懂,看不出好来。盖老就常常流露出自己的文戏比武戏有深度,虽然没有嗓子,唱功差,你要看他的举止风度,自有其不同于一般之处。曾有那么几天,他演全本《林冲》,前面好几场都是文的,老实说,台下观众都有点憋不住了,好不容易演到林冲来到柴家庄,与洪教头比武了,观众终于松了口气,盖叫天终于动武了,因为人家就是冲你的武戏而来的。
盖叫天还有他的自信与自尊。与人合作演戏,有的地方就要照他的路子演。比如有一出《龙凤呈祥》,这是好多名角会演的群戏。梅兰芳如在上海,孙尚香一角自然非梅先生莫属。赵云由谁演,组织会演的人就会请盖老。梅兰芳上场,盖老也答应演了。但是他的扮相与别人不一样,赵云也穿靠,背后插旗,但头上戴的不是珠盔,而是软巾,就像史文恭戴的那种,沿着帽沿还扎着一根长长黑带子,一边飘下来,垂直一边,的确也很好看。我到后台采访时,盖老正在穿戴,对我说:“你瞧,这多麻烦,演我那个戏(指《武松》)省事多了。”
早先,京剧界南方的角儿和北方的角儿两大阵营分得很清楚,京派看不起海派,海派也不服帖京派。到了解放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盖叫天也很能适应形势了,他就很喜欢李少春。周信芳欣赏裘盛戎、袁世海,都成了当时的梨园佳话。
“反右”以后,我就不去盖老家了。1961年我摘了右派帽子,又恢复做了记者(采访范围有限制,戏曲界只能接触评弹),盖老家我也不去。1962年的一天下午,我到静园书场听书,不想碰到了盖老夫妇。他们坐在当中的座位上,我坐在靠近门口边排的位子上,本来可以不交谈的。但休息的时候,盖老夫人跑到我面前来了,问我以前给盖老写的文章还在吗?我忙说:“在,明天给您送来。”很奇怪,“文革”以前,我在报上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自认没有什么价值,都不留存。独有写盖老的这份连载,有剪报,贴在三本练习簿上。第二天下午,我敲开东湖路盖老家的后门,就在门口将三本贴报交给了盖老夫人,没有进门就掉首而去。我认为做人要识相,我现在虽然摘了帽子,还是不能与一般人相比。盖老有着很高的声望,我不能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从此我再也没有与盖老相遇过。直到“文革”爆发,他老人家也不幸遇难,家里值钱的东西损失何止千万,我那几本小贴报簿又算得了什么,随它去了!
前前后后算起来,与盖老相识到相交也不过是1952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回头一看,真是一眨眼的功夫。那时候我还年轻,识见浅陋,甚至有点天真,现在想起来,觉得是很惭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