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世”与“飞升”:汉画像石中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
□ 杨 赫 杨孝军
“蜕世”与“飞升”:汉画像石中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
□ 杨 赫 杨孝军
本文通过考察汉代画像中“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来探讨宗教思想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同时从“蜕世”到“飞升”的向往与构建来简要揭示汉代早期民间信仰的生死观的变迁,以及这种观念作为象征符号被赋予在汉代墓葬画像中,显示出人们对于早期宗教思想有着强烈的信仰和认知感。
汉画像石 “蜕世”“飞升” 宗教思想
秦汉之际,不死的追求,始终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在这一信念的推动下,人世间不断演绎出一幕幕闹剧,如《史记》记载,方士李少君死后,武帝命人发少君之冢,不见有尸,空棺衣衾而已。武帝于是相信法术可以使人死后通过某种神秘变化脱离世人[1]。另有武帝巡幸黄帝所葬的桥山,当祭黄帝陵时,他问道:“我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随从答曰:黄帝的确已成神仙,墓中埋的不过是他的衣冠[2]。又如秦始皇巡游东海、汉武帝泰山封禅,都无不透露出对生命的渴望。而李少君的传闻就是以死者身体的神秘消失为征兆,被认为死是遗其形骸而化去,是死后登仙,故称其为“遗蜕”或“蜕世”。至于飞升,在汉代广为流传,能够像黄帝一样举行封禅而升天;像淮南王刘安服不死之药而升天,甚至其鸡犬也都随他升天;或像卢敖一样服金玉之精,食据说使人身轻的紫芝之英而升天。
总之,西汉哲人、方士、王侯所执着探寻的长生之道并不是要征服死亡,而是着眼于无限地延长生命。“蜕世”和“飞升”他们之间共同联系又强化了人们在无限延长生命的渴望,人们相信达到这样的境地,生命就会有所转化和升华。
从“蜕世”到“飞升”的向往与构建,激起了人们对这种神奇之境的精神幻想。汉代墓葬是汉代民众对于生与死的认识,尤其反映在汉代墓葬图像上,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陵墓画像中“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充分反映了中国早期各种思想和民间信仰的影响。本文以“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为研究对象,在图像的基础上加以文献佐证,提出了从“蜕世”到“飞升”的理想境界并进一步探讨汉人对生死的构想与信仰。
一、汉代画像石中的“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画像及意义
汉画像石中的“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就目前所见出土的内容来看,大约分为以下几种。

图一 山东微山两城出土的祠主受祭图

图二 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祠主受祭图

图三 山东诸城前凉台孙琮墓的祠主受祭图
1.山东微山两城出土的“祠主受祭图”(图一)。微山县文物管理所藏。纵67厘米,横104厘米。画面正中是一座建筑,四阿式顶,前面敞开,两立柱刻画着花纹。男女主人抄手端坐在屋内,男右女左。来宾居男主人右侧,里外各两人,皆戴进贤冠,其中室内两人捧着策板俯首躬身站立。左侧立两侍女。屋顶左右两凤凰,皆口衔丸丹状仙药,预备赠送人间。凤鸟之间有两披发仙人,手舞足蹈,希图讨得凤鸟欢心,获得仙药。另外,屋檐两端还各爬着一只猴子。右侧空中飞着两鸟,其下一大鸟在哺育小鸟,左侧飞鸟下有一头大熊。北壁右侧还有一处题记,自右而左分别为:“永和四年四月丙朔而廿七日壬戍,桓孨终亡,二弟文山、叔山悲哀,治此食堂,到六年正月廿五日毕成。自念悲痛,不受天佑,少终,有一子男伯志,年三岁,却到五年四月三日终,俱归皇泉,何时复会,慎勿相忘,传后世子孙,令知之”[3]。
2.山东嘉祥县宋山出土“祠主受祭图”(图二)。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祠主车马出行图,上层为祠主受祭图。上层的祠主受祭图中,画面左侧是一座由双阙夹峙的二层楼阁,祠主受祭的场面在楼阁内展开。楼阁下层在榻上右端端坐的祠主,明显比其面前的两名跪拜者和身后的侍者以及楼格外的持板谒者要高大的多。
3.山东诸城县前凉台村出土的“祠主受祭图”(图三)。诸城市博物馆藏。纵151厘米,横75厘米。画像分为上下两组。上组,刻拜谒图:上一庑殿顶厅堂,堂中高大的主人端坐于三面有屏的榻上,前置几、杯、樽。屏外五侍者或捧杯、执便面,或执拂尘,或拱手侍分四列侍立;榻前左一吏,右六吏,皆执笏向主人跪拜。堂前二人执笏拜谒,其左右二十四吏役分四列侍立,前二列吏役执棰,后二列吏役执棨戟;左侧二吏执笏跪,二侍者恭立,皆左向;右侧二吏执笏,二侍者右手前伸,皆左向立。下组,刻议事图:二层楼房一座,三楼有六人跽坐,二楼有八人跽坐,楼下有十一人相对,均似在议事。楼外,左六人执笏右向立,右四人执笏左向立。
4.山东嘉祥武氏祠出土“祠主受祭图”(图四)。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刻二层楼房,左右有重檐的双阙,屋、阙脊有仙人喂凤和猴、鸟;楼下男主人左向端坐,接受宾客拜谒,左右有侍者和宾客;楼上有女主人端坐中间,左右有女宾和女仆;楼阁左边有一棵连理树,树下停有屏的轺车和一马,树上停、飞数鸟,一人立于车盖上弯弓射鸟。树上方一列人物拜会。下层为车马出行的场面。

图四 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祠主受祭图

图五 山东嘉祥焦城村出土的祠主受祭图

图六 山东嘉祥五老洼出土的祠主受祭图
5.山东嘉祥焦城村出土“祠主受祭图”(图五)。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车马图,上层即“楼阁拜谒图”。“楼阁拜谒图”的正中是一座高大的二层楼阁,两侧是高耸的双阙,楼阁二层左右房间各有一名妇女凭栏正面端坐,楼阁下层是拜谒的场面,右侧一人面左而坐,左侧一人向右拜伏在地,楼阁内外有六名执板恭立的侍者。在被拜谒者身后的楼柱上,刻有“此斋主也”四字题记。
6.山东嘉祥五老洼出土“祠主受祭图”(图六)。画面分为两层,上层即“楼阁拜谒图”,下层为车马图。在上层的“楼阁拜谒图”中,楼阁下层左侧面右而坐的被拜谒者身上刻有“故太守”三个字,字体是东汉时期流行的八分书。
7.凤凰山小祠堂复原。凤凰山汉墓小祠堂是徐州汉画馆收藏的较为完整的墓前小祠堂。现有祠堂后壁石一方,侧壁石两方,立柱石两方,共五方,唯缺顶盖石。小祠堂左右长约120厘米,前后进深约90厘米,高57厘米。A、B,铺首衔环(小祠堂左、右侧立柱石刻)。纵57、横20、厚20厘米。馆藏。石刻两面刻画,一面为铺首衔环,一面为菱形纹饰。C,六博(小祠堂左侧壁石刻)。纵57、横56、厚19厘米。画面中间为一楼阁,楼内有二人六博,两边有二侍者。楼上刻有凤鸟、猫捉鼠。边饰菱形纹。D,乐舞(小祠堂后壁石刻)。纵57、横100、厚14厘米。画面中刻一厅堂,两边有双阙。堂内有男女二人对坐,堂外两边有二侍者,堂前有乐舞表演。边饰菱形纹。E,建鼓舞(小祠堂右侧壁石刻)。纵57、横56、厚19厘米。画面中刻一建鼓,两边有二人击鼓,鼓上有羽葆华盖。建鼓后有二人跽坐手摇鼗鼓、吹奏排箫。边饰菱形纹。

图七 徐州市铜山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建筑人物图
8.徐州市铜山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建筑人物图”(图七)。纵74、横134、厚18厘米。画面中刻一房屋,屋内二人对饮,屋外一人背袱,一人持物。屋上一展翅凤鸟,其左右各有两只小鸟。房屋的两边各有一株连理木。
9.徐州市铜山汴塘出土“建筑人物图”(图八),纵100、横72、厚30厘米。画面中刻一亭,亭内有二人对坐,亭子上面刻一对凤鸟,天空中有两只鸟飞翔,边饰有菱形纹、三角纹和幔纹。
10.徐州市茅村蔡丘东山出土“建筑人物图”(图九),纵92、横78、厚30厘米。画面凤鸟交颈,下刻一亭,亭内男女主人座谈宴饮。边饰幔纹。

图八 徐州市铜山汴塘出土建筑人物图

图九 徐州市茅村大蔡丘东山出土建筑人物图
11.徐州市茅村蔡丘出土“铺首、伏羲女娲、宴饮”(图一〇),纵92、横177、厚25厘米。画面分为三格。中间一格刻建筑人物,房屋斗栱下立柱弯曲,屋顶上刻有一对凤鸟展翅;左面一格刻铺首衔环,铺首上方刻双龙交颈;右面一格刻铺首衔环,两边刻伏羲、女娲。边饰幔纹。

图一〇 徐州市茅村蔡丘出土建筑人物图铺首、伏羲女娲、宴饮
12.徐州汉画像石馆馆藏“人物升仙图”(图一一)。纵76、横182,厚25厘米。画面横向分为三格:左边两格刻柿蒂纹、菱形纹;右格刻二人正面端坐于榻上,均肩生羽翼。边饰斜剁纹、幔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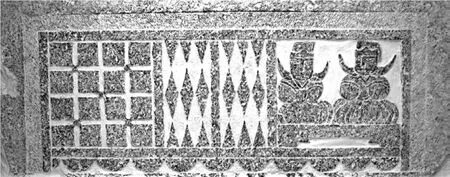
图一一 徐州汉画像石馆馆藏“人物升仙图”

图一二 江苏铜山洪楼汉墓出土的升仙图
13.江苏铜山洪楼汉墓出土的“升仙图”(图一二)。纵122、横298厘米。画面右刻两架云车,分别为鱼、龙所拉。左下部有雨师布雨、雷公布雷,还有仙人骑白象、风神致风。画面的左边立者为方士,跽者为墓的男主人,其意在导引升仙。右上角二高髻女子,左边当为墓的女主人,她正在向家人揖别仙飞而去。这幅巨型画面表现的是墓主人在方士的导引下,在众神灵的簇拥护卫下,浩浩荡荡飞升天国的情景。
14.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的“导引升仙图”画面用阴线刻线描的手法,表现的是墓主人在方士的导引下,在众神灵的簇拥护卫下,飞升天国的情景。图中主要刻有鱼车、鸟车、龙车、鹿车;并有虹龙、星象蟾蜍,风神致风,伏羲、女娲等,一派天国景象。古人死后,想归入天国。就是屈原诗中“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的景象。
15.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的“升仙图”。该石纵41,横240,厚15厘米。画面上刻从左至右依次为凤鸟、二人御龙、九尾狐、一人戴笠执锸、乌龟,右边一兽漫漶不清;下面中间刻羽人骑虎、骑鹿,左为东王公正面抚案端坐,右为西王母,中刻一面具。
“祠主受祭图”,又叫做楼阁拜谒图或楼阙人物图,一般位于画像石祠堂的后壁,如山东微山两城、山东嘉祥县宋山、山东诸城县前凉台村、山东嘉祥武氏祠、山东嘉祥焦城村、山东嘉祥五老洼、安徽凤凰山小祠堂的后壁石刻等;当人们到祠堂来祭祀死者时,面对的正是祠主受祭图。图像的简化形式是厅堂拜谒,如山东微山两城永和四年(139年)祠堂后壁石,大厅内墓主夫妇并排正面端坐,男墓主左侧有两人持笏拜谒,厅外左侧有两人等候接见,右侧有两女子袖手站立,厅堂顶上刻仙人戏凤和猴子上攀,空白处刻飞鸟和一只熊。由此可见,厅堂或楼阁拜谒是祠主受祭图最基本的要素。
“升仙图”,又为导引升仙图,一般图像的简化形式是墓主人在方士的导引下,在众神灵的簇拥护卫下,飞升天国的情景。图中画面的左边立者为方士,跽者为墓的男主人,其意在引导升仙,右上角的女墓主也向家人揖别仙飞而去。画面还刻有两架云车,分别为鱼、龙所拉。左下部有雨师布雨、雷公布雷,还有仙人骑白象、风神致风。
现在,对于“祠主受祭图”的研究,学者都有过详细阐述。以信立祥先生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一文“祠堂后壁楼阁拜谒图的内容和意义”和杨爱国先生的《“祠主受祭图”再检讨》最具有代表性,其他学者对于汉画像石中的“祠主受祭图”图像研究也有精彩论述。首先,信立祥先生认为“祠主受祭图”作为祠堂后壁石刻,是子孙祭祀祖先之处,其上面祠堂正中画像就是祠主,而祠主面前的跪拜者当然是其子孙后代了。墓地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墓祭用建筑,是维系现实的人间世界与地下鬼魂世界关系的纽带。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墓地和祠堂是“祭祀是居,神明是处”是“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在那里皆有神灵[4]。
其次,杨爱国先生认为既然墓上祠堂的功能是用来祭祀死者的,那么祠堂里的图像就应该是以墓主人为中心来安排的。在《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一书中,曾专列一章从建筑的性质、图像的题材内容及其布局、建筑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死后世界三个方面对祠堂里以墓主为中心的图像布局进行了论述,认为:祠堂后壁的图像是祠堂图像的中心,尊贵如西王母、东王公之类的神仙,与其他图像一样只是陪衬。得出这样的认识:一是祠堂后壁象征祠主夫妇受祭的图像占据着祠堂的中心位置,从而在布局意义上确立了主人地位。二是就单幅图像而言,祠主受祭图是整座祠堂中画面面积最大的,体现了人们对它的重视。三是它正好面对前来祭祀的人们,尽管象征男墓主的形象在图像上多是侧身接受拜谒。
目前,学者们对祠堂后壁中祠主受祭图含义还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楼阁的象征意义、楼阁中的人物、楼阁旁的树、车等也都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见解。除此之外,又从楼阁与双阙,楼阁中的人物,大树,树下车马,车马出行图多种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本文对此不再赘述。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可知汉代墓葬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国早期各种思想和民间信仰的真实写照;汉画像石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重在它的象征意义。“祠主受祭图”不是简单的家人祭拜,也不是再现墓主本人的形象,以及在祠堂接受后人的祭祀,而是希望通过受祭以后在陵墓中蜕世,然后飞升到不受外界干扰的仙人世界。
“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无论在祠堂和墓葬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反映墓主受祭与升仙的主题。例如山东微山两城出土的“祠主受祭图”,山东诸城县前凉台村出土的“祠主受祭图”;江苏铜山洪楼祠堂出土的“升仙图”、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的“升仙图”,均表现的是祠主受祭、天上仙境。周到先生认为,在汉画像石中“道家迷恋羽化升仙的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与汉代人们信仰灵魂不灭的思想有关,是想让死者灵魂从墓室中驾驭着画像上的飞廉、应龙、腾蛇、翼虎、白鹿、仙鹤升腾飞仙。”[5]汉代盛行厚葬,人们都以为人死后的灵魂是不灭的,可以升入天界,如马王堆1号汉墓非衣帛画,描绘了灵魂升天的情景和灵魂所生活的天界仙境,以寄托渴望成仙的遐想。所以,“受祭”与“升仙”汉画像石,反映了汉代人们较为普遍的追求——希冀长生不老和死后升仙的愿望。
二、“蜕世”和“飞升”的内在象征与空间表现意义
“先死后蜕”的“蜕”,在《无上秘要》中曰:“夫尸解者,形之化也,本真之练蜕也,躯质之遁变也”,《续仙传》云:“其隐化者,如禅留皮换骨”。成仙尸解余“蜕”,不留肉身,而遗留衣物(身外之物,包括衣、杖、帚等)。其肉身似返归真,裸而离世。《神仙传》:“王方平死三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解开也),如蛇蜕耳。”当中隐含的观念随后发展成道教中的“尸解”概念,关于尸解,人们经常引用《抱朴子》中的一段话:“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
关于尸解一说,由来已久,据《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宣之时,邹之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都是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6]形解销化,又称尸解飞升。战国时,燕齐一带的方士将其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道家、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揉合起来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社会,其法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企图长生求仙。其所谓“方”指不死的神方,所谓“仙”指长生不死的神仙。另外,马王堆帛书《十问》载彭祖传授王子巧接阴之道曰:“彼生之多,上察于天,下播于地,能者必神,故能形解。”这里的形解,亦称“尸解”。“尸解”(刘仲宇释)条曰:“指弃尸于世,而自己却解化仙去。……如汉末三国时葛玄自称‘吾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于是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神仙传·葛玄》)……道教认为尸解而死,不是真死,而是托死化去。且尸体下葬后经太阴炼形,仍可白骨再生。然而因与肉体飞升的理想尚有距离,故视作仙法下品。……‘夫解化之道,其有万途。或隐遁林泉,或周游异域……或授箓而记他生……或髻发但存,或衣结不解,乃至水火荡炼,经千载而复生。’……后世道人化去,亦泛目之尸解以神话之。”[7]
“飞升”在汉代广为流传。《论衡·道虚篇》便记载时人对升天的几例:其一是关于黄帝——“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须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七十余人”。其二是关于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犬鸡食之,并随王而升天去。”[8]还有以其他方式飞升,一,服食飞升,包括服食丹、符、丸等。人物有《神仙传》中的沈文泰、陈安世、李八百、玉子、九灵子、北极子等。二,乘龙(或其它神兽)飞升,如《列仙传》中的马师皇、黄帝、陶安公、茅君之高祖父——以上乘龙;子英——乘鱼;东郭延——乘虎豹,这些人物均骑神兽而飞升。三,修道有成、乘羽车而去。如《列仙传》中的木羽;《神仙传》中的茅君、安期、刘纲等。可见,飞升成仙作为得道的最高境界。
巫鸿先生认为汉代墓葬图像生动地表现了汉代人的宇宙观和生死观,这些证据所呈现出的汉人的死后世界,幻想将死者的灵魂送到一个仙境,或是将通过死者的身份变成一个不朽之身来达到长生的目的。
“蜕世”与“飞升”应该从墓主人的视角加以观察来理解,墓葬本身是“为死者开辟的创造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进入的是‘天人合一’的,祥瑞纷呈的,有各种神灵护佑的,可辟邪消灾的,能羽化升仙的,有理想道德规范的,充满着安乐生活享受的天地境界。”[9]表现出一种人们自古以来对于长久延续生命的企望[10]。例如濮阳西水坡45号墓古盖天图式墓中的龙虎图案;表明西汉人们热烈追求神仙境界,强调人死之后形体的消亡和灵魂的转化重生到追求在世飞升和长生不老,使升仙成为生命的升华。郑岩指出:“东汉时期壁画墓与画像石墓大量流行,描绘墓主形象的图像随之大量出现,一部分见于地下的墓室中,一部分见于地上幸存的祠堂中。”[11]在汉代画像石中会经常看到祠主端坐在阁楼里接受家人的祭拜的画像。对于这一画像,据统计如山东微山两城、山东嘉祥县宋山、山东诸城县前凉台村、山东嘉祥武氏祠、山东嘉祥焦城村、山东嘉祥五老洼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墓葬;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的多幅墓主人的升仙图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坟墓建筑装饰是以墓主为中心,保证墓主在阴间生活殷实、把阴间生活需要的东西尽可能的全面的表现出来,使死者在阴间不在感到寂寞;……在前者的基础上,人们为死后生活设计了更加美好的蓝图、那就是升仙,过上神仙的日子”[12]。汉代画像中的“祠主受祭图”和“升仙图”,不论是墓主人还是其亲属,都试图通过这一手段,达到从“蜕世”到“飞升”的一种超自然的目的,再造出一个人们死后期望从受祭——升仙,达到彼岸神奇世界。
三、汉代墓葬画像与汉代民间宗教信仰的生死观
目前,我们见到的汉代画像石祠堂基本上都是东汉时期的,分布在北自山东东阿,南到安徽灵璧,西起山东嘉祥,东至山东临淄,这样一个南北狭长的地区。其中以微山湖周围及其临近地区的山东滕州、微山、嘉祥及江苏的徐州最为集中[13]。
“祠主受祭图”正是该地区的祠堂汉画像的代表,画像表现的是墓主人接受家人的祭拜,例如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吊唁图,正是描绘的是丧葬吊唁的场面。首先是官员们的祭拜,在前室东西两壁安排了两组吊唁活动,一是进入庭院的吊唁;一是在祠堂前进行悼念活动,官吏们在丰盛的祭品前,或跪伏在地,或躬身施礼,聆听着主祭者对死者的悼念致辞。其次是祠堂周边的礼拜活动,众多亲友们或驾车,或牵羊,捎带着酒、食物和一袋袋的粮食,来到祠堂进行吊唁祭祀,祠堂两边大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种礼品沿途摆放。吊唁在汉代是乡间最重要的礼仪,在讲求以孝治国的汉代尤其为社会所看重。
“升仙图”表现的升仙场景是汉代陵墓中的主题,在汉代铜镜上记述了这样的内容:“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徘徊神山采芝草。”追求成仙、长生不老的思想由来已久。仙人们长生不老,永葆青春,遨游世界,不知饮食之苦,这种境界无疑是当时人们都憧憬不已的。汉武帝时期,是方仙道达到高潮的时期。汉武帝的求仙,在他身边,围集着一大批著名的方士,如李少君、李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劝说汉武帝要成仙,就要祠灶、封禅和化丹砂为黄金,黄帝成仙就是这样的,汉武帝果然就这样去做。公孙卿上书说黄帝铸鼎而成仙,现在宝鼎已出,只要封禅、炼丹即可成仙。武帝叹道: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庄子》一书中充满了对仙人仙境的种种描绘,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另外,徐州市铜山汴塘、徐州市茅村蔡丘东山出土“建筑人物图”,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称此类图像为坟墓中的夫妇,认为画中端坐的夫妇不是表现其生前姿态的肖像画和坟墓中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在彼岸世界中的形象[14]。又如徐州汉画像石馆馆藏的“人物升仙图”。画面刻二人正面端坐于榻上,均肩生羽翼。画像说明夫妇在墓室中已经升入了仙境,羽翼是成仙的标志。公元2世纪末的著作《论衡》记载仙人的形象:“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这里所指的仙人是从肩上长出来的一排羽毛,在《论衡》中所谓的翼。“人物升仙图”中的人物均肩生羽翼,表明已经升到天国里了,而该画像石又是墓室中出土的,这里既是墓穴中的世界,同时也是天上的世界,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墓主人通过受祭又经过尸解然后飞升呢!
“蜕世”、“飞升”与汉代的民间生死信仰的起因。在汉代陵墓图像中可以看出这种信仰已演化成一种普通的民俗——生与死。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对死后生活世界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显示出民俗巨大的渗透力和张力,而最终出现了民间灵魂信仰的盛行局面。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卷108《要诀十九条》云:“其欲知身成道而不死者,取诀于身已成神也,即度世矣,以为天信。”并指出:实现长生不死绝非易事,有时要借助某些法术来完成,譬如,尸解、飞升等。道士李少君的尸解成仙,类似此例,谓之甚多。《神仙传》也多次谈到尸解成仙之事。如卷3《王远·蔡经传》中载两位人物就以尸解脱世而去,且王远点化蔡经时语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汝生命应得度世,欲取汝以补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15]
另外,《太平经》认为,神鬼与凡人一样需要饮食。《太平经》中的祭祀,依对象不同可分为两类:其一是祭祀天地鬼神;其二对“家先”之祭祀。家先也要靠宗族后人的祭祀,才得以安宁。“祠主受祭图”位于墓上祠堂后壁,当人们到祠堂来祭祀先人时,面对的正是它。由于它处于如此显要的位置,对它的图像意义的判断和理解直接关系到对祠堂性质,乃至汉代丧葬礼俗和汉代人生死观的认识,因此,学人对它给予了高度关注。关于祭祀之事,《后汉书·祭祀上》曰:“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16]据有关研究表明,祭祀行为发源于远古时人对自然力量的自发崇拜。所以,画像石上出现“祠主受祭图”也就不难理解了。
“尸解”,是把“尸体肉身”之精气化解为神,遗其形骸而仙去。汉王充《论衡·道虚》:“所谓尸解者,何等也?谓身死精神去乎,谓身不死得免去皮肤也……如谓不死免去皮肤乎,诸学道死者骨肉俱在,与恒死之尸无以异也。”《晋书·葛洪传》:“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这个“尸解”,尸体明显是穿越了,而不是气化了。这里就包含了道教崇尚肉身长生不死的内在因素。
众所皆知,《太平经》特别关注超离此世而成仙,这种唯有通过修道登仙这一途径才能驱除死亡的威胁、获得生命永恒价值,这种不朽成仙观念,不仅为东汉的民间思想所接受,而且在民间广泛传播。升仙也是汉代思想与信仰中的特殊表达方式之一,尤其在汉代墓葬艺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民间思想中的求仙复出与升仙不死在当时占据主流,墓葬又是唯一来表达的手段,所以用象征性的手法加以表达。
由此可见,通过以上分析,祠主“受祭”到“升仙”以及“蜕世”到“飞升”,发生了重要的转化,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们只是替代死者灵魂的一个符号,人们并不在乎图像与其原型之间有多少异同”[17]。而主要表达的是通过“受祭”到达理想世界——升仙。“受祭”也不再是简单的祭拜,而是作为升仙的阶梯。“受祭”、“升仙”这些相关性的图像组合,让我们看到汉人对生死的理解。“受祭”、“升仙”的图像解释了生命的“蜕世”到“飞升”,这主要追随于在汉代相当普遍的民间信仰观念;对汉代人来说,死亡只不过是灵魂离开肉身而已,是新生命的开始。
[1]《抱朴子》,卷2,第 6页。这段记载是《史记》(第1386页)一段文字复杂化的版本。
[2]《史记》,第 1396页。
[3]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51页。
[4]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5]河南博物院《河南汉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艺术成就》,《周到艺术考古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
[6][汉]司马迁《史记》卷 28,第 1368~1369页。
[7]胡孚琛《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608页。
[8]黄晖《论衡校释》卷 7,第 317~318页。
[9]蒋英炬《关于汉画像石产生背景与艺术功能的思考》,《考古》1998年第 11期,第 90~96页。
[10]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68页。
[11]郑岩《墓主画像研究》,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同 [3],第 218 页。
[13]同 [3],第 164 页。
[14]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商务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5页~26页。
[15]姜守城著《《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87页。
[1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7,第 3157页。
[17]郑岩《中国表情——文物所见古代中国人的风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杨赫,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杨孝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