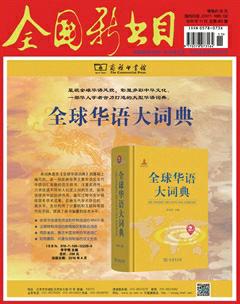独药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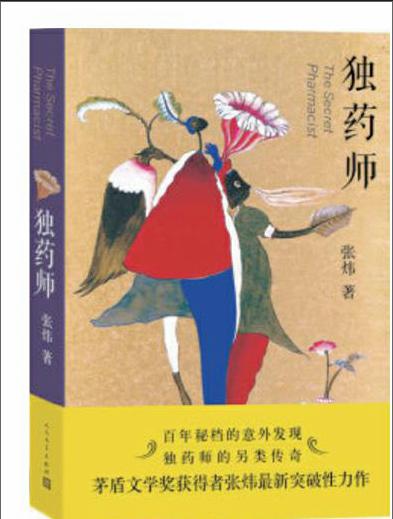
张炜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9787020115228/2016-05/36.00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基督教登陆东部半岛,教会学校及西医院初步兴起。半岛地区首富和养生世家的季府面临空前挑战。与此同时,因与北方革命党统领的密切关系,季府被卷入一场场起义的鏖战之中。季府主人、“独药师”第六代传人季昨非陷入与养生前辈的对峙纠缠、与西医丽人的缠绵悱恻、与兄长至亲的生死诀别……在长生、爱欲、革命之间,这个曾经清闲无为,作风虚浮的少爷能否接过传承百年的衣钵,守护日渐式微的季氏家业?他在革命的召唤中又该何去何从?
半岛养生秘术与革命史料首次披露,历史猛料与叙事陷阱暗合交错。这是张炜自《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充满象征和隐喻,背后处处隐伏着历史猛料和叙事陷阱,这种叙事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文字、现实与历史的张力和冲击力。小说叙事的魅力已经不是表面的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世界。
《独药师》书摘
作为声名显赫的季府主人,我对这个身份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但自己是半岛和整个江北唯一的独药师传人,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荣誉。在至少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季府不知挽救和援助了多少生命。在追求长生的诱惑下,下到贩夫走卒上到达官贵人,无不向往这个辉煌的门第,渴望获得府邸主人的青睐。
父亲离世后,我就成为那个最尊贵最神秘的人,接手人类历史上至大的事业:阻止生命的终结。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看成一个谎言或神话,但更多的人还是认真记取种种诠释,认为它起码是有益无害的:即便不能永生,至少也可以长存。
我作为第六代传人,有着无法掩饰的野心:着手整理季府大事记,将养生术的部分独立出来,给家族中九十以上的长寿者单独列传。我发现这其中有三个的确活过了百岁,另有两人一生都没有犯错,最后“仙化”了。
为证明这个家族所拥有的神秘能力,保持她巨大的无可比拟的荣誉,我先后走访了无数人,查看了不同的志书。可惜各种无法坐实的传说仍旧具多。好在几位先祖最后的逗留地还在,我一遍遍去那儿瞻仰和怀念。那是临海的一处海蚀崖,面对虚无缥缈的渤海与黄海分界线,雾气缭绕。先祖当年就站在这个崖上,最后看了一眼美丽的半岛山川,纵身一跃,成为不朽的仙人。
确认永生者的行踪成为我的重大责任。榜样的作用在于切近的说服力,我为他们的一生事迹亲手绘图并作出详细注解,先是油印成册,后又试过铅印,最终找到了半岛地区仅存的一家石印所精工制作。
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季府的宿敌。这个人住在同一座城市,活动范围大得惊人,迈动那双不知疲倦的脚走遍了大江南北。此人自然也是一个养生家,曾为季府老友,一度与父亲来往密切,最后才决裂分手。他叫邱琪芝,曾与祖父一起下过棋,推算起来也有一把年纪。
邱琪芝生在富裕之家,一生倾心于长生修炼。传说他的府邸中设有考究的丹房,修持也算清苦。此人诋毁季府,用语辛辣:所谓“秘传独方”不过是季府用以聚拢人脉的东西,目的全在于拓展实业,“独药师”不过是浪得虚名。
我相信父亲在世时不可能对其一无所察,之所以充耳不闻,皆因为心思用在其他方面。他当时忙于为革命党筹措银两,家族实业尚且无暇顾及,又岂能理睬这些谤言。先人已逝,时至今日,我知道从头维护家族荣誉的时刻到了。我需要蕴蓄足够的勇气,直面这个可怕的敌手。
这样的时机终于到来。那天我独身一人,未带一个仆人,好像单刀赴会。
邱琪芝那会儿正在静坐。几乎没有人可以直接进入他的私宅,我却被破例应允。由仆人引路,穿过几道曲折回廊,踏入一个生满橡树的后庭。当中一间小小草寮,一个扎了马尾辫的人坐在蒲团上,正以掌抚面。我待他双手挪开,以便看清这张可憎的面容。大约三五分钟之后,他双肘垂下,一对细长眼缓缓睁开。
我清晰地记住了那个瞬间,很久以后还对袭来的惊讶难以忘怀:眼前绝非一位百岁老人,看去顶多六十多岁,不,或者只有五十余;面庞无皱,几丝白发,颜色滋润。他轻轻扫来几眼,很快对来人失去兴趣,眼皮垂下了。
我开门见山连连发问,用语犀利。他依旧垂目,纹丝不动。这样捱过一刻才问:“多大了?”“十九。”“好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他站起,捏捏我的肩膀:“我算是你的父执辈了,其实还不止呢。第一眼想起的是你爷爷,我们一起下棋,我赢过三局。”
我不吱一声,好像在听黑白棋子落下的脆响。那声音若有若無。这样静默一二分钟,他再次开口:
“你谈的这些也太麻烦,来日方长,咱们留待以后罢。孩子,我今天只想告诉你,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我们有个共同的对手,它就是那个西医院,麒麟医院。”
与宿敌的第一次交锋就此告终。我许久之后回忆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他仿佛施以魔法,瞬间将一头冲力十足的牛犊安抚下来。当然我心中的愤懣仍未平息,一切还需时日。也许时间才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他说得对,那所教会医院才是我们的共同对手。该院背后依赖的是美国南方浸信会,自新教在半岛登陆以来,历经三十余载,筚路蓝缕,而今已有两处规模颇大的教堂,还兴办了学堂和医院,成为该地区最隆盛的存在。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将孩子送入洋学堂,生病则去西医院,渐渐酿成风气。麒麟医院不断传出惊人神技,比如通过手术让盲人复明,让气息全无的人死而复生。这一切都加剧了传统医学的沦落,动摇了半岛人苦苦培植了几个世纪的信心。如果我不经提醒就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整整多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几个显要人物进出季府药局。
像父亲一样,我越来越厌恶府中的烦琐实务,它们悉数交由府上老人打理。除非是极紧要的事项,主人一般不被打扰。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清闲无为的少爷,一个作风虚浮的主子,并未体察时代变局,也不知季府正面临艰难的赓续与抉择。作为一个新的掌舵人,我已经太疲惫了,仅仅是驱除头脑中的嘈杂就要耗去大半精力。endprint
我承认,那一天邱琪芝的及时点拨让我心头一悸。后来凡有机会我即痛陈西医弊端,在季府所有老友中申明立场,守护传统。我知道危机感由日渐式微的季府药局开始,已延伸至更深更远。我不想做一个心胸狭窄的诋毁者,而是要更加深入地追究源头义理。有一天我与邱琪芝在街头不期而遇,他不容我寒喧,短促而严厉地盯来一眼,嘴角瘪着扔下一句:“做得好!”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就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从这个宿敌身上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据说父亲只踏入半步又撤回:一半因为繁忙,一半因为厌恶。父亲不能容忍与季府恪守的理念相冲突的一切,无论它隐蔽得多么巧妙。邱琪芝从根本上怀疑季府那些丹丸,认为它们于事无补;还有极精微极严格的吐纳术,也被其质疑。邱琪芝来往于大江南北,广采博闻,深研典籍,创立学问,据说比半岛上几千年前的方士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方士们在中国历史上既大名鼎鼎又臭不可闻,如骗过秦始皇带走三千童男童女远涉东瀛的徐福、在咸阳城被坑杀的那些倒霉的家伙。
我在十七岁之前已经读完父亲交与的有关于“内丹”的藏书,毫不费力地完成了从虚静到内气周流的功课。我能够在双目垂帘的任何时刻,在仰躺或半卧、甚至是缓步行走中,让无形之气恣意流灌。如果我愿意,闭上双眼就可以感受内气怎样伸长了柔软的触角,小心地攀着背部一个个圆润的骨节往上爬行,翻山越岭,蜿蜒向前。我以内视法即可透视各个器官的精巧形状,以及荧荧闪烁的不同色泽。它们或愉悦或懊丧、经过一阵休眠醒来后的慵懒及顽皮表情,都在洞悉之中。我与它们建立了深长的友谊,却又不失威严,能够在肃穆的瞬间让其一一振作,像士兵一样挺身待命。
无须讳言,季府的生命重地即丹房。在曾祖父之前它是一个颇为显赫的存在,那是一处高耸的碉楼,里面有通宵达旦的神秘烧炼。至祖父开始这熊熊炉火才一点点熄灭,而今只余下冰冷的灰烬。后来的丹房其实就是药局作坊,独药师隐于其中一间密室,小心翼翼地操作,严格遵循古老义理悟想运思。由祖父做出的伟大变革即引进气息周流学说,最后竟将其与丹丸并列,视为不可缺失的仙鹤之两翼。就此诞生了一方静谧独守的领地,它只属于季府老爷一人。我继承了祖上这间密室,却无法忍受它的幽暗昏沉。经过一次次小心谨慎的改造,它如今已变得明畅了许多。
我在这儿冥思和猜悟,常常想到一個人,想他的语气和形貌,他的用心。
这个人就是邱琪芝。对季府而言,此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奇异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竟然让我从敌视到忍受,再到惘然,继而痴迷起来。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源自幽深学问底部的友谊与信赖,这就令我渐渐怀疑起父亲,为早逝的先人惋惜:他大半因为误解和急躁而入迷途,既伤害了自己的修持,也错失了一位伟大的朋友。
如果父亲晚年在交谊方面能够稍稍调整,也就不会犯下那些大错了。我对这一切暂时还未能一一认定和鉴别,但显而易见的是,某些可怕的选择导致了他的早夭,只活了七十四岁。对于独药师来说这寿命本身即不可饶恕:让家族蒙羞,令颜面扫地。
父亲的过早去世始终成为邱琪芝手中的一个把柄。他在我面前只一次提到了这一点,但我们俩只要在一起,他抬头瞥来一眼,我就能从那双长长的外眼角里看出对父亲的怜惜。我越来越无法怀疑这个长者的纯粹以及仁者的品质,甘愿让他引领,以纠正父亲那一代形成的可怕偏离。我身上鼓荡着一种责任,而且日益炽热。自此以来,我明白半岛方士们几千年开拓的事业不仅没有湮灭,而且还在暗中生长。这个世界秘不示人,它绝不会显现于声名巨隆的庙堂,而只存于顽强执拗的个人。邱琪芝掀开了一角,已让我震惊不已。
我知道,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如果是一块好钢,还需要数次淬火。我仿佛看到自己的赤体浸入不同的液体,激起泡沫四溅,直到颜色暗淡,那只夹住我的铁钳仍不松开。这个由宿敌变身的导师双目微眯,不动声色,一根马尾辫默默低垂,正紧紧握住钳柄。他问道:
“‘吐纳是气息的周流,它无形无迹;‘餐饮又是什么?”
“那当然是吃喝了,就是每天进食。”我答道。
“你说的是‘膳食,这也重要。这里的‘餐饮是指人的一生一世,如何用眼睛看取周边世界。”
我按住惊叹:“看什么?”
“什么都看,人,花,云彩,你能想到的一切。你用什么目光去看,结果也就不同了,这就是‘餐饮。‘膳食不用说了,还有‘遥思,就是人该怎么想事情。概括起来说,‘吐纳是气息,‘餐饮是目色,‘膳食是吃喝,‘遥思是意念。你先把这四样弄熟,然后才算入门。”
我那会儿只听得懂极少的部分,心里却充满好奇和感激。我知道这完全出自一个无私而高尚的灵魂,他深知我正处于一个危险时刻,担心伟大的传承会随时终止。他无比痛苦地指出一个事实:整个半岛已在长达一百四十年间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仙人!我听到这里再也无法沉默,脱口而出:“不,不对!我们祖上至少有两个!”
我大声喊过之后,有一二分钟的寂静。他看着我,抚一下我硬倔的头发,脸转向窗户。这样过了四五分钟他才吐出一句:
“你那两位先人,都是因为女人,跳崖身亡了。”
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愤怒和惊惧让我双拳紧握,全身颤抖。但我说不出一句话。接下去就像第一次见面,他叹息着拍拍我的后背。我嘴巴张开,露出了坚实齐整的一排“马牙”。邱琪芝摆摆手:“算了,我不该说破。”
我心里恨着那一场谈话,但好像并不太恨邱琪芝。我们继续往来。他吸引我的东西太多了,就因为令人着迷的这一切,我暂时还不会离去。午夜里想到自己的韬晦和隐忍、这种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时有自责。可是他真的侮辱了我们家族里两个显赫的祖先,这等于将我精心修订的石印族史撕掉了两页,好比釜底抽薪。
以前认为“吐纳”是烂熟于心的,与对方相处日久才恍然大悟,那实在只算一点皮毛。这使我愈发相信他关于父亲的论断:过于相信那服独药了,说到底它不过是支援生命的一种外力,并未牵涉生命的根本。我心里多少能够同意,只是出于家族自尊及其他,当面没有附和。
我与之相识的第四个年头,叹服逐步淹没了最后一丝疑虑。总之我们已由宿敌变为朋友,渐渐能够一起谈论养生,还有其他无法穷尽的一些话题。我全面投入新的修持,身心予以强烈回应,好像新生般地面对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是向内打开的,外部世界简直糟透了:半岛惨案一桩连着一桩,革命党的暴动正经历第十二次失败,土匪们不断制造绑架事件,一些豪门大户正酝酿逃离。清廷摇摇欲坠,驻守半岛的兵士变得嗜血。邱琪芝面对可怖的时局说了令人难忘的一席话:
“凡乱世必有长生术的长进,春秋魏晋莫不如此。我们如今又进入乱世,这样的年头除了养生,不值得做任何事情。只有生命危在旦夕,才更加明白生命的宝贵。”
我半晌不语,因为这让我想起了父亲的遗言。看来两个对手至少在这方面达成了一致。
在那个诸事顺遂的春天我正好二十四岁,接下来却经历了一生最大的挫折。我可能永远都搞不明白:这是命中必有的一个关卡,还是无比老辣奸诈的江湖术士设下的圈套?我不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也想不出以他的胸襟与气度,竟会如此卑鄙地加害后生。这个涉世不深的人对他是如此地信赖与忠诚,已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和家族事业托付与他。
起因是我在这个春天里患了一种罕见病症:下腹发烫以至于烧灼,焦躁难耐,极度渴望什么却又无以名状。我不知这是否因为过分沉迷典籍及其他。我的生活过于单调了,或者单调得还不够。我没法让自己安定下来,双目烧灼,长时间干枯无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双泪喷涌。下体胀痛,牙齿磕碰,有时一连几天难以安眠。
邱琪芝看着我,沉默一会儿说:这是人生必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趁着强烈的欲念还没有把你烧成一把灰,就赶快行动起来吧。这说到底这还要求助于他人,你自己是做不来的。好的“合作者”是这样重要,不可或缺,这需要是一些品质高尚的人;这些人可能个个都被误解,却又在所不惜,因为他们从心底明白要做什么。一旦开始了则容易许多,要顺藤摸瓜走下去。这中间少不了我的点拨,既不至于走火入魔,又不会劳而无功。那些好人会慷慨相助,只要你心存感谢就行。我实在等不及他的饶舌,就迫不及待问一句:“这些人是谁?”邱琪芝挠挠头皮,把垂到胸前的马尾辫轻轻荡开,回答:
“姑娘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