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源
李万华
一
我一直想知道,开始是否就是一个点。如果是,这个开始便是一个单向的发展过程,它的一头悬崖峭壁,绝然孤立,没有粘连,没有依靠,另一头如同流水,向前涌动,连续不断,走向分明。它或者直线前行,或者蜿蜒曲折,极尽柔婉之能。然而时间中没有一个孤绝的点,那怕这个点小到看不见,抑或大到无法触摸。除去万物变化这个外壳,时间还有一种模样,那便是,时间如同一串糖葫芦。没有一个孤绝的点,那么,开始就不是一个点。开始如果不是一个点,它必得两端延伸。如此,便会有诸多开始相重叠。结束亦然。如果真是这样,开始便没有开始,结束也便没有结束。
三十年代中叶的一个端午,那是清晨。青藏高原的端午时节,气温依旧只有十几度。又常有阴雨,于是端午就有些烟雨微茫的寒凉。年轻的祖母翻身起床,掀起门帘,推开院门,绕过围有木栅栏的菜园,走出雾霭笼罩的山谷。
然而这并非就是开始。在这之前,我的曾祖父说,他想在端午节这天吃到家乡风味的韭菜馄饨。对于一位从晋南出发,一路向西的生意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他经营生意有方,家境殷实,是附近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但是出生在青藏高原的我的祖母后来说,馄饨是什么模样我都没有见过,怎么做馄饨吃。于是祖母乘着微明天光,开始逃离。
与我祖母的逃离相比,门罗笔下卡拉的逃离远远缺乏戏剧效果。
祖母最终走进的那条峡谷叫珠固峡,珠固峡又连接仙米峡,大通河从峡底穿过。祖母逆着大通河流动的方向,向西北方向,门源县城浩门镇行进。
和现在一样,那时峡谷左侧的高山上,植被繁茂,好鸟向鸣,林中常有动物出没,峡谷右侧,多是连绵草山和滩地,牧人在那里搭起帐篷,放牧畜群。端午时节,青杨树叶刚刚伸展,白桦叶子才在成形,未曾凋落的云杉针叶裹着苍黑。林下灌丛,沙棘灰绿的叶子还无法将褐色枝干隐藏,党参也未曾攀爬,只有早早开花的头花杜鹃正在打苞。大通河水水势高涨,水花清越激扬,时有高低落差,水声喧哗。峡谷幽寂,整日不见行人。因为怕动物蹿出林来,祖母不敢走大路,只选择河右侧的草山前行。那时正逢阴雨连绵,天气寒冷,山坡湿滑,没有固定小道,只能跟随牛羊踩踏的痕迹,行走自然艰难。便是这样,祖母并未转身回去。白天走路,目标通常都是远处山洼或者平地上的一顶牧帐,晚间则借宿那里。那时牧人生活清贫,有时吃一碗酸奶便是一餐。不过牧人都很良善,通常将我祖母当成落难之人,竭力相助。
我见过祖母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梳着发髻,额头光洁,眉毛细长高挑,有着明显的修整痕迹,眼目微笑,藏有一丝桀骜,老式大襟衣服,裁制合体,不像出自山里人家。
快要走出峡谷时,祖母看见一所此处少见的庄廓。院内住着夫妻二人,祖母后来叙述,将那男子称为军官,女子自然是军官太太。夫妻二人何故隐居峡谷,并不清楚。大约隐居生活有些单调,军官太太竭力挽留祖母多住几日,祖母于是住下。军官太太或许出自大户人家,会写毛笔字,会梳各种样式的发髻。有时晨起无事,军官太太便教祖母学梳发髻。那些发髻名称多用比拟,我已忘记。
一次,军官太太拉祖母去一座名叫珠固的寺院游玩。寺院藏在峡谷中的峡谷中,环境清幽,少有人烟,传说那里常有虎豹出没,两人提心吊胆。终于到达。寺院依山而建,山势形同月牙,寺院四周嘉木扶疏,山峰叠翠,云生雾绕。那是祖母见过的最伟岸的建筑群,众多建筑中,重檐歇山式大经堂异常雄伟,共有四层,雕刻精美,绘画美轮美奂,据说那时大经堂重修不久,之前大经堂因为僧人点灯不慎,毁于火灾。
祖母最终还是回到家中,对于这段不该逃离的逃离,并不介怀。在我年幼时,偶尔提起。人事的事情我不清楚,但那条峡谷,还有珠固寺却留下深刻影响:刚刚泛绿的低矮山坡,狐狸将野兔追逐,牛羊和雾霭一起高低,偶尔出现的黑色帐篷,峡谷一侧,山峰高绝,遍布寒树,大通河河水湍急,猛浪如奔,珠固寺雄踞山中,远近闻名……
二
三十年之后,那是六十年代初,父亲同样推开青杨木院门,走进仙米峡,逆着大通河的方向,向西北行进。那时,父亲已经成为一名乡村畫匠,他骑自行车,车后座上捎着油漆斑驳的工具箱。
在父亲的回忆中,我感觉三十年后的仙米峡,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峡谷左侧依旧是险峻山峰和高寒林木,马路依着山势,大通河同样依山而行,河谷并不开阔,有些峡段,马路旁边便是哗哗河水。峡谷一侧,依旧是牧人帐篷、畜群和藏狗。那时秋天刚刚来到,也许上游有大量降水,大通河水挤满河道,河水浑浊,常有小树草根等植物漂浮水面,有时甚至有死去的羊羔漂流而下。
沿着左侧大路,一路骑行至午后,天气突变,暴雨如注。除去树木,峡谷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避雨。父亲顶雨而行,原本以为是一场雷雨,势头一过,雨会停住。但是雷雨渐渐变成连绵阴雨,天空暗云开始覆盖山头。再无法前行,只得去峡谷右侧的牧人家避雨。那一段路程,大通河上恰有人们自己搭建的简易木桥。桥离水面原本不高,现在水势暴涨,桥显得岌岌可危。要么抢渡过河,要么继续淋雨。父亲最终还是选择前者,推着自行车上桥。那时河水已经触到木桥,峡谷中的风又沿着水面挤来,推得木桥摇摇晃晃。父亲顾及不得许多,只低头推着自行车猛行。许是时间刚好,许是吉人护佑,父亲刚刚过得木桥,停下脚步喘息,木桥便在身后被大水冲去。
那一时河谷浊浪翻滚,水声如啸,夹岸碎石亦被大水卷走,灌丛倒伏,天地一片雨雾迷蒙,父亲在被雨水浸透的牧人帐篷等雨过天晴。
但那一场雨一下就是几天。父亲困守牧人帐篷,天天打搅人家生活,过意不去,便将人家一对已被尘埃蒙蔽的陈旧藏箱搬出,用擦皮打磨翻新,上漆,并画上博古和吉祥八瑞的图案。
父亲躬身画画的身影我早已熟悉,那件红漆剥落的工具箱我亦熟悉。多年后,当诸多回忆涌现,父亲在仙米峡牧帐中画画的身影同样显现其间。当年身影虽然未曾亲见,但父亲的叙述足以构筑出一个清晰场面:帐篷已被雨水浸透,时有水珠落地,地面湿滑,局促空间光线黯淡,父亲握笔,有孩子和黑色藏狗偶尔进出,帐篷被掀起一角时,水声哗然,冷风灌入……endprint
三
现在,我也进入这条峡谷,逆着大通河流动的方向,向西北行进。并非刻意要走当年老人们走过的道路,而是,这条路,始终有人行进。一条路,走过一个人,留下一个故事,走过两个人,留下两个故事,走过无数人,便是无数故事。故事太多,容易成为苍茫。然而苍茫还得继续,因为它缠结了许多开始和结束。需要开始的,必得开始,需要结束的,必得结束。
汽车进入珠固峡的时候,已过午后。此时十月刚刚开始,秋气尚未生起,蒙古绣线菊和黄花铁线莲还在开放,阳光的流泻却已经和缓。峡谷中,青杨树叶子已经黄去,小蘖开始变红,坡上草色,也已失去水的润泽,渐渐泛黄。红与黄,足够明艳,加上高远的蓝色天空,雀鹰的翅膀,以及哗哗流淌的大通河水,风生水上,一个秋天已恰到好处。河岸左侧山崖高耸,植被茂盛,崖下柏油路顺山而行。路不宽,只够两辆汽车驶过,好在公路平展,车子左拐右拐,便将一段路扔下一截。
其实我更愿意骑一匹瘦驴穿行这个峡谷。驴太壮,估计会像骡子,骑骡子走路,或者骑马走路,不是粗声大气,就是富户。骑一匹瘦驴,于如烟的细雨之中,于浅到近却无的草色之中,于霜晨的微白之中,于薄暮的昏黄之中,一直向前,一直向前,路旁一灯如豆,身后一叹如昔,那都是别人的时光,饥不从猛虎食,夜不从暮雀栖,如果风起,衣衫如同叶响……然而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太多,如果一旦成为现实,不是传奇,就是轶事。所以现在,我心甘情愿坐在汽车里,捧着大号水杯,从车窗向外探头探脑。
大通河一片静谧。要说静谧,并非毫无声响,而是,这种声响属于天籁。河谷时而开阔,时而狭窄。在开阔处,水明明流过碎石和草棵,却仿佛从丝绸上流过。在狭窄处,水在水上流过,却如同流过巨石。河岸时有植物,绿色一丛,偶尔开出一些颜色浅淡的花,车速太快,总是未及看清,花朵已在身后。也有青杨树,黄了叶子,两三株,或者一排,站在靠近河岸的平地上,流水在它们身旁,它们镇定自如的模样,也许很久没有洪水冲过。闲人很少。车子驶过一段,出现一群羊,染着蓝色屁股,再驶过一段,又出现一群羊,染着红犄角。有时会出现一两头牛,俯首草滩,甩着尾巴。远处山坡,是一些庄廓,和更多的牛。
资料说,大通河又称浩门河,因宋代在河畔筑有大通城而出现今名,源于海西州木里以西沙果林那穆吉木岭,向东流经祁连、门源盆地及甘肃的连城、窑街,于民和享堂汇入湟水,实为湟水正源。大通河水势湍急,迂回山间,下切力强。河两岸有阶地五级,河流沉积物中富含沙金。
途中某段,汽车在一个急速拐弯后,路旁出现一排青杨。在湟水谷地,青杨原本无处不在,无需惊异。只是现在,面前出现的这排青杨如同被人喝了号令,安静地守着规矩,一样粗细,一样高低。显得另类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叶子的黄有别于其他青杨。那是种仿佛藏着一轮太阳的黄,光线自里而外放射开来,穿透叶子筋脉。但那不是跳荡的黄,而是一种沉静的黄。常说莫扎特的音乐是含泪的微笑,现在,这些叶子也像莫扎特,是含泪的叶子,纯净安然,却又带些孩子的快乐。几个路人在那里停了车拍照。用相机拍了黄叶,又用手机自拍,显得兴奋。
我想逢着一个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他(她)应该有着被峡谷风吹红的脸颊和眼睛,有结实粗糙的手,有爽朗的笑和直截了当的话语,但是没有。除去一些经过的车辆,公路长时间保持沉默,林棵间连几只小动物都不曾窜出来。河右岸的山坡和滩地上,偶尔几个人影,要么忙着自己的事情,要么,安静着自己的安静,显然他们不需要打扰,也不需要关注。当下只是他们自己,无需分享,无需在意。
但我还是看见一匹马。那是一匹金棕色的马,我曾经在梦中见过,并且如此记录:“我看见金棕色的马,那么蓬勃的一匹,燃烧,并驰骋。它在我的面前,在无数热烈呐喊的花之唇齿上驰骋……我想着我就是那一匹,金棕色的马,它的鬃毛如此光滑柔顺,根根在握,它的四蹄腾挪,迅急,却又优雅的迈着侧步(马踏飞燕),它的鼻息,我听不到鼻翼翕动的声音,但是温热的气息之浪挟裹面颊,它的眼睛,专注,只容纳天空和花香……它的蹄下闪现时光,以及,连缀成片的花之光芒。而后,我看见孤绝的青海南山。耸立,覆盖冰雪,仿佛披挂莹洁铠甲。凉寒的风,还有凉寒的光。山顶之上,盛开大丛头花杜鹃。蓝紫的花瓣,荡漾水色,伸出手,我握不住它庞大如柱的金黄花蕊。回溯。我看见腾跃直上的马,越过山峰,隐入花丛。那火红鬃尾飞扬的一瞬,马的背影如同蛟龙。龙马精神”。现在,我见到梦中之马就在我的面前,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就是被称作青海聪的大通马。它站在河畔一块石头和杂草共生的空地上,低头啃草。说大通马以走侧步出名,又叫走马。除去那张马踏飞燕的照片,我从未见过马走侧步。我曾经问过一位老人,何谓走马,老人说,马中走姿漂亮者谓走马,我又问马漂亮有何用,老人说,马漂亮就不用劳动。看着那匹也许靠姿色吃饭的马,我希望它在那里昂起头来,摆动尾巴,喷着响鼻,飞扬鬃毛,优雅地走两步。但它理都不理。它专心于唇边青草,显得与世无关。一匹与世事无关的马,怎么能与历史有关,怎么能与演变有关,又怎么能与传奇和佳话有关。我以为自己会有些失望,但还是很愉悦地回到车上。世事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眼前所见,并非包含所有,眼所未见,也非虚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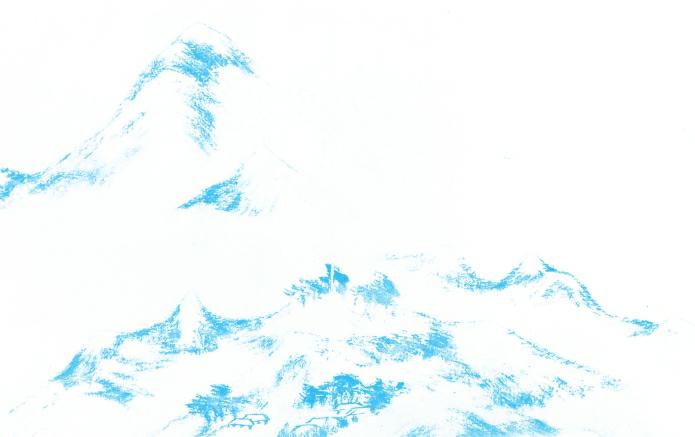
祖母和父親当年所见,一些依旧存在,然而另一些,早已消散。天空存在,但云已飞远,河道存在,但水已不是旧日容颜。坡上牧户,也已发生变化。帐篷早不是当年的帐篷,老人早不是当年的老人,吠叫的狗,早不是当年那一只,游走山坡的畜群,也不是当年那一群。除去这显而易见的一部分,更多隐藏定然也已天翻地覆。但是,要说某种截然不同,我一时又找不到确凿证据。除了沿着山道疾驰的摩托车,除了脚下的柏油公路,除了河道上的几座小型水电站,除了挖沙采金后留下的几个大坑。
四
到达浩门镇时,暮色已浓。浩门镇是无数县城中极普通的一个,老式和陈旧渐渐退却,时尚和开放正在渗透。沿街而立样式单调的楼房,四五层居多,一楼多是商铺,衣服鞋帽,普通百货,药店,理发店,以清真和川菜为主的小饭馆,“亚峰灯饰”,“一方元手机城”,“时尚发艺”,“欧派电动车”……街道宽阔,来往车辆并不多,街道两旁的行道树长势欠佳,树梢上方,电线密集。此时夜从高处漫下,洪水一样。许多卷帘门已经拉下,人们背起包,忙着回家,小小街道,带些入夜前的混乱和杂沓。
浩门古城高踞县城东南的一块台地上,南沿陡崖,北依高粱,东西两面皆是深沟。古城仅开南门,东西两面都是封闭城墙,并掘有护城壕。根据《西宁府新志、地理、山川》及《大通县志、建置沿革》记载,浩门古城为宋神宗熙宁年间所筑,原名达城,崇宁二年改为大通城。史册记载,此城建成后 210年间,金夏交替占领过此城,元代沿用,明洪武八年曾屯兵戍守。古城北廓外,南北设有九条街道,据说当时内地商贸往来不绝,生意兴隆,居民生活殷实,安居乐业。明天启年间,古城失陷于蒙古人。当初蒙古人欲攻此城长达十年,只因防守严密,无法正面攻取,只好智取。据民间传说,蒙古人智取浩门城的方式和西方的木马屠城相似,不过,蒙古人不是用木马,而是骆驼背上的木箱。
此一时,夜色渐渐将小镇席卷,去古城已是不能,漫无目的行走到广场,清冷,几只乌鸦扇着翅膀过去,携带比夜色更深的黑影,几辆自行车随便停靠,似乎已将主人丢失。风从河谷刮来,没有任何形状,但是冷硬,广场边上稀疏的波斯菊,似蹲伏又似蜷缩。路灯开始昏黄,大街越发空阔,偶尔行驶的车辆,安静的停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路人寥寥。这是十月,房屋已经供暖,人们不愿外出。除去汽车偶尔驶过的声音,街道一片寂静。裹紧棉衣,继续穿街而过,回到住宿,结束一天的奔波。
但是我知道,在白天结束,在夜晚也终将慢慢结束的时候,寒霜降临。那些细碎晶莹的存在,将在屋顶,在木叶,在电线杆,在无人关照的玻璃窗户,开始凝结。而它们的结束,又要等待白昼来临。旦复旦兮,暮复暮,如此往复,如此循环。 endprint
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