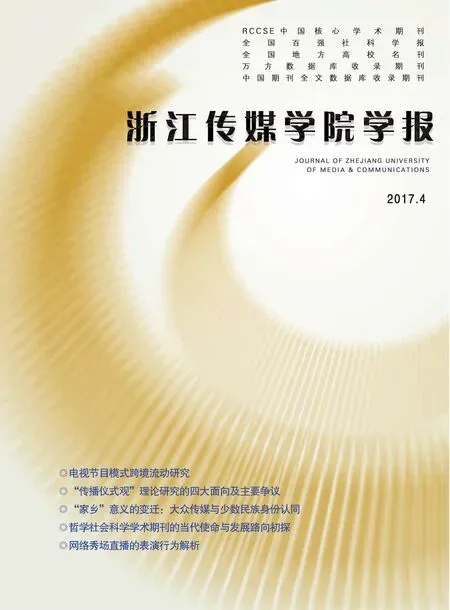大数据背景下音乐版权公共性的再认识
薛 微
大数据背景下音乐版权公共性的再认识
薛 微
文章从音乐版权公共性入手,总结出音乐版权公共性具有的两大特征,即著作权与邻接权、传播权与听众体验高度依存。在大数据背景下,对音乐版权的公共性高效挖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音乐创作的不确定性,拉近了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与音乐消费者的距离,有助于音乐创作的繁荣和音乐作品财产权的实现。
音乐版权;公共性;著作权;大数据
2013年是我国大数据元年,也是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一年,中国音乐产业开始由实体唱片为主的传统模式向以网络音乐为主的数字模式转型。从《201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转型开启了中国音乐产业的大数据时代:2015年由PC端、移动端、电信音乐增值业务三大部分构成的数字音乐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98.18亿元,网络音乐用户规模高达5.01亿,与此同时传统线下音乐唱片销售量则锐减,仅为4361.3万张,比上一年下降23%。音乐作品传播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音乐的著作权和邻接权互动加强,联系更加紧密。本文拟从音乐版权的原初动力——公共性,对大数据背景下音乐版权的新变化进行审视,找出公共性在大数据牵引下的音乐版权运作规律,为产业界的竞争与学术界的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思路。
一、音乐版权公共性的特征
与其他版权作品一样,音乐版权保护法规的出台基于功利主义原则,其主旨是使音乐作品的传播尽可能地扩大到公共领域,通过法律手段保障音乐作品创作者对音乐作品的财产权,鼓励他们创作和传播更多的原创音乐作品。相比其他法律对财产权的绝对保护,版权法对版权这一无形财产权的保护是一种受限制的垄断保护:首先,版权的存在被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过了这个期限就流入公有领域,被所有人自由使用。其次,版权保护的是创作者的表达方式而非思想。再次,“在存续期内,创作者通过自己的版权作品来获得经济上的收益。”[1]版权之所以采取非垄断保护,是为了确保公共利益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如果实行版权的强保护,可能扩大版权人的收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类文化的传播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阻碍了后继的作者创作热情。为此,各国的版权法设计者力求在创作者、出版商和使用者之间维持平衡,如美国法律做出这样的规定:“从作者角度来考虑,原创作品应当被鼓励并获得报酬,但另一方面,私人的创作热情最终应当是服务社会公益,并扩大公众整体的文学、音乐和其他艺术的素养。”[2]相比版权法保护的其他作品,音乐作品除了具备上述的三种受限制的非垄断保护特征外,还具备另外一些特征,如著作权与传播权、听众体验和传播权高度依存等,这些特征导致音乐版权相对于其他版权产品,更加体现在公共性,即作品在公共领域中的广泛传播才能得以认可,从而实现其经济价值。
1.著作权与邻接权高度依存
一部音乐作品创作出来,音乐创作人即拥有著作权,但是如果没有表演者对作品的演绎,这部作品只能停留在纸面的音符上。同样,如果没有音乐发行商的介入,音乐作品也不能得到机械复制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因而,世界各国对音乐作品复制权最重要的限制就是强制性机械许可,机械许可允许被许可方以录音形式复制和发行有版权的音乐作品,无论版权所有者同意与否都可获得机械许可。由此可见,音乐版权涉及到著作权、邻接权这两方面的权利,缺少任何一个权利,音乐版权都无法存在,其中著作权是版权赖以成立的前提,邻接权则是促进版权变现的手段。相比诸如文字、图画等版权作品,音乐作品的邻接权与著作权存在较高的依存度。
作为与著作权“邻接权”相邻的权利,是作品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在国际层面上,这一法律术语特别是指表演者、录音制品制造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邻接”这一表述显示在一定程度上与著作权的紧密联系,但同时又与著作权有所区别,例如,一首歌曲的著作权属于词作者和曲作者,但是歌曲的表演者(歌手、音乐家),录制歌曲的CD的制造者和传播歌曲节目的广播者则享有邻接权,任何人都要尊重他们所作的贡献,即表演、录音和广播。
根据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法律所保护的是著作权的客体——音乐作品,准确地说,是视觉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即乐谱文本。然而,对于听觉艺术的音乐而言,法律意义上的文本作品并不是构成音乐作品的唯一要件,表演者和乐谱创作是音乐作品形成的一体两面。这是因为:首先,“乐谱文本相对于音乐作品而言,如同一个纲要式的草图,是未完成的作品,”[3]其空白点有待于表演者和其他辅助人员完成。音乐作品可谓是创作者和表演者的合谋,甚至有的国家注意到表演者对音乐作品的演绎不像录音人那样是对音乐的机械重构,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将音乐作品的本体性得以呈现,因而将表演权与邻接权中的录音制作者的权利和广播电视组织的权利区别对待,赋予表演者人身权。其次,乐谱文本与音乐作品存在着约定俗成的从属关系,一部作品的全部特点并不能被单一的乐谱文本确定下来,而是可以用多种乐谱记录下来,即同一部作品可用各种乐谱体系记录下来。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音乐语言不像科学语言一样是陈述式的,而是伪陈述式的,将具象和抽象合二为一,因此,不能以具有陈述式特征的乐谱文本取代全部的作品。然而,当前的立法模式未将音乐作品定义为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乐谱,只是顺其自然地将乐谱的创作者赋予音乐作品的作者地位,这显然是没有将音乐作品的创作特性考虑在内,是一种典型的“作者为中心”的权利模式。这种权利模式与现代“读者为中心”的权利模式有悖。对于音乐作品到达对象的听众而言,乐谱是模糊的文本,需要由离听众最近的表演者清晰化地演绎,才能将死的“音符”变成“活”的旋律传达给听众。
2.传播权与听众体验高度依存
对于传播权利人而言,一部音乐作品能否取得理想的经济收益,取决于对听众音乐消费体验的洞察,这是因为:首先,音乐作品有很强的创意性成分,其价值不能用时间来衡量,至少无法靠生产竞争形成,“文化产品交换价值的形成不取决于生产过程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文化生产的形式、条件和手段,取决于外部市场对于某一文化产品的需求程度”。[4]其次,音乐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听众需要借助个体体验才能感觉到创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脉动,但个体感受迥异,不同的听众,即便对于同一个音乐作品,也有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这就是所谓的“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因此,对音乐作品的认识不能采用惯常的因果解释思维来理解作品传达的精神。再次,由于性别、种族、民族、阶层、年龄等方面的不同,消费者有着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者有时会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随时改变自己的消费偏好。
综上,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高度依存、邻接权与听众体验高度依存,最终还是要以音乐作品在听众中的接受度为旨归。换句话说,无论是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还是表演者、出版者,录音制品的制作者、发行者等,要试图从消费者中获取收益,就必须高度重视版权的“公共性”,而公共性的取得的前提是音乐创作人被人知晓,被人认可。在前互联网时代,音乐作品“公共性”的获得大多需要借助诸如春晚、收视率高的影视片等受众面广的渠道。而互联网时代的音乐作品公共性的获得,则需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介入逐步放大,从而为创作者的创作提供确定性的依据。
二、大数据对公共性的挖掘
由于对音乐作品的接受与消费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与非理性,以及音乐作品对新颖性的追求导致市场调查和预测难以见成效。为了防范消费者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唱片公司一般通过两种方法来规避风险:一是“过量生产”,即以少数畅销作品的利润抵消失败作品的亏空;二是格式化、明星效应和促销宣传等营销手法的综合运用,如社会上存在着乐评人、制片人、广告人与作家型记者等文化中间人,其功能就是在音乐创作者与公众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即便传播权利人尽其所能地扩大创作者和音乐作品的知名度,唱片公司仍然很难确保所售卖的音乐产品能满足听众的需求。此外,版权人在努力接近公众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作品被抄袭的风险,因为与传统制造行业不同,音乐作品的制作成本高昂,词曲创作、录制、混音与编曲都需要耗费时间与人力,而“原版”制作出来的复制成本却极低。音乐版权涉及著作权、邻接权中的表演权、制作权、广播权等,权利归属的多元化也影响了音乐作品在市场上交易的安全性。
在大数据技术应用前,上述风险一般由唱片公司、出版社、演出公司等中间商承担和控制,他们通过选题策划、金融运作、市场营销等经营活动增强创作者、公众对他们的依赖程度,通过海量生产获取少数成功产品的超额利润。互联网出现后,音乐版权人将音乐作品放在网上销售,于是他们开始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数字载体代替了磁带、唱片等物质载体,音乐作品的首次销售不再存在。技术手段和反规避规则的介入,使得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由原来的兼顾合理使用变成了刚性保护,即对所有未付费的使用者实施排他性。另一方面,数字音乐作品可以借助技术手段防止未被授权使用,这是一种方便而廉价的方式,可以有效克服以往唱片等实体载体在发行中遇到的“市场失灵”情况。但是数字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在有效避免传统音乐出版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遏制了使用者享用作品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公众,不利于作品的销售。
大数据技术的介入为高度不确定性的音乐产业带来了福音,数字唱片公司DigSin首席执行官杰·弗兰克曾这样评价大数据对音乐产业的贡献:“大数据技术不是要把人的因素抹去,而是最大程度地呈现人的因素——受众的反应。”[5]我们知道,只要上网,每个人都会成为数据的提供者,浏览音乐网页、试听音乐作品、发表评论等等行为都会被智能终端自动记录下来,并上传网络,存储下来。人们的一切所思所想,在网络上都能以数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可以做到:其一,了解音乐消费者的消费爱好和趋势。消费者在音乐平台上收听、收藏和分享音乐的行为,在社交网络、视频网站、各类论坛点赞、转发和评论等动作,均可以视为他们对音乐人的态度,为音乐产品的精准营销提供可靠的数据。其二,依据消费者购买的音乐作品的历史数据,数字音乐出版商可以推荐消费者可能购买的其他音乐作品。其三,可以通过挖掘音乐消费者之前购买行为所产生的大数据,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其四,把握音乐消费的未来发展趋势。国内数据挖掘的翘楚阿里音乐已经开始使用word2vector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与消费者在网上转发和点赞的数据相结合,再通过gbdt分布式算法对音乐作品和未来音乐之星进行预测分析。数据覆盖用户行为数据与社交网络数据、新闻资讯数据等。如果说在5年前这种做法还受制于技术不能实施,那么现如今全球大数据计算性能已比5年前提升了21倍。阿里云MaxCompute只需要377秒就可以完成100TB数据的排序,而在5年前却需要8274秒。[6]
三、大数据背景下公共性再认识
在大数据背景下,作品的流通速度加快,版权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这是我们重新认识音乐版权公共性价值的前提。当然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版权人与被动的音乐消费者互动,后者只消费音乐作品,并不参与到新作品的创作中,然而她们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通过阅听行为获得感官的愉悦,并分享这种愉悦,或者直接转发作品,这种现象引发人们对版权人的关注,从而形成了有利于版权人的口碑效益,换句话说,赋予了版权人一定的社会资本,且这种社会资本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势能”。[7]第二种情形是版权人与积极的消费者的互动,如在2016年浙江卫视播出的第一季《中国新歌声》中,仅导师周杰伦的歌曲就有《双截棍》《双刀》《雨下一整晚》《爱情废柴》《牛仔很忙》等被学员翻唱,有的学员对词曲做了很大的改编,甚至让版权人周杰伦都赞叹不已。这些改编的作品随着《中国新歌声》的热播,不仅放大了原有版权作品的影响力,同时也繁荣了音乐创作环境,有助于音乐接近听众、有助于既有版权作品财产权的实现。
1.有助于音乐创作繁荣
音乐产业进入数字时代后,正版音乐作品如何与盗版作品抗衡,不仅是摆在著作权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更是音乐制作人必须解决的症结之一。笔者认为,正版与盗版的博弈前提是,正版作品出版商必须向消费者提供与盗版商同等质量的服务,即品种丰富、价格低廉,否则消费者会千方百计地从其他非法途径获取音乐作品,从而损害音乐创作繁荣。
大数据技术介入音乐创作和传播中,可以有效协同音乐作品生产中的各个权利主体(见下图),从而在一定程度化解上述难题,有助于音乐创作的繁荣。由私人云和公共云形成的云环境是数字音乐作品的储存层,它连接着制作层和传输层。在制作层中,曲作者、词作者和表演者是音乐作品内容最初的创作者,三者的劳动形成了在场的音乐作品,其中曲作者和词作者的劳动构成了现存立法模式中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表演者、录音者和数据处理者的劳动形成了数字音乐作品,他们取得了邻接权,数字化的音乐作品进入储存层。在此,云服务商要提供存储、搜索、上传、分享和交易的服务。在储存层和传输层连接中,网络运营商需要提供数据接口,将音乐作品传播链条上所有的参与者联系在一起。在传输层中,无论是音乐创作者,还是音乐处理商和提供商,抑或是消费者,通过预装的设备,如MP3播放器、手机、电脑等享受着音乐作品带来的心理愉悦。当然这里的音乐消费者还包括公众媒体和娱乐行业。云计算等大数据可以第一时间把握音乐市场动态,并将市场信息及时传递给词作者和曲作者,使他们的创作与受众期待的距离进一步缩短,有助于实现音乐创作的繁荣。

图1 数字音乐创造传播机制
2.有助于音乐接近听众
国外不乏通过数据挖掘发现音乐市场的案例,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依据音乐雷达软件Shazam提供的数据,在世界4900个城市中找到了拥有相同音乐品味的孪生城市;Shazam能够采集外部歌曲的指纹,并同服务器端指纹比对,实现歌曲识别;无独有偶,美国的House of Blues采用一种独特的算法来安排“拼盘明星巡演”,音乐人则可以结合粉丝位置数据,安排更合理的演唱会巡演路线,以便最广泛地接触忠实歌迷,并能根据当地情况,编排不同的曲目。对于音乐爱好者而言,这种接近意味着提供了普通大众创作音乐作品的机会:他们可以重新编排知名艺人的作品,以混搭和混合为特征的新型作品形式得以出现。如摇滚说唱专辑《灰色专辑》(Grey Album)就是融合《黑色专辑》(Black Album)和《白色专辑》(White Album)而形成的新的音乐作品。
3.有助于财产权的实现
在大数据技术介入音乐生产之前,音乐作品与消费者之间是隔绝的,音乐生产过程中只有作词家、作曲家、表演者、制作人等角色的身影。这种音乐制作过程与大众的疏离正是音乐版权收益不稳定的根源。但是在网络环境下,上述音乐作品的生产者却可以跟大众进行无障碍的沟通,一个个音乐作品的主题可以在交流中制造出来。因为公众参与了音乐选题过程,甚至一些聪明的音乐人在未创作前便对作品实行了众筹,这样的音乐作品在上市前,就确定了市场需求。而在数字消费平台上,音乐供应商提供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点击率以及流量走向,都可以被挖掘到,这也能帮助版权人对音乐市场的需求进行更为准确的判断,从而决定下一步的市场行为。
目前国内几档音乐类电视节目如《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我是歌手》在扩大音乐知名度、快速推进音乐财产权实现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作为在国内观众中美誉度极高的音乐类选秀节目,浙江卫视和湖南卫视两家电视台也都在借力网络放大节目的影响力。如浙江卫视将《中国好声音》和《中国新歌声》播出期间所有的版权作品授权腾讯视频独播,节目原声无损音频在QQ音乐同步首发;湖南卫视则联合爱奇艺全网独播,节目原声无损音频在QQ音乐、酷狗同步首发。为了调动《中国新歌声》听众对音乐作品的深度参与,QQ音乐还推出了“零时差专辑”、“专题榜单”、“达人点评”、“人气金曲大选”、“K歌翻唱大赛”等一系列创新玩法,将平台化的音乐展示过渡到生态化的音乐交互,并充分利用1+N平台优势,使得听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呈几何倍增长。有了关注力资源,便有了创造利润的平台,无论是项目本身还是周边衍生品,都具有了不可估量的高价值。
[1]大卫·J·莫泽.音乐版权[M].权彦敏,曹毅搏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6.
[2]U.S.Supreme Court.Twentieth Century Music Corp[R].V.Aiken,422 U.S.151,156(1975):74-452.
[3]刘文献.未完成的作品:哲学诠释学视野下的音乐作品权利重构[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4(1).
[4]荣跃明.论文化生产的价值形态及其特征[J].社会科学,2009(10).
[5]大数据将音乐行业推入平民时代[EB/OL].http://www.caijing.com.cn/,2016-02-18.
[6]郭雪红.阿里音乐打算用大数据发掘下一个TFboy[N].每日商报,2016-2-16(10).
[7]崔波.数字化背景下版权冲突的动态协调机制研究[J].出版参考,2016(9).
[责任编辑:詹小路]
本文系2016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大数据背景下音乐版权跨界运营研究”(2016N227)的阶段性成果。
薛微,女,讲师,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音乐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D923.41
:A
:1008-6552(2017)04-00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