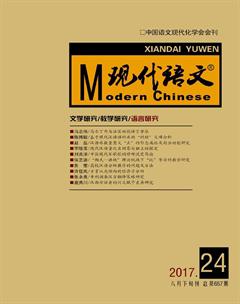语言接触视域下畲语归属问题思考
摘 要:本文通过回顾前人关于畲语归属的研究,反思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运用语言接触理论来探讨这一问题是将研究向前推进的一种有效方法。结合语言接触理论,提出对畲语归属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应考虑几个问题:1.区分不同性质的接触;2.区分不同等级、强度的接触;3.区分由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和由语言内部因素导致的演变。
关键词:畲语 归属 语言接触
20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及“谱系树”理论在国内语言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一些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中华民族经历数次大的变迁,社会更革、王朝更替,带来多次移民迁徙,民族融合与接触十分频繁。这些都使得历史比较法有时很难执行,在鉴别同源还是深度接触带来的严整对应上也遇到了难题。因此,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作为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的现象,从横向观察语言之间的关系,从语言接触角度探索彼此的相互影响的方法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汉语及民族语研究领域,该理论不仅用来研究方言亲属关系,也用来探索由于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
关于畲族的族源与畲话的归属,历来是民族学界和语言学界的两大难题。诸多学者曾就这个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但目前学界仍未达成共识,且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本文将从语言接触这一视域出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指出问题的症结,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一、前人关于畲语归属的讨论
关于畲族所使用的语言的性质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始,到目前为止,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有民族学和语言学者的共同参与,有历史、文化、语言的多种角度,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也有分歧巨大,甚至相反的观点。关于各家的具体论证,在此不一一列举。关于畲语归属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少数民族语言层面的讨论:一是汉民族语言层面的讨论。由于现代畲语分布区域不同,通常将畲语分为两大区域来讨论:一是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畲语,仅占整个畲族人口的1%,二是其他地区占畲族人口百分之99%的畲族使用的语言。
具体而言,少数民族语言层面的讨论涉及早期畲语性质和现代畲语是否是畲族民族的语言。例如,罗美珍(1980)认为1%人口使用的畲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1](P39)毛宗武、蒙朝吉(1986)认为是与苗瑶语族中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接近。[2](P5)陈其光(1984)则认为与苗瑶语族中粤北盘瑶的勉语接近。[3](P204)游文良(1995)的观点是:更接近瑶族语言,而非畲族原生型语言。另外,游先生还认为,现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畲民说的就是畲族的民族语言。[4](P13-122)
在汉民族语言层面的讨论也十分热烈。可分为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客家方言
罗美珍(2013)认为,“自称‘山客和‘畲的畲族所说的语言,从现今发表的论著来看,其语言的主体结构(包括语音结构和演变特征、常用词、基本词、特征词以及语法特点)大多和客家话接近。但属于客家话或其他汉语方言的特点并不多见。如果将这些语言称‘某地畲话,就容易让人误解为是一种独立于汉语方言的体系。”[5](P1)罗先生倾向于称它们为“某地畲族山客话”。
(二)区别于客家话的特殊汉语方言
有的学者认为畲语是一种汉语方言,但不是客家方言。赵则玲(2004)认为,“畲话是一种比客家方言古老、超地域分布、与客家话关系密切、历史层次复杂的,具有汉语特性的畲族人所说的话。”“它们(畲话与客家方言)是不同民族所说的两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两者同属于汉语语系:一种是‘汉语客家方言;另一种暂且称之为‘汉语畲方言,是汉语语系中的两个并列的方言。”[6](P93)
(三)混合型方言
傅根清(2003)认为:“从畲话的发展历史与语言事实看,畲话与客家话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畲话是一种古老的、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以族群分布的、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方言。”[7](P72)至于所说的“方言”是否属于汉语方言的一种,是否像赵则玲认为的要将它与其他汉语方言并列对待,傅文没有明确指明。
游文良(2002)在《畲族语言》一书中认为:“现在畲族所使用的语言是由古畲语成分、汉语客家方言成分和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成分三结合的一种混合型的语言,不应把它看作是汉语客家方言或‘基本上属于汉语客家方言。”游先生称之为“现代畲语”,认为99%以上的畲族人所讲的畲语就是畲族的民族语言,而不叫作“畲族所说的客家话”。[8](P520-523)
语言定性和划分归属问题属于语言科学范畴,只能根据语言事实说话,而不能因为一些畲族人出于对本民族热爱的情感,难以接受自己的语言属于客家话,又根据自己的语言与当地或临近的汉语方言无法直接交流,从而认为自己有独立的语言。为什么面对基本相同的语言事实(即使对同一个地区同一种畲语),而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对语言材料的立场、分析的方法、角度等各方面的不同,都将导致结论的不同。
二、目前畲语归属上的讨论存在的问题
(一)语言层次的复杂性和多源性不是鉴别语言系属的绝对根据
现代畲语中有多种来源成分的叠加,这是学界基本一致的观点。游文良(2002)將之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成分:古畲语的底层成分、汉语客家方言的中层成分、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8](P25)其中,关于古畲语底层的语言性质,到底是苗瑶语族中的哪一支,各家有不同意见。至于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从民族迁徙的历史看,现代畲族居住地最多的闽、浙、赣(以闽东为最多)地区的畲民主要是明清迁入的,由于年代不是太久远,接触不够深,其语言的表层成分比较容易辨别。所以,从现代畲语中,往往可以看到闽语、吴语或粤语的一些特点。
有些学者不主张将畲话归属于客家方言的一个原因是畲话的语言层次复杂,其方言成分不单纯是客家话,还有闽、粤、赣、吴语等方言成分。我们认为这一理由较难让人信服。因为语言层次的复杂性和多源性不能作为鉴别语言系属的绝对证据。endprint
汉语诸方言在其形成历史上都是多源融合的。在一些语言接触频繁的地区,语言之间的影响不可避免,因而产生了一些相似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能否作为鉴别语言系属的证据,关键要看这些“成分”占这种语言的比例,以及各种“成分”的实质,是语音系统中的音素还是音位,与词汇层面的语素有何关系,在语法层面是组合关系还是聚合关系的改变,这些“成份”占基本语素、核心语素的比例。
所以,将现代畲语与民族语和汉语方言相对照,找出其中的异同,看出畲语的复杂性和层次的多源性,是符合语言事实的,也是符合畲族发展历史的。然而,由此而直接得出它是一种混合型方言,或者是一种与其他汉语言并列的特殊的方言,又或者是独立的一种民族语言,其结论和论据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底层遗留和使用族群不是将畲语分立出来的有效证据
有些学者强调畲语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它有来源于非汉语的底层,且使用的人群是与汉语方言不同的少数民族。然而,考古、历史的研究都说明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源性。语言中的底层遗留也体现出它们历史上与中原文明的不同。例如,东南沿海汉语方言中存在状语后置、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后、独特的地名、核心词、封闭类词等诸多底层现象。我们在对汉语方言进行划分时,主要是根据它们与汉语史各阶段的特点的不同,从语言同源分化的角度进行分区,而不是根据底层遗留或语言使用族群来分类。即使拥有相同底层遗留的方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可能变成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而不同的族群可能说相同的语言(例如,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已放弃自己的语言,改说一种汉语方言),相同的族群也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或方言。
至于畲族是否在历史上由于与客家人深接触而最终放弃畲语,改用客家话,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不能因为古畲语还保存一些“底层”,就完全否定这一观点。因为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完成了母语转换,而仍存留“底层”成分。也就是说,底层遗留与母语转换不矛盾。
(三)语言相似度也不宜作为畲语区别于客家话的有效证据
有些学者在对比畲语与客家话时,认为语音上二者相似度较低,而各地畲语基本能通话。因此将通懂度作为区别语言或方言差异的经验性标准。我们认为,首先,语音上是否相似不能以音值的相似为称量标准,要看语音特征(从目前的调查报告看,与客家方言的语音特征有诸多相似)。其次,“听懂”虽然是一条经验性标准,有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与被试的文化程度、生活经验等诸多因素有关(有时被试对音值差异的敏感度往往高于音类),带一定的主观性。再如,闽语内部差异极大,闽东、闽南、闽北和闽中地区说闽语的人彼此无法交流,但不宜把它们视为不同系属的方言。
(四)语言比较过于简单、缺乏标准
如上所述,畲语中有多种成分,将它与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自然成为被广泛运用的方法,诸如畲语与客家话、闽语、吴语、粤语等等的比较。认为畲语属于客家方言的说法比较流行,将畲语与客家方言进行比较自然也是最多的。同样进行比较的学者,得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部分认为是客家方言,一部分却认为不是客家方言。这说明语言比较不能只进行表面的、简单的比较。
例如,以古全浊声母的今读表现看。景宁畲话中的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逢今单音、塞擦音,比较均衡地分化为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两类,找不出分化的条件。而客家话通常表现为中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逢今塞音、塞擦音,今读送气清音。如果单从送气与否的类型及收字数量看,景宁畲语与客家话比畲语与闽语差异度更大(闽语不送气音多于送气音)。我们认为,这样的语言比较相对来说过于简单。该问题其实还有几点因素需要考虑:首先,要分析畲语的不送气是否是受闽语影响的结果。其次,闽语内部在古全浊声母的今读上也存在差异。例如,闽北有些方言有浊声母。无法笼统地说畲语与闽语的语音特征接近。最后,闽语的文白异读复杂,送气与否还需考虑层次问题。畲语与闽语的这种表层相似是晚近语言接触的结果还是早期语言层次的对应。又如,傅根清(2002)比较粤语和景宁畲话语音系统的一些特点,认为浙江景宁畲话还保留一些畲族发祥地粤语相似的语音特点。比如,广州话的韵母特点之一是没有普通话中常见的“?”类韵母,也没有舌尖元音“?、?”和卷舌韵母“?r”。景宁畬话有舌尖元音?,但也没有舌尖元音?和卷舌韵母“?r”。[9](P118-122)由此将二者看作是共性,以此来证明其源流关系有待商榷。没有舌尖元音“?”和卷舌韵母“?r”是很多汉语方言的共性,与其说景宁畲话的韵母特点与粤语有共性,不如说与客家话共性更大,因为很多客家话有舌尖元音“?”。可见,该文的比较方法略显表面、武断。
三、语言接触视域下畲语归属问题的重新思考
畲语的性质究竟如何,存在诸多分歧,至今仍无定论。但畲语是在语言接触的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目前学界的共识。因而,运用语言接触理论来探讨这一问题,是将研究向前推进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一)区分不同性质的接触
瞿霭堂对语言接触的定义:“一种是指存在于一个人头脑中的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是指结构层面上的接触,即语言内部的接触;另一种是指一个人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这是指应用层面上的接触,即语言外部的接触。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接触:前者涉及语言思维,后者则关系到语言态度。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接触,都会对接触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的性质不同:内部接触产生结构上的影响,比如成分或手段的借用或渗透,甚至规则的改变,系统和结构的变化,直到两种语言混合产生一种新的语言;外部接触产生应用上的影响,比如产生语言兼通现象,即双语或多语现象,语言兼用和换用现象,即一部分人或全社会成员放弃使用自己获得的语言而使用另一种习得的语言。”[10](P58-59)
长期而深入的语言接触和影响,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种是两种语言单向或互向同化,形成一个语言区域。母语虽保留下来,但变成另一种类型的语言,系统中包括两种语言。另一种结果是语言使用者完全转用目的语,母语消失。endprint
因此,在分析畲客方言关系时,要区分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语言接触问题。
语言长期接触会形成语言混合现象,即甲语言与乙语言的接触,形成既非(是)甲又非(是)乙甚至又非(是)丙的语言结构。这种中介语并不是一个种类,而是一个集合,是一系列不同的变体。混合语是语言接触最深、相互影响最大而产生的一种深层变异,往往产生在民族杂居区域和语言走廊地带。一般认为,当某种语言的组成成分来自几种不同的语言,且这些成分都是基本的,占相当大比重的,这样的语言就已经成为混合语了(目前国内认可的混合语有四川的雅江倒话、青海的五屯语,云南的卡卓语、新疆的艾努语、海南的回辉话。)。畲语与客家话在接触过程中是否产生了一种新的、非(是)畲非(是)客甚至又非(是)畲客方言的第三种语言,即混合语,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语言转用是由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根据我国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几种:“民转汉”(从少数民族语转用汉语)、“民转民”(一种数民族语转用另一少数民族语)、“汉转民”(从汉族转用少数民族语)、“汉转汉”(从一种汉语方言转用另一种汉语方言)。也就是说,畲族先民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完全改用客家方言(也有人认为是客家人放弃自己母语而用畲语)。语言转用不是语言的绝对挪用。使用目的语时或多或少地带有母语的一些特点,产生不同程度的语言变异。学界
(二)区分不同等级、强度的接触
学界对于语言接触是无界还是有界这一问题有过较多的讨论。以鲍阿斯(F.Boas)、梅耶(A.Meillet)、萨丕尔(E.Sapir)、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雅各布逊(A.Jakobson)、马丁内(A.Martinet)、魏茵莱希(U.Weinreich)为代表的一些语言学家着眼于语言内部结构来讨论语言接触,认为语言的形态部分和音系部分不会受接触的影响,即接触是有界的(参见彭嬿,2007)。[11](P140-143)但后来一些语言学家对历史比较法中的同构对应确定同源关系的原则提出质疑,提出同构和语音对应关系也可能是语言联盟或语言接触的结果,语言影响不仅有词汇的借用,也可能造成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渗透,即接触是无界的。
吴福祥(2007)根据托马森的理论,概括出比较全面的借用和接触等级。其中,接触等级分为:偶然接触、强度不高的接触、强度较高的接触、高强度的接触。[12](P7-8)这四种接触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借用成分的种类层次。不过,托马森主要强调社会因素决定接触程度的深浅。
陈保亚(1996)提出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观点。两种语言在接触中有规则地相互协调、趋向同构,形成有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这一相互协调的过程呈现出无界有阶的特点。接触可以深入到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深入的“度”由接触时间、双语方向、双语人口等社会因素决定,而“度”的演进是有阶的。“阶”是由结构因素决定的。社会因素决定了接触的深度,决定了干扰和借贷的方向;结构因素决定了同构和对应的产生。[13](P141-153)
也就是说,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既有轻度的或表层的,也有重度或深层的。语言接触的程度与语言影响成正比,浅层次的语言接触,多表现为词汇(包括词汇词和语法词的借用),深层次的语言接触会影响到语音和语法。虽然接触具有普遍性,但各个层面接触的深浅是不同的,是不平衡的。
在研究畲语性质的过程中,无论是早期古畲语与汉语的关系,还是畲语与客家话的关系,以及畲语与现代居住地的汉语方言的关系,在谈及接触时,或引史料印证,或只是简单的语言比较,没有将语言间接触的深浅程度解释清楚,未能将借用成分的种类和层次阐明。
(三)区分由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和由语言内部因素导致的演变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几种语言同时使用时,可能发生借用、代用、混用、交叉、错位等现象,也可能产生两种语言要素交融的新变化。这些不是由语言内部发展引起的,而是由于语言接触造成的。
吴福祥(2007)基于托马森的研究框架,讨论了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相关问题。在如何区分“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和“接触引发的演变”上,吴先生指出:这两类演变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演变的过程和后果)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演变的触发因素不同:前者的触发因素是某个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压力;后者触发因素是另一语言的影响。[12](P17-18)
因此,在分析现代畲语中不同于客、闽、吴、粤各方言的方面时,主要要确定触发因素是该语言内部的结构压力,还是其他语言的外部影响。从而判定其演变因素是“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还是“接触引发的演变”。
四、结语
近些年来,语言接触成为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共同关注的对象。畲语归属是个复杂的、跨学科的问题。前人已从多角度做了诸多研究。语言接触包括方言接触和不同系属语言的接触。畲语归属问題同时涉及这两个方面。“谱系树模式的分化和联盟树模式的接触语语源关系的两个方面,但分化的机制不容易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到,而接触可以通过双语现象从微观的角度进行观察。”[13](P293)我们相信,语言接触理论将在未来的畲语研究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闽东方言的语音特征及其历史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5CYY012]。)
参考文献:
[1]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1).
[2]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3]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J].语言研究,1984,(1).
[4]游文良.论畲语[A].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畲族历史与文化[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5]罗美珍.关于畲族所说语言的定性和命名问题的思考[J].龙岩学院,2013,(2).
[6]赵则玲.试论畲话的归属[J].语言科学,2004,(5).
[7]傅根清.从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论其与客家话的关系[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8]游文良.畲族语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9]傅根清.景宁畲话语音系统中的粤语成分[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10]瞿霭堂.语言思维和语言接触[A].邹嘉彥,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彭嬿.语言接触研究述评[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12]吴福祥.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J].民族语文,2007,(2).
[13]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袁碧霞 福建泉州 华侨大学文学院 3620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