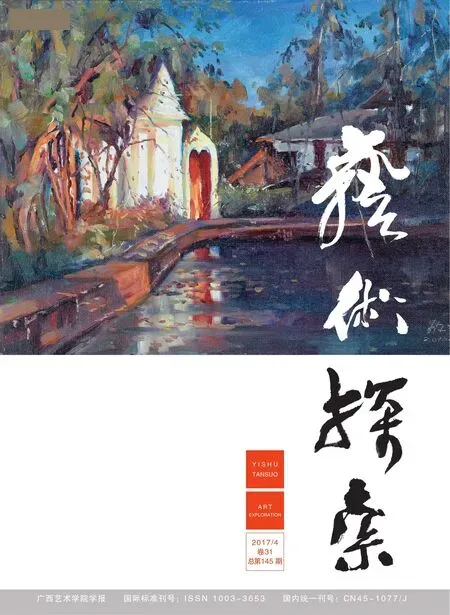“重塑现代”的政治合法性及其艺术悖论
——论“十七年”电影中的现代文学改编
穆海亮(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重塑现代”的政治合法性及其艺术悖论
——论“十七年”电影中的现代文学改编
穆海亮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十七年”电影对现代文学的改编,是一种“重塑现代”的话语行为,政治合法性是其中凌驾于一切艺术因素之上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本位和以“新”塑“旧”是“重塑现代”的合法性基础,强化阶级立场和新旧对比是“重塑现代”的合法性策略。然而,这样意图明确、主动迎合的改编策略,终究不具备将“现代”与“当代”之间的意识形态沟壑彻底填平的作用力,且往往导致艺术的扭曲或自我阉割。影片由此遭到的境遇错位和意义减值,就呈现出显而易见的艺术悖论。
“十七年”电影;现代文学改编;重塑现代;政治合法性;艺术悖论
改编文学作品是十分常见的电影创作方式,“十七年”时期也不例外。根据《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电影集》的统计,“十七年”时期的400多部故事片(不包括戏曲片)中,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就有120余部,所占比例不可谓不大。不过,这些改编影片的原作大多是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红旗谱》《李双双》等。而改编自1949年之前现代文学作品的影片,则数量很少,并且大约一半都是改编自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包括话剧、歌剧等),如《白毛女》《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抓壮丁》《小二黑结婚》等影片。实际上,这些影片的文学原作尽管在时间上属于“现代”,但其创作立场、审美特点诸方面,都可视为“十七年”文学的先声。除此之外,真正算是根据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仅有《我这一辈子》(老舍原作,杨柳青编剧,石挥导演,文华影业公司,1950年)、《腐蚀》(茅盾原作,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文华影业公司,1950年)、《家》(巴金原作,陈西禾编剧,陈西禾、叶明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祝福》(鲁迅原作,夏衍改编,桑弧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56年)、《林家铺子》(茅盾原作,夏衍改编,水华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早春二月》(柔石原作,谢铁骊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1 9 6 3年)等几部。①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界也出现了一批根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根据巴金原作改编的《秋》(秦剑导演,香港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1954年)、《寒夜》(李晨风导演,香港华联电影企业公司,1955年)、《故园春梦》(夏衍编剧,朱石麟导演,香港凤凰影业公司,1964年)等。由于香港电影的生产体制、意识形态、文化属性等与内地截然不同,因此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有意思的是,这屈指可数的几部现代名著改编影片,几乎都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代表着“十七年”电影的艺术水准。
既然在“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改编电影的成功率这么高,那么此类影片为何如此之少呢?这类影片采取了哪些改编策略以满足特定的时代要求?其改编又体现出什么样的时代特点,折射出什么样的艺术悖论呢?
一、政治本位与以“新”塑“旧”:“重塑现代”的合法性基础
“十七年”时期,所有的文艺样式无一例外地受到政治形势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深刻影响,文艺创作风云变幻,对以往文艺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也随之不断地发生变化。1949年之后与之前的两个时代,被人为地区分出“新”“旧”:以“新”自居者自然带着道德和政治的优越感去审视过去之“旧”,而跨越两个时代的一大批亲历者必须弥合这巨大的断裂,通过或真诚或故作姿态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而获得新生的机会。因此,当“当代”艺术家试图以电影形式重新呈现1949年之前的现代文学作品时,就不单单涉及电影创作的问题,同时也是在对现代的重述中,彰显着自身的当代立场。这也就决定了“十七年”电影人必须对现代做出小心翼翼的选择和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电影对现代文学的改编,其实是一种“重塑现代”的话语行为,以“新”塑“旧”,就成为这种重塑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而这种合法性首要的必然是政治合法性,这是由“十七年”电影的政治文化属性决定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电影的生产体制、文化属性、审美功能、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电影承担着重新阐释历史、描绘现实、憧憬未来,并以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大众思想认知的重要使命。因而,“十七年”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宣传部门对电影极端重视,首先是看重电影可能发挥的政治功能。艺术家的电影创作,显而易见地受到政治运动与观念的深刻影响。“新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是新中国政治的组成部分,它在为中国百姓提供意识形态想象的同时,也为中国主流政治塑造审美形象。”[1]1于是,在“十七年”时期,选择将哪些现代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以及如何进行改编,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艺术问题,尤其是当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席卷整个电影界的时候。从1951年对《武训传》以及《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的批判,到1964年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1965年对《林家铺子》《不夜城》的公开放映批判,政治的腥风血雨始终令电影人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境下,政治合法性就成为凌驾于一切艺术因素之上的决定性因素。
“十七年”电影对现代文学的重塑有着太多的禁忌和暗区,可选取的对象其实并不广泛,所选题材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处理以体现“新”时代的精神。电影人自然会优先考虑立场更“正确”、政治上更“安全”的题材。“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小心翼翼地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规约,迎合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要求;而解放区文学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靠拢,所以在电影人眼中,改编这些作品可能政治风险更少,此类作品也就数量更多——当然,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即使改编此类作品也同样面临风险。至于改编现代文学名著,就更需倍加小心了。电影人最终选择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的作品,不仅由于他们是公认的文学大师,更重要的是他们作品的思想主题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至于柔石《二月》被改编,自然是因为作者的中共党员、“左联”烈士的身份,以及鲁迅作序赋予该小说的“护身符”。关于这一点,当时的电影人是坦白承认的。夏衍堪称“十七年”文学名著改编电影领域的杰出代表,他将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搬上了银幕。20世纪50年代初期夏衍推荐拍摄的《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之后,他在电影题材选择上变得极为谨慎:“对这件事,我也得到了一点教训,我懂得了有些题材可以写小说,但不是小说都可以改编电影。理由很简单,领导上不一定看小说,而拍成电影,那就逃不过领导的关注了。因此,1955年我调到文化部分管电影之后,包括我自己改编的电影,都是鲁迅、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的作品,这就比较保险了。”[2]442“十七年”电影人的改编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在“十七年”时期,只有题材“保险”显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原作进行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改造,以弥补“现代”与“当代”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落差。而改造的主要方向,就是使现代文学作品更加符合“十七年”意识形态的要求,从而表明改编者政治立场的坚定。为此,“十七年”电影在改编现代文学名著时,采取了或多或少有其合理性,但更多是出于无奈的改造策略。
二、阶级立场与新旧对比:“重塑现代”的合法性策略
首先,自觉地强化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意识,凸显受压迫阶级的反抗精神。茅盾在其小说《林家铺子》中表现20世纪30年代南方乡镇的破败、萧条及社会众生相时,尽管已试图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但小说同时呈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真实、客观的艺术风格,对主人公林老板的破产和妻离子散寄予了深切同情。这在小说发表的1932年不是问题,但在改编为电影的1959年就成了问题,因为林老板这样的小商人、资本家已经被列入“剥削阶级”。因此,在征得茅盾同意后,夏衍的改编就必须对林老板做出新的阶级分析,凸显其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是一个中小资本家,本质上是剥削阶级,一方面在他上面有欺侮他的更大的剥削者、压迫者,他随时有受剥削、受压迫的可能;可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是个‘老板’,所以他也决不放弃剥削和压迫比他更弱小的弱小者的机会”,“见着豺狼,他是绵羊;见着绵羊,他是野狗”。[3]5为此,夏衍和导演水华特别增加了林老板在走投无路时抢夺王老板存货的情节(王老板已经破产,妻子卧病在床,孩子哭声一片),并把林老板应付朱三太和张寡妇的手段表现得更加狡猾和残忍。林老板逃跑、林家铺子倒闭后,影片还安排于会长等人就盘点林家余货发生争执,以表现“大鱼吃小鱼”的场面。此时影片配了一段旁白:“林源记垮了,林老板带着女儿走了,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受到更大的打击,遇到更重的苦难的,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批压在更下层、更穷苦的人。”铺外拥挤的人群中,哭天喊地的朱三太和张寡妇就是被压在最底层的可怜人。影片《早春二月》特意增设了原著小说《二月》所没有的因贫困而辍学的王福生一角,并增加了全班同学因受镇上恶势力的蒙骗而集体旷课的情节,也是出于同样的阶级分析思维。
影片《祝福》对祥林嫂与贺老六的关系及命运的改写,同样遵循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路。鲁迅原著中贺老六并未出场,也未直接表现祥林嫂与贺老六相处的场面,只是借卫老婆子之口告诉读者,贺老六“有的是力气,会做活”,还暗示贺老六曾以强力占有祥林嫂,后来得伤寒去世了。而在“十七年”的语境中,贺老六作为一个穷苦农民,理应属于被压迫阶级,对祥林嫂应有阶级同情,而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只能是剥削阶级。因而影片就把贺老六塑造成勤劳、本分、善良的农民,祥林嫂与他过着虽贫穷却幸福的生活。原著中祥林嫂的小叔子是强卖她的帮凶,影片改为他暗中帮助祥林嫂逃脱,因为青年农民同样应是正面形象。在此基础上,影片增加了地主七老爷和师爷两个角色,是他们的残酷剥削生生害得贺老六受伤、病重,他们又赶来抢夺贺老六的房子,逼死贺老六,也间接害得阿毛被狼吃掉。这样的情节安排显然就使狼吃人和地主逼债形成一个微妙的同构关系。面对地主逼债、抢房、害人的举动,贺老六以命相搏,这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与阶级斗争的强化密切相关的,就是凸显被压迫群众的反抗斗争。影片《祝福》最为引人关注的改编,是祥林嫂用辛辛苦苦攒了一年多的工钱去庙里捐了门槛之后,在别人眼中仍然是罪孽深重的不洁之人,这让她的情绪彻底爆发了,跑去庙里砍掉了门槛。砍门槛的行为在当时得到了不少赞誉,被认为符合祥林嫂的性格发展规律。[4]49夏衍自己也解释说:“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是一个反抗性颇为鲜明的人物”,“祥林嫂有决心用死来反抗现实的吃人社会的迫害,就是这个祥林嫂,难道永远会是神权下面的不抵抗的奴隶么”。[5]13话虽如此,其背后仍然是时代所需要的阶级意识在发挥作用。在压迫越大、反抗就越大的阶级社会,祥林嫂砍门槛就被视为受压迫人民觉醒之后的反抗,这样的召唤对普通电影观众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在“十七年”的语境中,电影改编必须坚持坚定而明确的阶级立场,容不得半点含糊,否则就有可能像根据茅盾原作改编的《腐蚀》那样,由于片中的女特务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憎恨,反而激起些许同情,而难逃被禁的命运。
其次,通过强化新旧对比,凸显新时代的优越感,尤其是针对原作可能流露的低沉悲观情绪,增加影片的亮色。当影片通过回望旧时代以讴歌新时代时,一个简单易行的方式就是将过去定义为黑暗的渊薮,并通过拉开时间差来告诉观众,片中的罪恶只属于过去,今天我们已经永远告别这样的黑暗和罪恶了。为了让观众更顺畅、更简捷地理解这一点,不少影片都使用了旁白。《林家铺子》一开始就用画外音设计了这样一段旁白:“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一年,离开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这是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剥削阶级工商业者,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作家描写了一幕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景。”《祝福》开始时的旁白异曲同工:“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大约四十多年以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山村里。”影片结尾祥林嫂在大雪纷飞的晚上冻饿而死的画面,也配上一段旁白:“祥林嫂,这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了,死了。”即便如此,仍怕观众沉浸在悲伤之中,于是旁白紧接着就说:“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此时配乐的风格由此前的悲怆凄凉转向了昂扬向上。夏衍甚至还为《林家铺子》设想过这样一个开头:“公私合营后,在一个工商业改造的讨论会上,一个小老板(寿生)回忆过去,叙述旧社会大鱼吃小鱼的故事,然后用倒叙的手法转入本题。”[6]3尽管这样的设想终究由于是“多余”的“旧套子”而被放弃,可其中所折射出的创作意图,显然是为了更清晰地彰显新旧对比。
影片《我这一辈子》的改编,不仅拉长原作的时间跨度,从清末写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更重要的是,影片增加了原著所没有的人物申远,从进步学生发展成为英勇的共产党员,时时鼓舞着“我”和儿子海福,甚至在狱中为“我”指明方向。结尾处“我”虽然死了,但伴随着激昂的《解放军进行曲》,“我”的儿子海福威武地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下,满脸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即便如此,导演石挥仍然担心影片不够“光明”。其实他最初设计的结尾是:北京解放了,解放军进城,海福行进在队伍中,父子拥抱,跟着队伍前进。但是,要一个私营电影厂发动很多人去拍“入城”实在无法实现,所以只得忍痛割爱,让“我”死去。[7]谢铁骊编导的《早春二月》,弱化了原作《二月》过于消极低沉的情绪,将原作肖涧秋弹奏的《青春不再来》改为《徘徊曲》,增加了肖涧秋与陶岚阅读《新青年》杂志的场面。原著结尾,肖涧秋陷入矛盾的漩涡,最终被迫逃离芙蓉镇;影片则改为经历过挫折之后,肖涧秋有所醒悟,决心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格调更加昂扬。
三、境遇错位与意义减值:“重塑现代”的艺术悖论
阶级立场的强化和以旧衬新的改编,尽管使现代文学获得了在“十七年”电影中呈现的合法性,然而这千方百计去迎合政治需要的改编策略,往往导致艺术的扭曲或自我阉割;更有甚者,即便电影人已尽力迎合意识形态的感召,这些策略也终究不具备将“现代”与“当代”之间的意识形态沟壑彻底填平的作用力。上述根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除了《祝福》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之外,无一例外地遭到批判或禁映,终究难逃政治打击的悲剧。因此,这样的改编立场与策略所造成的艺术悖论同样引人深思。
就影片的现实境遇来看,即便电影人已竭尽所能地对原著进行了改造,但在政治本位的“十七年”语境中,仍然经常被批评改造不够彻底,甚至适得其反,改编初衷与现实境遇之间形成明显错位,由此给影片招致尖锐批判乃至政治厄运。以《林家铺子》为例,尽管改编者已经特意增加了林老板压榨下层民众的场面,来体现资产阶级的罪恶,却仍被视为“美化资产阶级”:“影片《林家铺子》不但没有正确地反映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正确地表现当时正在上升的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没有表现出当时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和斗争,而把劳动人民描写成消极愚昧、听天由命、任人摆布的人物。”[8]迎合性的改造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成为“欲加之罪”。《早春二月》尚未公映就被判了死刑,对它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谢铁骊试图增强革命气息和政治亮色,但这样的改动反而被认为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故意拔高,不如原作表现他们“从失败到失败”;原作的三角恋爱是要揭露资产阶级的精神堕落,而影片将其纯洁化,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9]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谢铁骊之所以敢冒险改编《二月》,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曾为之作序——为小说上了一道“保险”。而在那些批判者看来,鲁迅作序就是要批判肖涧秋这样的人,[10]所以,电影对肖涧秋的拔高就是对鲁迅的否定。面对这样的批判,电影人真是左右为难了。
就影片的思想传达和艺术表现而言,在经过了意图明确、主动迎合的改编之后,原作思想的丰富性、多义性、深刻性往往遭到简单化的处理。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祝福》了。影片竭力表现祥林嫂所处时代和社会的黑暗,刻意强化鲁四老爷等旧势力的恶行,并温情脉脉地展现贺老六与祥林嫂的幸福生活,更隐去了原著小说中“我”的叙事视角。这样一来,就单单将原著表层的社会批判强调到极致,而夫权、族权、神权对女性命运的戕害被弱化了,鲁迅更看重的对人性愚昧的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软弱与灵魂自省,也遭到了有意无意的遮蔽。可以说,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意义减值,审美格调也发生了某些偏移。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形,《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影片都有类似的艺术扭曲或自我阉割。这种情形的形成,从历史的维度看,自然是由政治语境的规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所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所蕴含的从艺术技法到美学规则的固有规律。
从艺术技法的维度看,这是电影人意识到小说与电影的差异,进而在实现艺术形式迁移时采取的策略。在改编《祝福》时,夏衍针对小说与电影的受众群体与传播方式的不同,明确提出“通俗化”的原则:“由于原作小说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而电影观众却是更广泛的劳动群众……为了使没有读过原作以及对鲁迅先生的作品及作品中所写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情风俗等等缺乏了解的观众易于接受,还得做一些通俗化的工作。”[5]12在他后来改编《林家铺子》和参与改编《早春二月》时,“通俗化”原则都是一以贯之的。如取消《祝福》原著第一人称“我”的主观叙事,改为客观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给《祝福》《林家铺子》加上“画外音”以揭示主题等等,都是“通俗化”的举措,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意义减值的客观原因。
从美学规则的维度来看,现代文学在“十七年”电影中的呈现是文学图像化的过程,而意义减值也正是文学图像化的必然结果。赵宪章对此做过透彻的分析:
所谓“文学图像化”并非图像对于语言艺术的简单对译。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对语言的模仿只限于筛选之后的“语言残留”,但却丢弃或置换了图像之不能或不宜的世界,从而导致原作的虚化;另一方面,图像也可以作为语言的替身,在语言不可名处为世界重新命名,将“惚兮恍兮”的世界以图绘的方式定型,从而进一步虚化了文学的世界。图像对于文学的这种“双重虚化”使文学所承载的事理变得轻薄了,同时也减轻了“图以载文”的负重。“图以载文”对于文之事理的“减负”必然加速它的传播速度,使观看被图像化过了的“文学”无需很长的时间,也无需阅读过程所必需的凝神静思、反复回味和深度理解。可见,以“轻装”换取游走的速度是“图以载文”的主要表征,卸载文之事理是文学获取图像传播力之必需的选项,可谓“图以载文文自轻”。这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文学图像化规律。[11]32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学作品以图像方式呈现时,都或多或少地因为“减负”的需要而发生思想与艺术的变化。因而,“十七年”电影在改编现代文学名著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著的意蕴与格调,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1]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2]夏衍.懒寻旧梦录[M].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夏衍.漫谈改编[J].电影创作,1960(2).
[4]章抒.《祝福》学习札记[J].电影创作,1959(6).
[5]夏衍.杂谈改编[J].中国电影,1958(1).
[6]夏衍.对改编问题答客问——在改编训练班的讲话[J].电影剧作,1963(6).
[7]石挥,口述.石邦书,叶明,记录整理.只得让“我”死的原因[N].大公报,1950-02-26(7).
[8]苏南沅.《林家铺子》是一部美化资产阶级的影片[N].人民日报,1965-05-29(7).
[9]景文师.《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N].人民日报,1964-09-15(7).
[10]丁景唐.鲁迅是怎样评价《二月》的[N].人民日报,1964-09-17(7).
[11]赵宪章.语图传播的可名与可悦——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文艺研究,2012(11).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黄宗贤/泊/布上油画/95cm×115cm/2016年
黄宗贤,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美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高校美术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教育学会理事长。
长期从事艺术史、艺术学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同时致力于艺术创作。在学术研究上取得较为丰厚的成果,多次承担全国艺术科学及省部级艺术研究课题,出版的重要著作有《佛陀世界》《大忧患时代的抉择——大后方美术研究》《抗日战争美术图史》《中西雕塑艺术比较研究》《艺术批评》《陪都画坛辑佚》《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原理》等,在《文艺研究》《美术》《美术观察》《美术研究》等刊物发表美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等方面学术论文上百篇。在艺术创作上力求心与景、意与境的契合,作品充溢着内敛与激情的张力和写意的韵味。多次参加重要的学术性展览,作品多有被艺术机构或画廊收藏。
OnModern LiteratureAdaptation in the"Seventeen-years"ChineseFilmsin the PerspectiveofPoliticalCorrectnessand Paradoxof"ReshapingModern Times"
MuHailiang
Themodern literature adap tation in the"seventeen-years"Chinese films is a d iscourse actaim ing at"reshap ing the modern times",in which politicalcorrectness is the decisive factorofoverriding significance overany artistic elements.The politicalends therein and the c laimed innovation serve as the basis ofpoliticalcorrectness while em phasis on c lass stance and contrastof"the past"and"the p resent"is the strategy in"reshaping themodern times".However,the adap tation w ith the articulate politicalintention to p laying up more often than notresulted in the d istortion ofartistic ends.Therefore,the Chinese film shad been sub tracted in significance and considered as a case ofartistic paradox.
"Seventeen-years"Chinese Films,Modern Literature Adap tation,Reshap ing Modern Times,Artistic Paradox
J905%
A
1003-3653(2017)04-0123-06
10.13574/j.cnki.artsexp.2017.04.015
2017-04-22
穆海亮(1980~),男,河南濮阳人,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戏剧、电影。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
——祥林嫂的悲剧原因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