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生命意识略谈
田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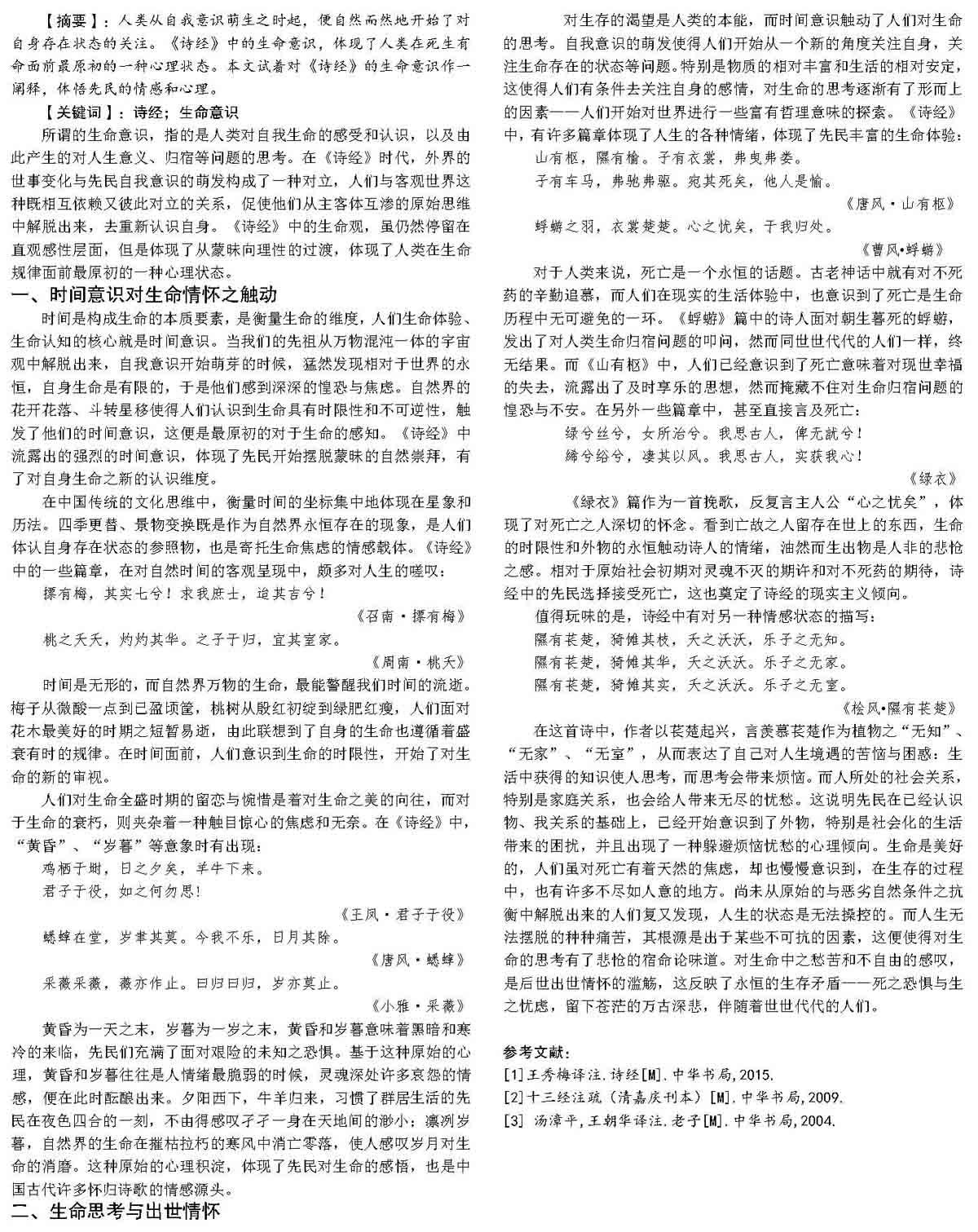
所谓的生命意识,指的是人类对自我生命的感受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生意义、归宿等问题的思考。在《诗经》时代,外界的世事变化与先民自我意识的萌发构成了一种对立,人们与客观世界这种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对立的关系,促使他们从主客体互渗的原始思维中解脱出来,去重新认识自身。《诗经》中的生命观,虽仍然停留在直观感性层面,但是体现了从蒙昧向理性的过渡,体现了人类在生命规律面前最原初的一种心理状态。
时间是构成生命的本质要素,是衡量生命的维度,人们生命体验、生命认知的核心就是时间意识。当我们的先祖从万物混沌一体的宇宙观中解脱出来,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的时候,猛然发现相对于世界的永恒,自身生命是有限的,于是他们感到深深的惶恐與焦虑。自然界的花开花落、斗转星移使得人们认识到生命具有时限性和不可逆性,触发了他们的时间意识,这便是最原初的对于生命的感知。《诗经》中流露出的强烈的时间意识,体现了先民开始摆脱蒙昧的自然崇拜,有了对自身生命之新的认识维度。
对于人类来说,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老神话中就有对不死药的辛勤追慕,而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体验中,也意识到了死亡是生命历程中无可避免的一环。《蜉蝣》篇中的诗人面对朝生暮死的蜉蝣,发出了对人类生命归宿问题的叩问,然而同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终无结果。而《山有枢》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死亡意味着对现世幸福的失去,流露出了及时享乐的思想,然而掩藏不住对生命归宿问题的惶恐与不安。在另外一些篇章中,甚至直接言及死亡:
在这首诗中,作者以苌楚起兴,言羡慕苌楚作为植物之“无知”、“无家”、“无室”,从而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境遇的苦恼与困惑:生活中获得的知识使人思考,而思考会带来烦恼。而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也会给人带来无尽的忧愁。这说明先民在已经认识物、我关系的基础上,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外物,特别是社会化的生活带来的困扰,并且出现了一种躲避烦恼忧愁的心理倾向。生命是美好的,人们虽对死亡有着天然的焦虑,却也慢慢意识到,在生存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未从原始的與恶劣自然条件之抗衡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复又发现,人生的状态是无法操控的。而人生无法摆脱的种种痛苦,其根源是出于某些不可抗的因素,这便使得对生命的思考有了悲怆的宿命论味道。对生命中之愁苦和不自由的感叹,是后世出世情怀的滥觞,这反映了永恒的生存矛盾——死之恐惧与生之忧虑,留下苍茫的万古深悲,伴随着世世代代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