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星圆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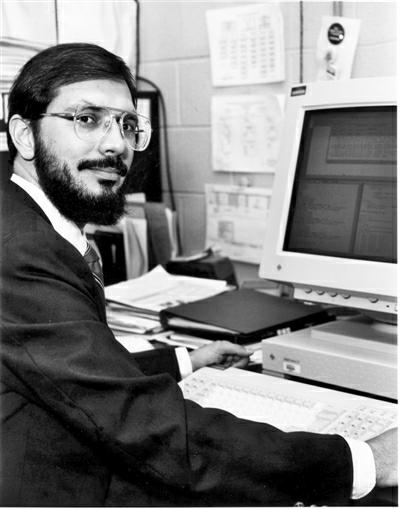

韦伯在声望鹊起后的快速陨落,使引力波探测在燃起短暂的希望后重新陷入渺茫。然而大致就在这时,一项天文发现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为引力波探测注入了新的生机。
卢昌海
1974年夏天,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研究生赫尔斯受导师泰勒教授的“指派”,在阿雷西博天文台从事一项系统的脉冲星搜索,作为博士论文的基础。
搜索天体是比较枯燥的,且每天的流程高度重复,不过跟依赖肉眼的早期搜索相比,赫尔斯的搜索已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计算机辅助技术,从而减轻了繁重性。
在赫尔斯的搜索展开之时,人们已发现了约100颗脉冲星,因而脉冲星已算不上稀罕天体,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只要技术足够先进,发现新的脉冲星乃是意料中的事。由于阿雷西博天文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直径1,000英尺(约合305米)的射电天文望远镜,技术的先进毋庸置疑,因此赫尔斯的工作虽然枯燥,成功却是有保障的。
不一样的脉冲星
果然,搜索展开后不久的1974年7月2日,意料之中的发现就落到了赫尔斯头上。
赫尔斯发现了一颗信号很微弱的脉冲星,只比探测阈值高出4%左右——换句话说,信号只要再弱4%以上,这颗脉冲星就会被赫尔斯的计算机探测程序所排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颗脉冲星的发现有一定的幸运性。
由于脉冲星已算不上稀罕天体,信号微弱的脉冲星照说即便被发现,也容易遭到轻视。不过这颗脉冲星有一个指标引起了赫尔斯的重视,那就是它的脉冲周期——也就是它作为中子星的自转周期——特别短,仅为0.059秒左右,在当时已知的所有脉冲星中可排第二,仅次于大名鼎鼎的蟹状星云脉冲星。这种个别指标上的“冒尖”抵消了信号微弱的劣势,使这颗脉冲星变得吸引眼球,于是赫尔斯对它进行了再次观测。
再次观测的时间为8月25日,目的是对脉冲周期作更精确的测定。
测定的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在短短两小时的观测时间内,脉冲周期居然缩短了28微秒。脉冲星脉冲周期的变化本身并非稀罕之事,比如尘埃阻尼就可使脉冲星因损失转动能量而致脉冲周期发生变化。但那样的变化往往是极细微的,短短两小时内改变28微秒可谓闻所未闻。更离奇的是,尘埃阻尼一类的因素只会造成转动能量的损失,从而只会导致转速变慢,也即脉冲周期增大,赫尔斯观测到的却是脉冲周期的减小。
为了搞清状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赫尔斯对这一脉冲星作了更频繁的观测。观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脉冲周期确实在以一种对脉冲星来说快得有些离奇的方式变化着,且变化的快慢并不恒定——比如在9月1日和9月2日的两小时观测时间内,脉冲周期的减小幅度就不是28微秒,而是5微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赫尔斯考虑了若干可能性,比如某几次观测出错,或计算机程序有误,但都逐一得到了排除。
双星系统
最后,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假设浮出水面,完美地解释了观测效应,那便是:赫尔斯所发现的脉冲星在绕一个看不见的伴星——确切地说是绕它与伴星的质心——作轨道运动,脉冲周期的变化是轨道运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
这一假设若成立,即脉冲周期的变化果真是轨道运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那么一个直接推论就是:依据轨道运动沿地球方向的投影速度之不同,脉冲周期应该既可以减小(对应于投影速度为正)也可以增大(对应于投影速度为负)。赫尔斯针对这一推论作了更多观测,结果不仅观测到了脉冲周期的减小和增大,也观测到了其在两者之间的转变,为这一假设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证据链”。不仅如此,从脉冲周期的变化规律中,赫尔斯还推断出了脉冲星的轨道运动周期约为7.75小时。
7.75小时是非常短的周期,这意味着脉冲星离那个看不见的伴星相当近,轨道线度相当小,运动速度则相当快。由于天体世界里的轨道都是由引力支配的,而脉冲星块头虽小,以质量而论却是像太阳那样的庞然之物,能让如此庞然之物沿相当小的轨道高速运动,则那个看不见的伴星也必然有极可观的质量。这种绕伴星“翩翩起舞”的脉冲星属首次发现,这使得其地位由仅仅吸引眼球变为了非同小可。
这非同小可的发现在泰勒和赫尔斯的搜索计划里其实是有所期待的。
泰勒和赫尔斯的搜索,其主要目的固然是发现更多脉冲星,从中窥视它们的更多性质,但在这堂正目标之外,对意外惊喜也是有所期待的。在事先拟定的搜索计划中,泰勒和赫尔斯特别提到的一类意外惊喜就是“发现哪怕一例双星系统中的脉冲星”。
为什么“发现哪怕一例双星系统中的脉冲星”也算得上惊喜呢?因为在天体世界里,双星系统与单星有一个巨大区别,那就是提供了观测天体在相互引力作用下作轨道运动的机会,通过那样的机会能测算出天体的许多性质,其中包括质量。别看当时已发现的脉冲星多达100颗左右,能测算出质量的却一颗也没有——因为孤零零漂泊在遥远天际里的脉冲星是没机会显示质量,从而也没法测算质量的。
惊喜既已迎来,消息就不能一个人扛着了。9月18日,赫尔斯通过信件及内部短波通信(那时长途电话还很罕见)通知了远在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导师泰勒。在重大发现面前,科学家的行动速度丝毫不亚于侦探,接到消息的泰勒当即乘飞机赶赴阿雷西博天文台,展开了对这一双星系统的研究。
这一双星系统如今已被称为“泰勒-赫尔斯双星”,其中的脉冲星则被命名为PSRB1913+16。泰勒-赫尔斯双星中的那颗看不见的伴星被认为也是中子星,并且有可能也是脉冲星——只不过由于脉冲不扫过地球方向,因而无法观测。泰勒-赫尔斯双星与我们的距离约为21,000光年。
泰勒-赫尔斯双星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极大兴趣。在1975年初的短短两星期内,知名刊物《天体物理学期刊快报》一连发表了7篇有关这一双星的论文。截至1977年,论文数目更是超过了40篇。这在科学日益“产业化”,许多科学计算有现成软件包可用的今天并不稀奇,在当时却算得上相当热门且相当快速了。那些论文对泰勒-赫尔斯双星所涉及的物理效应几乎进行了“地毯式”的研究。
经过那样的研究,这对双星的基本信息被摸清了——而且是以相当高的精度被摸清了。不仅如此,这种摸清信息的过程还有着相当的新颖性,值得略作介绍。
首先说说质量。对双星系统来说,推算质量的基本线索是轨道运动。具体地讲,只要知道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周期,就能用牛顿理论推算出双星的总质量。但不幸的是,对泰勒-赫尔斯双星来说,伴星压根儿就看不见,轨道大小自然也就未知了。
相对论“逆袭”
有什么办法能补上这一缺失信息呢?答案是广义相对论。
熟悉物理学史的读者也许知道,广义相对论提出之初有所谓“三大经典验证”,其中之一是解释了水星近日点的反常进动。这种反常进动在一般双星系统中也存在,被称为“近星点进动”。不仅如此,双星系统的“近星点进动”其实比水星的近日点进动更简单,因为后者混杂了来自其他行星的引力摄动,真正广义相对论独有的效应——所谓“反常进动”——只占很小比例。而对双星系统来说,其他天体的影响可以忽略,从而所有进动都是“反常进动”,都是广义相对论独有的效应。按照广义相对论,双星系统的近星点进动幅度与轨道大小有关。利用这一额外关系,双星的总质量与轨道大小这两个未知参数便可被“一锅端”——同时得到推算。
这种推算在数学上十分普通,在物理上却是一种开辟新局面的新颖做法,因为这是首次用广义相对论推算物理量的数值。在以往,科学家们虽早已习惯用牛顿理论推算诸如行星质量那样的物理量的数值,比牛顿理论更“高级”的广义相对论却反而始终只处在一个被检验的位置上。只有这一次,由于牛顿理论“黔驴技穷”,广义相对论才终于有机会做了一次漂亮的“逆袭”,成了推算物理量数值的工具。
科学家的胃口是“贪婪”的,这种“逆袭”有一次就有两次。
这种“逆袭”之所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脉冲星PSRB1913+16的脉冲周期的高度稳定。在扣除了诸如轨道运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之类可以确切计算的物理效应之后,脉冲星PSRB1913+16的脉冲周期每100万年仅变化5‰左右,堪称是当时已知最精确的时钟之一。这种脉冲周期的高度稳定意味着泰勒-赫尔斯双星所处的环境高度“洁净”,尘埃阻尼一类的未知效应微乎其微。这种脉冲周期的高度稳定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进一步探索的重点当然是相对论效应。泰勒-赫尔斯双星的轨道半长径仅为日地距离的1.3%左右,甚至跟太阳的直径(139万公里)相比也大不了多少。两个总质量比太阳质量大数倍的天体,沿着几乎能塞进太阳肚子里的紧密轨道运动,简直是一个探索相对论效应的“梦工厂”。
在这个“梦工厂”里,各种相对论效应都比太阳系里的显著得多,比如近星点的进动——如前所述——跟水星近日点的反常进动相比,快了约35,000倍。
除近星点的进动外,另一类重要——并且同样“老资格”——的相对论效应是时钟延缓效应。这类效应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轨道运动产生的运动时钟延缓效应;另一部分是伴星引力造成的引力场时钟延缓效应。时钟延缓效应会对观测到的脉冲周期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比多普勒效应小得多,因而对观测精度的要求更高,同时也有赖于脉冲周期本身的高度稳定。由于轨道参数已知,对时钟延缓效应起决定作用的脉冲星PSRB1913+16的轨道运动速度及它与伴星的距离便也成为已知,时钟延缓效应于是于是计算出来。
时钟延缓效应的重要性在于:这种效应可以对双星质量做出区分(这可从伴星引力造成的引力场时钟延缓效应只取决于伴星质量这一特点中得到预期),从而可推算出两者各自的数值。具体的结果是:脉冲星PSRB1913+16的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1.44倍;伴星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1.39倍。
这种推算使广义相对论再次成了推算物理量数值的工具,是又一次漂亮的“逆袭”。
引力波效应
不过,在一个探索相对论效应的“梦工厂”里,广义相对论不能只搞“逆袭”,也得老老实实接受一些新的检验。从检验的角度讲,对双星质量的推算就先天不足了,因为它是靠了广义相对论才能得到结果的,从而精度再高也不能反过来验证广义相对论,否则就成循环论证了。那么,这个探索相对论效应的“梦工厂”能否对广义相对论进行新的检验呢?答案是肯定的,手段之一正是引力波。
泰勒-赫尔斯双星包含了两个比太阳还“重”的天体,并且沿着几乎能塞进太阳肚子里的紧密轨道运动,这些因素都是非常有利于发射引力波的。这种引力波的辐射功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结果约为7亿亿亿瓦,相当于太阳光度的2%,或一颗绝对星等约为9的暗淡恒星的光度,从而可勉强跻身天文数字。
不过虽功率勉强跻身天文数字,考虑到泰勒-赫尔斯双星远在21,000光年以外,直接探测其所发射的引力波仍远远超出了目前的技术能力——更遑论当年。
但幸运的是,由于引力波会带走能量,因而双星轨道会逐渐蜕化,使双星逐渐靠近。而双星靠得越近,轨道周期就越短。因此通过对泰勒-赫尔斯双星的轨道周期进行细致监测,原则上就可对引力波造成的轨道蜕化效应进行检验。这种检验假如成功,虽不等同于直接观测,也依然能构成对引力波极为有力的支持。
1978年12月,距离泰勒-赫尔斯双星的发现相隔了四年多的时间,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一次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上,泰勒作了历时15分钟的演讲,报告了对泰勒-赫尔斯双星轨道周期所做的细致监测,监测结果表明,轨道周期的变化在20%的精度内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引力波造成的轨道蜕化效应——相吻合。美国广义相对论专家威尔盛赞了这一结果,并将之与1919年发布的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结果相提并论。这虽是显著的夸张,但在广义相对论研究长期低迷的时代,这一结果确实堪称亮点,而且它所涉及的是引力波这样一种此前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天堂”里,却从未得到过观测检验的概念,从而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意义。
不过,泰勒的结果虽是亮点,区区20%的精度却绝非观测和检验的终点。科学不是一种固步自封的体系,自泰勒的结果发布以来,天文学家们继续改进着观测,积累着数据,以越来越高的精度对广义相对论的这一重要预言进行着检验。这种对比在千分之一量级的精度上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而对引力波的存在提供了虽然间接却极为有力的支持。
双星合并终有时
科学家们试图倾听时空的乐章而暂不可得,却意外地在脉冲星的圆舞曲里得到了补偿,这在人类探索引力波故事中是一个“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难忘插曲。脉冲星的圆舞曲虽“听”不到,却“看”得见,它精确地遵循着广义相对论的指挥,基本扑灭了对引力波的残存怀疑。
而且跟前面提到的“逆袭”成果不同,对引力波造成的轨道蜕化效应的检验不折不扣地构成了对广义相对论的检验,因为在这种检验里,诸如双星质量那样的参数在计算之前就已作为“逆袭”成果得到了确定,从而不再有变更的余裕。换句话说,广义相对论对引力波造成的轨道蜕化效应的预言是不再有回旋余地的预言,其所经受的是直面观测的严苛检验。而比这更严苛的则是:自泰勒-赫尔斯双星之后,天文学家们陆续发现了更多双星系统里的脉冲星,它们每一个都在观测所及的精度上检验着广义相对论。
这也是检验现代物理理论的共有模式。现代物理理论都带有一定数目的自由参数,比如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带有约20个自由参数,从而都有一定的拟合观测的能力。但一个高明的物理理论之所以高明,就在于它能经受的独立检验及它能做出的独立预言的类型和数量远远超过了自由参数的数目,这两者的差距越悬殊,理论就越高明。广义相对论正是这种理论的佼佼者。
在本文的最后,有两件“后事”交待一下。第一件事关泰勒-赫尔斯双星:由于引力波造成的轨道蜕变,泰勒-赫尔斯双星将在约3亿年之后合并,圆舞曲也将“曲终人散”(实为“曲终星聚”);第二件事关泰勒和赫尔斯这两个人:由于泰勒-赫尔斯双星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重要价值,泰勒和赫尔斯这对师生拍档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