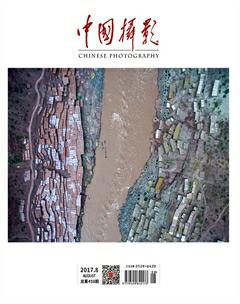摄影,一种生产新知识的媒介
何:很高兴又能在伦敦相见,我想今天采访以一个陈词滥调的问题开头:您最初为什么选择摄影?
克诺尔:我在德国出生,因为我的父母都是美国人,所以我出生在德国的一家美国医院。我的父母现在都去世了,父亲生前是一名富有想象力的生意人,他曾在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开设了自己的公司,我后来就跟随父母移居到了波多黎各。
我读书的那个年代(1960-1970年代),中学学历的女性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是很难的事情,因而我在高中毕业后想继续去上大学。但当你特别年轻,比如18岁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我在父母的支持下去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法兰克尼亚学院(Franconia College)学习,那时我第一次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学习的专业,我选择了摄影,另外还有哲学、文学和艺术史。我在法兰克尼亚学院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摄影专业老师,名为艾琳·考文(Eileen Cowin)。我当时对摄影一窍不通,但考文给予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我在那时开始接触并学习了一些关于摄影的知识,但当时年纪尚小,也只是在做不同的尝试。当时的学院还教授创意写作的课程,我也因此开始接触到学术写作,但这些学习直到后来才产生了作用。
由于我在拉丁美洲长大,所以在美国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星人,并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更无法同其他人分享我的成长经历。第二年,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除了我心爱的摄影之外,我在当时的学习生活并不快乐。他紧接着问我,你是否想过去法国巴黎学习?我回答道:没想过,但未尝不可呢。
于是,我去到了巴黎,在一个为申请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或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的学生设计的预科学校学习古典美术和纯艺术,学习绘画和素描,然而虽然我尝试过,但我并没有通过这两所学院的入学考试。于是,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重新思考自己对于摄影的喜爱,所以我决定申请英国学院的摄影课程,因为当时只有英国开设了摄影专业的学位课程。其中,伦敦中心理工学院(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授予学生摄影和电影荣誉学士学位,我在第一年同时学习了摄影和电影的课程,之后特别选择了摄影实践。
然而, 在被伦敦中心理工学院录取之前,当我在1976年7月4日第一次来到伦敦时,我知道如果我想成功进入到这所大学就必须要一份摄影的作品集。我当时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但还是希望能够有技术上较硬的照片,所以我去到了哈罗技术与艺术学院(Harrow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Art)开设的一个半日制的课程,这个学院如今已被并入了威斯敏斯特大学了。我在这个课上学习了职业摄影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如何运用大画幅相机以及影棚广告摄影的技术,我也正是在这个课程上认识了奥利维耶·里雄。
我们成为了朋友,晚上一起去俱乐部看现场演出,然后发现了“朋克”这个音乐亚文化群体,便决定一起去拍摄朋克乐队和乐迷,并将这些肖像作为我们的作品集。不久前《朋克》系列以摄影书的形式正式出版了。因而,我們在1976年拍摄的一组16张的作品集帮助我进入到伦敦中心理工学院。很有趣的一点是,当我向人们展示我和里雄共同完成,且共同署名的作品集时,人们都觉得这太不寻常了,因为摄影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艺术实践类型,但我们决定共同拍摄,且共同署名,因而系列中并没有提到哪张照片是我拍的,哪张是里雄拍的。
正是凭借《朋克》系列我们共同进入了这所大学,不过我当时被问到一个问题,即是否受到了奥利维耶·里雄的影响,但事实上我在申请中递送了两件作品,其中一个就是我个人的作品集,它是一个三维的摄影作品,类似雕塑化的摄影,如今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只可惜当时没有留下存档的文件。
这个课程事实上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学院的左翼老师对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批判性,我们会参加独立的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试图理解对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关意识形态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我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的调研促使我展开关于《贝尔格拉维亚》(Belgravia,1979—1981)摄影系列的创作。
当时我还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深知那个时代的纪实摄影是去记录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纪实摄影师往往是白人男性,很少有女性摄影师。当然,随着我对摄影史逐渐深入的了解,我发现还是有女性纪实摄影师的存在,例如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 White)曾在印度完成了一组非常迷人的作品,当然还有其他人,不过总的来说都是少数。当时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都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他们去到其他的国家拍摄照片,但很少深入到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中去,他们往往不会说当地语言,只需要一个助理就好了。我发现这种摄影完全不是我想要去追随并实践的。我想要去拍摄特权阶级的文化和生活,我自己便是出生于中产阶级上层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国际商人,所以我随之开始拍摄特殊的、名为《贝尔格拉维亚》的项目。
何:能和我们简单描述一下《贝尔格拉维亚》这组作品吗?
克诺尔:这是一组高度风格化的、与拍摄对象合作完成的肖像作品,系列中的被摄对象是居住在伦敦贝尔格拉维亚区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们。贝尔格拉维亚区靠近哈罗德(Harrods)和哈维尼克斯(Harvey Nichols)百货,是伦敦最具大都会气质的区域,世界各地的人都聚集在此,但仅有非常少数的富人买得起这里的房产。我在这一系列的创作中将他们告诉我的一些话用作了作品中的文本,我花了很长时间跟他们聊天,我和他们一起去衣帽间挑选衣服并且一起完成了作品。接着我将文本打印出来,并将其置于图像的下方,强调这些文字和图像一样是被建构起来的。
何:你在作品中将图像和文字结合的策略是否受到维克多·布尔金(Victor Burgin)的影响呢?
克诺尔:维克多·布尔金是我的导师,他的作品参考了广告摄影的策略,人们在这个领域内会同时使用图像和文字,就像我作品中那样。我记得布尔金有件作品就是在图像中间和下方运用了文字。布尔金当时邀请了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来学校讲座。
欧文斯所创作的《郊区生活》(Suburbia )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它也影响了马丁·帕尔,但却是不同的方向。《郊区生活》是欧文斯拍摄的生活在南加利福尼亚郊区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系列纪实作品,他们都住在这些被房产商成片开发的住宅(tract house)中,由于房价低廉,质量又好,很多南加州的工人和中产阶级都选择生活在这里,包括欧文斯自己。欧文斯拍摄并采访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并引用了他们的话。当《郊区生活》在美术馆展览时,欧文斯将照片和文字分开予以展示,后来他被建议将图像和文字结合起来,这样作品会显得幽默一些。
欧文斯受布尔金邀请来到伦敦中心理工学院给我们做了一堂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和他一起去了酒吧,我当时问了他一些问题,问你会挪动拍摄场景中的物件吗?你是怎样拍照的?他说他会接受一切本来的面貌,作品中使用的文字也都是他们如实所说的内容。然而,这种如实照搬人们本意的说法并不是我在创作中想要的,我也跟他本人进行了一些辩论,接着他说事实上他也和拍摄对象有些合作,比如适当移动了某些陈设之类的。上述这些大概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也对欧文斯的作品有了更多的理解,这直接影响了《贝尔格拉维亚》的产生,我也非常感谢维克多·布尔金在伦敦中心理工学院开设的这门课程对我的影响。
事实上,布尔金协助学校一起组建了这门课程,我们当时学习了很多哲学理论,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与符号学相关的议题,关于标志性符号如何被转译到摄影之中。我当时阅读了很多语言学的书籍,对诸如索绪尔、皮尔斯的论著十分感兴趣,尤其是英国语言学家皮尔斯,他的符号三分法中有一个对摄影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总之,我论文的结论是,摄影是一种话语,而不是一种符号学(semiology)意义上的符号(sign)。
我们在课程中还学习了罗兰·巴特的理论,阅读了关于图像和文本的知识,而这些都对我创作《贝尔格拉维亚》产生了影响。另外,还有关于文字可以延长观者阅读时间的考量,这也是布尔金的实践内容之一。除此之外,我还尝试在作品中运用解构的策略,这在新浪潮电影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我在《绅士》系列中运用了演员的概念,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大多是我在当地找到,或是朋友们扮演的,从中可见电影对我所产生的影响。
何:这正好呼应了我下一个问题,作为英国第一批受益于后现代理论的摄影实践者之一,你的创作也大多基于理论为出发点,那么这种创作方式对你过去近40年来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克诺尔:事实上艺术家都会做调研,但调研的价值直到观念主义出现之后才被珍视,因而我们继承了这一传统,我也将调研作为艺术实践的一个过程,并一直在使用这种创作方式。在我看来,摄影也是一种研究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摄影是生产新知识的媒介。
何:我在近期研究你早期作品的過程中看到了一张早在《学院》系列中就出现的动物形象,这张作品名称为《地方精灵》(The Genius of the Place),背景是欧洲某个艺术院校美术馆,这张照片与你未来的作品遥相呼应,而在作品中将动物和地点并置也成为你之后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克诺尔:事实上,我作品中出现的第一只动物是《德行与欣悦》(The Virtues and the Delights,1992-1994)中的一只宠物狗,但它和后来作品中出现的动物不是一个概念。《地方精灵》中出现的那只猩猩事实上是我刻意构建的一个有关达尔文的笑话,我想说的如今的精英、绅士事实上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图像中出现的动物像是对空间的一种侵扰,我也尝试在每个系列不断改进将动物和场景联系到一起的方法。对我来说,早期作品中出现的动物是对绅士和鉴赏家概念的戏仿,而后期的作品则指向空间中越轨的议题。
早先,我在《学院》系列的一个名为《参观者》(The Visitor)的章节中挪用了猴子标本,这组作品是在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中完成的。我从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租借了不同种类的猴子标本,然后将其中的一组标本放置在奥赛美术馆的雕塑展区。所以我每一次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将动物形象运用在作品中。近期我在拍摄野生的动物,尤其是在印度,你在今天依然可以在印度城市的街道中看到非常多样的动物。当我第一次到印度之后,脑中就闪过我可以拍摄活着的动物的念头。
何:你在1991出版了一本名为《卓越的标记》(Marks of Distinction)的画册,其中集中展示了你从毕业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四组作品,能回忆一下那个阶段你的工作和生活吗?
克诺尔:这本书有英文和法语版本,1980年毕业后,我重新回到了法国,拜访了当时的法国摄影博物馆,除此之外,法国还有一个由欧洲摄影之家(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策划的、每年11月举办的名为“摄影之月”(Month of Photography)的活动,《贝尔格拉维亚》的27张作品有幸在“摄影之月”期间于一家名为萨米亚萨马的画廊(Galerie SamiaSaouma)展出,我也成为这家画廊中参与展览的第一位女性摄影师。
这次展览获得了来自法国不同杂志的一致好评,但当时卖得并不好,我当时作为自由摄影师会想办法生存下去。不过我的作品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第二年我有机会作为五位摄影师之一参与了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的群展。坦白的说,1980到1986年之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六年,直到1986年我创作的《鉴赏家》系列有了一些销售才有了一些好转,之后我也获得了教学的职称,但那个过程并不简单。

何:我在《卓越的标记》画册后读到帕特里克·莫里斯(Patrick Mauries)撰写的一篇论文,名字叫做《局外人》(The Outsider),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
克诺尔:我就是局外人。我认为英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在这里并不会完全脱离,但会从一定的距离来观察事物。我在伦敦生活了40年,但我依然不会称自己为英国人,我可以听出我的美国口音,我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性格来适应这个社会,但我对英国的机构充满了憧憬之情。除了我的美国身份之外,从技术上来说我可以算是一名英国摄影师,这也是我喜欢伦敦的原因。
何:你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很多作品都与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院校等艺术机构有关,能谈谈原因吗?
克诺尔:这些作品是有关摄影在纯艺术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摄影挑战并改变纯艺术的对话。摄影改变纯艺术的现实还在于有越来越多女性艺术家,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女性主义摄影实践者的出现,她们的作品涉及关于女性主义和自由的话语。
何:我们接下来聊聊你在2002年出版的《场所精神》一书,你是如何理解“场所精神”在你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
克諾尔:“场所精神”重复出现在我的作品当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意为建筑空间的“氛围”,将这个词用作书名既简单又能达意。我在这本书中还展示了几张录像作品的截屏,我本想在设计上做一个后现代的尝试,但如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它在设计上非常失败。即便如此,我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和丽贝卡·科美(Rebecca Comay)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对话,她作为哲学教授对我作品中的哲学问题展开了讨论。此外,大卫·坎帕尼(David Campany)在这本书中贡献了他的第一篇摄影评论,内容是关于博物馆和摄影的议题,而紧接着他便出版了《艺术与摄影》(Art and Photography)一书。
何:在此之后,您花费了很多年创作《印度之歌》,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克诺尔:《印度之歌》的拍摄过程并不算复杂。2008年我在一次旅行中找到了一些我想拍摄的地点,接着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去获得进入这些地点拍摄的许可,并且拍摄场景和动物的照片。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拍摄印度,往往人们都选择拍摄建筑的外观,但我希望通过拍摄建筑的内饰、结构,以及那些允许女性进入的空间,并将动物的形象带入作品中以表达不同的意思。
我尝试在《印度之歌》中将照片与印度性别问题、上层阶级文化联系起来,同时还尝试去追溯那些印度神话故事,而我的确发现很少有西方摄影师如此深入地用影像去探讨和印度相关的议题。
除了那些精彩的神话传说之外,吸引我的还有印度各式的融合建筑,比如希腊和印度风格的混合让我感到十分惊奇,我也希望能够突出这一点。如果印度历史中可以接受西方建筑文化上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或许这点太过罗曼蒂克,但我认为建筑文化的融合正反映了印度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和谐相处。
我最近刚从印度回来,之前去到本迪宫殿(Palace of Bundi)看到一个被庭院围绕的房间,四周都装饰着印度袖珍画(miniature painting)。令我感兴趣的是袖珍画作为档案的概念,这也源于我对虚构纪实(documentary fiction),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以及对摄影构建这种虚构纪实能力的概念所产生的兴趣。这些墙面上的袖珍画是对日常生活的记录,画上有对真实建筑的刻画,也有故事和神话的描述,这是一种档案。
我觉得我在做的作品正具备着袖珍画的功能,即是对现实记录的同时又融合了虚构的故事。当这些博物馆的空间不断发生变化时,我作品中的纪实功能便首先展现了出来。我当时在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里拍摄了一个房间,而那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趣的是时间的改变也能改变照片本身的意义。
何:在印度之后您又选择了到日本拍摄《物语》项目,我相信日本神道教中对“场所”有着特别的认知,他们相信每个地方都是自己的守护神,我想这与您作品想传达的“场所精神”不谋而合。
克诺尔:你在日本到处都可以看到神社,这是发源自日本且在当地最流行的一种宗教文化。然而,我感兴趣的是,佛教从印度起源,经由中国传到朝鲜,又来到了日本,我对这些国家佛教文化演变的形式十分入迷。印度的佛教和日本佛教完全不同。当我第一次来日本时,我决定要在日本不同的大城市拍摄不同的宗教空间,因而我去到了京都和东京,我当时在东京住的酒店隔壁就是一处绝美的神道教神社。
我从2012年开始拍摄日本的项目,我被地震后日本文化的脆弱性震撼了,除此之外,日本高科技的现代文化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觉得日本传统家庭价值观对女性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正在创作的项目是36张女性肖像,照片上会附有她们书写的俳句。这一系列名为《花柳界》(Karyukai),作品中拍摄的女性都身着和服,一方面是因为它无可复制的美,而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一种束缚,和服穿在身上本来就不舒服。我在影棚中拍摄了一些照片,同时也拿到了她们写的俳句,目前已经完成了6张作品,然而我还需要完成30张。
何:那么除了上述的项目之外,您近期还有哪些计划呢?
克诺尔:我和安娜·福克斯(Anna Fox)准备合作一个美国公路行的项目,想法起源于大卫·坎帕尼所出版的那本《开放的公路:摄影与美国公路旅行》(The Open Road: Photography and the American Road Trip)。我们在巴黎摄影展(Paris Photo)上一拍即合,所以去年一起抽时间去到美国进行其中一个部分的拍摄。这一项目的概念是去回述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所拍摄的美国东海岸1号公路(U.S. Route 1),她的这一项目原本并不出名,直到最近史泰德出版社(Steidl)出版了她的这一作品之后才被人们所熟知。我们不想太刻意地沿着她走过地路线,而是选择这条公路中最贫乏的一段,即从缅因州(Maine)到基韦斯特(Key West)的部分。
在拍摄过程中我用手机来做记录,回来之后将这些照片打印出来,然后再重新回到其中的一些地方拍摄。事实上我们俩人都想在这个项目中找到全新的创作方法,并且一起去体验一个新的旅程。下一次拍摄将在今年的9月。
何: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英国脱欧对你作为艺术家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克诺尔:当然。我很多作品都是关于移民的话题,而我本身也是在跨国文化中成长的移民,我的父亲是从波兰搬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我的母亲是早前移民到美国的挪威和德国裔混血。移民是美国文化中的一部分。英国执行脱欧之后势必出现社会问题,它也会影响我思考的方式。
图片提供:凯伦·克诺尔(Karen Kno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