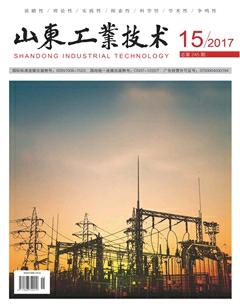解读广东省集中交易第一单
岑建军++王梦瑶


摘 要:本文详细解读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完成的2016年首次电力集中竞价交易过程。通过分析本次交易中的交易特点,并详细模拟了本次交易过及电价形成过程,在对之后的广东省竞价交易新动态的对比分析后,得出电力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的深度思考,并分析得出电力交易中的异常现象对交易对象心理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电力交易;集中竞价;申报价差;交易异常
DOI:10.16640/j.cnki.37-1222/t.2017.15.259
0 引言
能源革命的核心价值诉求是绿色低碳,节能优先,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在能源供给上,建立多元供应、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在产业技术上,要紧跟国际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推动技术、产业、商业模式创新;在体制上,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强调“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立法是电改的顶层设计,没有立法,就不能实现国家电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因此,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必须审时度势,从推动能源革命和建立法治社会的战略高度来进行总体设计,必须紧紧扣住这两个大背景、大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清本轮电改究竟改什么,从而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2]。
据此本文主要针对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重点内容进行解读,并对电力体制改革文件的意义进行了探讨[3]。
1 新闻简报
在国家能源局电力体制改革专栏中,改革动态专题中报道了“售电公司首次参与竞争交易 ,广东成交电量68096万千瓦时”消息,报道称3月25日,广东省内36家发电企业与81家电力用户在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开展了3月月度集中竞争交易。经过3小时的报价后,出清结果公布。7家发电企业未能中标电量,80家电力用户最终成交,最终平均降价水平为0.125元/千瓦时。据悉,这是广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首次吸纳售电企业参与的集中竞争交易,标志着售电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
据了解,广东下月月度集中竞争交易将继续根据各市场主体的申报电量,合理控制供需规模,实现有效合理竞争。
2 交易详情
3月25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了2016年3月份集中竞争交易,集中撮合,竞价规模为10.5亿千瓦时,竞价申报时间2016年3月25日10:00-12:00.其中 申报价差即(用电企业申报价-目录电价)或(发电企业申报价-批复电价)
供应方:共有36家发电企业参与报价,总申报电量为12.9767亿千瓦时,异常报价剔除量为0万千瓦时,其中29家最终成交,成交的发电企业平均申报价差为-0.429023元/千瓦时,其中最高成交申报价差为-0.2403元/千瓦时,最低成交申报价差为-0.500元/千瓦时。
需求方:共有81家用电企业参与报价,总申报电量为11.218亿千瓦时,其中80家最终成交,成交的需求方平均申报价差-0.0243973元/千瓦时,其中,作为需求方的售电公司获得较大收益,共9家参与,8家成交,平均成交价差为-0.151元/千瓦时,成交电量6.81亿千瓦时,占总交易量的64.86%。
本次交易的售电公司主要包括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司、华润电力(广东)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广州恒运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新奥(广东)能源销售公司和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等8家在粤企业。
3 交易特点
3.1 交易时间临时调整
交易规定时间原定为2016年3月25日9:00-11:00.但实际操作中出现了电力用户不积极现象,未能按时填报交易需求电量。实际竞价过程,由于对市场预料不足,为提高交易量,监管部门和政府采取临时不就干预措施,将时间推迟至10:00-12:00。
3.2 申报量上限临时调低
按照交易规定,电力交易机构应提前发布发电企业集中竞价允许申报量的上限。发电企业可以以此为依据确定竞价电量的上限。此次交易过程中,在发电企业已经按要求完成申报上限电量的情况下,临时接到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通知,要求修改调低申报电量上限,一定程度造成发电企业的心里恐慌。
本次交易前,由于发电侧总意向电量为17.3亿千瓦时小于用电侧总意向电量10.8亿千瓦时,交易规模从14亿千瓦时被临时减少为10.5亿千瓦时,导致发电企业竞争压力较大。
3.3 存在非理性報价
发电企业在对用户和售电公司期望的降价水平不了解情况下,临时被要求降低报量水平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发电侧出现了不理性的大幅降低报价水平以争取市场的情况,表现为“纯杀价”。有的发电厂最高成交申报价差达-0.5元/千瓦时,导致平均成交价差水平为-0.1255元/千瓦时的“血拼价格”。
此次竞价结果创广东省组织集中竞价历史里来的最高降价水平,成为全国范围内发电企业降价水平较高的省份之一。
3.4 交易规则存在缺陷
交易规则中引入价差返还系数,申报价差电费差额按照3:1的比例返还给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在目前严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此举容易诱发发电企业在申报竞争电价时采取大幅降价以竞量的侥幸心理。
在《关于明确2016年售电公司参与直接交易的通知》中的异常报价和踢出电量机制在此次交易中被暂停,发电企业少了‘报太低可能作为异常报价被剔除的担心,整体让利过大。发电侧平均申报价差达-0.5元/千瓦时。
3.5 政府干预过多
从此次竞价过程来看,仍然是政府控制供需关系和竞争强度的形态,虽然名为“集中竞价”,但实际还是大用户直购的集中撮合模式,离真正的市场还有很大差距。endprint
4 模拟集中竞价计算示例
假定集中竞价交易规模上限为500万千瓦时,发电企业申报电量上限按竞争直购电量的1.2倍计算。
4.1 申报数据
供应方(发电厂)有5家参与报价,总申报量600万千瓦时,最高申报价差-0.1元/千瓦时,最低申报价差-0.18元/千瓦时。需求方(电力用户)共有7家参与报价,总申报量620万千瓦时,最高申报价差-0.001元/千瓦时,最低申报价差-0.02元/千瓦时。具体申报见表1。
4.2 形成价差对(已按差值从小到大排列)
价差对(发电企业申报价差--用电企业申报价差)形成规则:
(1)价差对为零或负值时,按差值对小者优先中标。
(2)价差对为正值时不能成交;即用电企业与发电企业所出价格小于目录电价或批复电价。
(3)若价差相同,按申报电量按比例分配或申报时间进行优先匹配。
4.3 集中撮合
(1)第1,2号价差对相同,成交电量按发电企业B,D申报电量B(均为96万千瓦时)分配;D,B企业分别售出40万千瓦时,用户1购到80万千瓦时,因用户1购电量满足。则与之对应的15,16,17价差对自动失效。
(2) 第3,4号价差对相同,但电厂D,B剩余电量不足以满足用户2的申报电量,所以全部成交后,用户2分别从D,B购得56万,共112万千瓦时,缺口8万。此时与D,B相关的第5-14价差对自动失效。
(3)按剩余价差对撮合18,19,20.因为用户2还缺口8万千瓦时,所以成交分配按(C:A:E申报电量=216:96:96=9:6:6)分配。
4.4 撮合结束后,成交电量,成交价差
可以看出,由于报价策略不当,用户7没有获得中标电量;由于主要受规模控制的约束,ACE电厂和用户6只有部分成交,反之,由于报价策略得当BD和用户1,2,3,4,5全部成交。
4.5 结算价格
(1)
(2)
(3)
其中为价差返还系数,在本次广州电力交易中为1:3。
5 深度剖析
5.1 交易评价
(1)广东省作为电力体制改革试点之一,开创了售电公司进入电力市场交易的首单,在售电侧改革推进过程中写下浓重一笔。但在售电主体进入业务实际操作阶段,支撑售电公司业务开展的信息化支撑平台成为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推进的迫切要求[4]。
(2)应加快完善电力体制改革市场交易的竞争规范;降低相关政府部门过度干预。
(3)发电企业报价偏离正常价格价格过多,存在非理性降价行为,这是市场规则混乱和市场刚开始博弈混乱的结果。
5.2 市场异常行为对电力用户心理影响
(1)电力信息平台发布交易信息不及时或临时变动导致用户心理恐慌,出现不理性竞价行为。如临时调低申报电量上限,导致发电侧出现了不理性的大幅杀价(心理群体整体智能低下定理)。
(2)电力用户仍依据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参考电价进行报价(集中撮合),若购电大宗电力用户(如售电公司需求量占60-70%)出现私下价格协商形成联盟,容易使三大类交易主体中的大用户(散户)为了保证能竞上中标,大用户只能选择跟随售电公司的报价在市场形成盲目跟风的羊群行为[5]。
(3)在交易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发电侧(供方)为防止没有中标电量和确保最大申报量全部出清,发电申报提交最低成交申报价(-0.5元/千瓦時)是个大概率事件。而在此后的交易时,没有成交的发电企业“吃一堑长一智”一定会杀价进入,依此趋势发电企业在电力竞价中压力山大。
(4)在交易中政府部门过度干预,如交易初期临时退后报价截止时间,及指定价差返还系数,相对松懈或宽松的电力规则使得售电侧与购电侧用户产生投机心理,对电力市场期望值降低,打消之后参与市场竞争积极性,不利于规范化市场体制形成。
5.3 广东电力交易新动态
4月26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公布了第二次月度集中撮合结果。交易系统网站的公布结果。
对比第二次交易结果,可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结果中:需方最高成交价-1.1厘/千瓦时。这部分电量的成交价是由散户报的,也就是参加交易的供应侧(发电厂),需求侧(售电公司,大用户)这三大类电力交易主体中所占比重较低的大用户成交结果。说明两年来,部分大用户的市场意识没有培养起来,参与度与实力都不如售电商。
(2)结果中:需方最低成交价-79厘/千瓦时。这部分是由售电公司报的,而最终市场竞价的利润又流入电网,肥水不流外人田。
(3)结果中:需方平均成交价-51.58厘/千瓦时。可知上个月初次市场交易后,交易双方都或多或少获得利润,需方的赌性显现,多数需方拿出至少10%出来,进行博弈。
(4)结果中:供方最高成交价-371厘/千瓦时,最低成交价-500厘/千瓦时,平均-436厘/千瓦时。说明供应方主要的电力生产方式中火电机组开始真正的竞争。
参考文献:
[1]朱成章.电力体制改革的难度(上)[J].大众用电,2016(04).
[2]戴丽.这些年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J].节能与环保,2016(01):24-31.
[3]刘洪深.电力体制结构模式演进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方向[J]. 大众用电,2016(01).
[4]洪猛.电力体制改革与核电电价政策浅析[J].中国核工业, 2016(01):51-53.
[5]刘纪鹏.国企改革助力电力体制新发展[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6(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