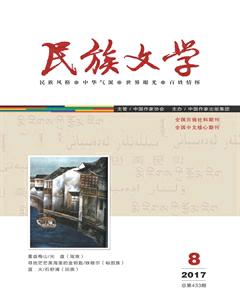枇杷郁郁生长
潘沁
老家的院子里,就剩下那棵枇杷树了。在它扎根的地方,原来是生长着一棵柿子树的,才长了两年,就高大飒爽,枝叶繁茂,但父亲却嫌它不结果,一刀砍去,才种下了这棵枇杷。枇杷树发扬前辈的传统,长得快而高,也懂得汲取前辈的教训,第二年就结了果,果实不大,却很甜美,这才保了命。
父亲喜种果树是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果子狸”,太爱吃水果。我读中学那年,沉迷赌博近一年的父亲眼看着他辛苦赚来的几十万元所剩无几,输出去的亦搏回无望,当即痛改前非,用所剩的几万元回乡下建起了这栋两层楼房。从一个城镇人变成一个乡下人,我并不情愿,但那红砖围墙围着的大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庭院吸引了我。次年春天,我们从母亲单位的平房宿舍搬到了距县城两三里路的村庄。一家四口站在大门前,望着宽阔的大院,父亲问我们想种什么。母亲说要种上各种蔬菜,再养些鸡鸭,这样平时连小菜都不用买了,过年过节又有鸡鸭吃。我说要在整个院子植一片桃林,春天满院桃花,再做一块“桃花谷”的牌匾挂在大门上。妹妹说要让院子满架葡萄,夏天可以坐在葡萄架下看书乘凉,一举手就可以摘到葡萄吃……
前院最终混合了我们各自想象的片段,李树生长,桃树开花,青菜、豆角、苦瓜生机盎然,靠墙的葡萄顺着架子遮住一米阳光,猫狗和谐相处,鸡鸭吵闹不休……我们的乡村生活就在前院的葳蕤中开始了。
母亲每天把家具门窗擦得光亮清爽,内心却是有些许不喜,她原想在县城新修的环城路旁买块地建一栋房子,但父亲死活不同意。现在想来,还是母亲有投资眼光,那里的房子不知升值了多少倍。但年纪越大,越是庆幸父亲的选择,父亲给了我们一院的乡愁,给了我们可以叶落归根的山水田园。尽管,父亲坚持的理由,按母亲的说法,“你爸就是想天天有人和他猜码喝酒!”父亲真的是找着各种借口请客,打一口井他就請亲戚邻人工人喝了半个月,而且是中午喝,晚上也喝,直喝到狗都睡了才散。
父亲以前是不恋酒的。他最初的工作是在远离县城的水泥厂做电工,那时的他勤奋积极,一门心思想入党。他个子不高,却爱打篮球,他和母亲在工厂的球场上相识相恋。母亲说起第一次去父亲家拜访,眼见泥砖老屋,四壁空空,“太穷了,真的就想跑!但知道了你奶死得早,你公身体又不好,你姑和你叔放学回来还要做农活,又觉得心疼。”其实母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只是没有父亲这么重的负担,但那时父亲的帅气和上进是母亲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父母成家后不久,双双调到了镇上,我仍记得所居住的县计量所里的那间低矮的平房,进门要猫着腰,屋里暗得像个窑洞。但父亲爱这个小家,他在家里是木工,自己做碗柜、桌椅;还是煤球工,太阳好的时候,他会做上百个煤球。他还常回村里帮弟妹插秧种田,收割种菜。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要养家,供养爷爷,供弟妹读书。我和妹妹出生后,姑姑见父亲太辛苦,没读完高中就辍学了,这令父亲一生自责。
父亲亦因为“文革”无缘大学。他从小学时就在爷爷的安排下养了一群鸭,靠着这些鸭子和它们的后代,供自己读完小学和中学,又考上了广西民院附中。可他再优秀也拧不过时代和命运。在县计量所几次申请入党而不得,跟同事又合不来,他赌气回到了那个远离县城的水泥厂,却不料等待他的是一场牢狱之灾。那时我刚读一年级,懵懂无知,父亲成为“贪污犯”我还是从家在公安局的同学口中知道的。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我再没有见过父亲。在学校里,没人跟我玩,没人跟我说话。我年纪小小就知道了忧愁,但却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我从母亲和叔叔的谈话中隐约知道,父亲是一个太讲义气的人,义气用事到为领导顶罪。但他的义气最终却都没了名目。这个双鱼座的男人总是把现实想得太过诗意,“出来”以后回到厂里,他才醒悟,他不是英雄,在别人眼中他已是个不可信任的人。
父亲似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喝酒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时父亲喝的是闷酒。停薪留职离开工厂,靠什么养这一大家人?父亲学会了弹棉被,跟着一个表兄走村串户。不知走了多少个村庄,我只记得那时的父亲变黑了,又变白了,黑的是脸膛,白的是他衣服、头发上仿佛永远都洗不掉的细细的棉絮。但父亲的运气渐渐来了,他卖水果,进山里收山货,与人合伙开矿,在生意场上打滚摸爬,失败过,但他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后来他找关系倒车皮,开始挣到一些“大钱”。我们那个县城是广西有名的煤炭之乡,县里的有钱人大都是煤老板。父亲用他几年间倒卖车皮的钱也开了个煤矿,成为一个小煤老板。富起来的父亲哪堪锦衣夜行,他又是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人,于是天天请客吃饭,先是在家里请,后来就上饭店请。这也罢了,他却不知何时起开始跟人打大字牌,常常夜不归宿,若半夜回家,总会跟母亲吵架,他拿了钱摔门而去。
乡下的房子建好后,父亲用所剩资金顶下了一个小石灰厂。钱不赌了,酒继续喝。但在这些乡村的酒桌上,他却受到了意想不到或许也是意料之中的侮辱。那天已是晚上十点,一盏一百瓦的白织灯照耀着大院,飞蛾撞了一晚上灯泡都倦了,父亲还在跟村人兴致勃勃地猜拳。母亲一直在唠叨,终于忍不住,大声叫他们别喝了,吵到孩子睡觉。邻居国文叔正喝在兴头上,育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的他,不怀好意地笑着对母亲说:“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在这里吼什么!”父亲大喝一声,斥责他这是什么话。国文叔一生都在农村,农闲时到外面做点小工,家中虽贫,但觉得有儿子就是他作为男人的面子,于是借着酒意也喊,“你有钱又有什么了不起,连个儿子都没有!”父亲把饭桌一掀,动起手来,一时间两人拳脚相向,众人忙拉扯相劝。我听到吵嚷出来看时,只见父亲被打得眼珠掉出眼眶,犹在大声叫骂。我心惊胆战地看他用手把眼珠塞进眼眶,一声不吭捂着血淋淋的眼睛上医院。
我家前院从此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不在家里请客喝酒了,但他到别人家里喝。喝醉了一路骂着回家,母亲远远听到了,就跑到别人家里躲藏。父亲骂的是母亲,骂她杀了他的儿子,断了他家的后。原来计划生育开始实施那年,母亲正怀着第三胎,她老老实实去打掉已经六七个月大的胎儿,也没跟父亲说一声。好事的医生后来跟父亲说,流掉的那个是个男孩。父亲从前只是心痛、可惜,但国文叔的话伤了他的自尊,更唤醒了他心中的魔鬼。自此一喝醉就旧事重提,跟母亲不罢不休。
但没有儿子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于是他就把我当成他的儿子。我打算结婚的时候问他的意见,他最在意的两条是:愿不愿意上门?同不同意将来的孩子随母姓?大女儿的爸爸当时什么条件都同意,到孩子出生的时候却反悔了,他给孩子办出生证、户口本上的名字仍用了自己的“江”姓。父亲很气愤,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能做到的,是给孩子另取了一个随他姓的名字,如今家乡人都称呼女儿“潘晓语”,搞得女儿有段时间很糊涂。另外,他要晓语用仫佬话叫他“公”,不准叫“外公”。同样,晓语叫我母亲“玻啊”(仫佬话“奶奶”)。这样的叫法让孩子们疑惑,特别是小女儿果儿出生后,两姐妹对家人的称呼都不一样,乱成一团。
我对父亲这样的做法不支持也不反对。我本来以为母亲对此是反感的,父亲生前,母亲无论怎么跟父亲吵,嘴都是硬的,一直坚持说男女都一样。可父亲去世后,她却成为父亲这一“方针”最坚定的贯彻者,不仅不准晓语叫她外婆,也不准果儿叫她外婆。后来我才发现,她忌讳的是“外”字,无关“重男轻女”,而是觉得“外”字不够亲,有种疏远感。
晓语不到两岁我就跟她父亲离了婚,父母于是来到北海帮我带孩子。父亲对孩子极有耐心,晓语幼儿园举行运动会,她大胆报名参加跳绳比赛,可她连怎么摇绳都不会,每天父亲接她放学后,就在客厅里教她跳绳,为她一点点的进步喝彩。晓语有时偷懒不肯练习,他去小区旁的小超市买回几颗棒棒糖、一两盒冰激凌,骗她继续跳。晓语后来在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他比孩子还要开心,还对孩子说:成功的道路,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的道路。这件事不仅让孩子受益匪浅,也让我从中得到感悟。
父亲来到北海后像变了个人。他和母亲每天早早去市场,买回许多便宜的鱼虾螃蟹,用水一煮就可以上桌了。父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餐桌前,一日三餐都少不了小酌一杯,一杯三两,即使常常又加半杯,母亲也不多说,因为相较于他在老家的喝法,已经是太斯文不过了。每天中午,父亲常常会给母亲读我带回来的报纸,那些社会新闻他念得眉飞色舞,有时还配上动作。母亲在一旁安静地笑,不像我觉得他表演太过。午睡起来,我去上班,他和母亲在家看看电视,等到四五点钟,就去接晓语放学。他最受不了北海的夏天,动一动就大汗淋漓,一天要冲几次冷水澡。但北海的夜也常有凉风习习的时候,他会下楼去找门卫老苏,下一晚上象棋。
为了方便父亲接送晓语上幼兒园,我给父亲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父亲用这车,不仅送晓语上学,送母亲去买菜,还接送我去加夜班。那时这也算是单位一景吧,区别于同事的男友、丈夫接送。我坐在电脑前编写稿件,父亲坐在办公室的木沙发上,水也不喝一口,就看着报纸静静地等我几个小时。我像孩子一样依赖着父亲,连上班都要他送我、接我。以前我们单位会给职工送生日蛋糕,自己拿着票到离单位挺远的蛋糕店领取。那天正是我29岁生日,晚饭后父亲骑着电动车,搭着我和晓语一起去四川路拿蛋糕。一路霓虹闪烁,春风拂面,我们像出游一样在车流中穿梭,父亲不停地说着笑话,逗得我和晓语咯咯不停。其实那些笑话是我从小就听他说过的,在女儿的笑声中,仿佛昨日重现,我似又回到小时候,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搭我回乡下看爷爷的情景。时光一眨眼就让我们变了模样,眼前的父亲发福了,白发也日夜生长。然而,总有一些东西沉淀在我们心底,从来没有变过……
这样波澜不惊的日子成为我一生中最温馨难舍的回忆。以至数年后父亲去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上班,每次上街买东西,都禁不住一路哭着回家。办公室里,街头的人流中,我总会看到父亲的身影,看到他的笑脸……亲人不在了,要经过多么久的痛苦我们才肯接受才肯承认?而当这种锐痛渐渐减轻,那份对亲人的愧疚又像一把钝刀子似的夜夜划割着你的心,你真希望时光可以回头,你一定要待他好一点再好一点。然而,太晚了,只有痛,沉沉的痛……
是的,当年若我选择另一条路,父亲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那时我虽常常觉得,就是这样,陪着父母,守着女儿,我也能幸福地过完这一生,但人生的际遇谁也无法预料,我的第二段婚姻在后来的几年粉墨登场,我住到了婆家,晓语跟随她父亲生活,而父母又回到了老家乡下。我盘算着过两年再把父母接来,再把晓语接回来,我们一大家人再在一起生活。
然而父亲回到乡下,又开始日夜喝酒,又开始与母亲吵架打架。当他被发现患上肝癌时已是晚期,医生说,没救了,最多还能活三个月。我那时刚怀上果儿,听到这个消息感觉天都要塌了——在此之前,我觉得父亲会一直健康地活着,只要他在,我就是可以依靠他的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也会降临在他身上,我总觉得应该等到很久很久以后,等到我老了以后。我哭了一个晚上,怨自己怎么不早些发现父亲的病,怪自己当初不该让他和母亲回乡生活。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怀着身孕,几次千里奔波,看着父亲的痛,偷偷流泪,又擦干。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多想坐在他床边陪着他,一直陪着他。那个曾经整天叨唠着要减肥的父亲,那个在酒局上吆喝猜码自吹为“天下第一拳”的父亲,如今已经瘦小得只剩下包着骨头的皮囊。他那么无力地躺在床上,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失去了。那些天,我躲到父亲房间的窗后,让自己哭出声来,我受不了这死亡逼近的一幕幕。几个月前,我还在筹划着为父亲办六十大寿的宴席,还在打算等果儿出世再接他和母亲一起去北海——父亲也想去北海,他买了双新皮鞋,一直舍不得穿,说要等到北海再穿……
那几天,医院不肯收治他,说还是准备后事吧。我不相信,我仍盼着奇迹。我通过以前的同事从医院拉回氧气筒,给父亲输氧;父亲连一口奶都吞不下了,我也不甘心,叫老同事拿药水来给他输液……我知道,父亲他不想死,他那么想活,想和我们在一起。肝癌那么痛,他从没有吭声,再没有胃口,他也要强迫自己吃,他曾对我说:“我知道如果我不吃,我就马上完了,只要能吃,还有希望。”他求生的愿望那么强烈,以至于觉得我们给他找的中医没什么用,而听信一个亲戚吹的江湖骗子,要我们去那里拿药。我们都认为,如果不是这药,他或许还会多活几个月甚至还要久。
多年前,父亲去体检发现肝硬化时医生就告诫他少喝酒甚至不要喝酒。可是父亲说:“不喝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一边大口饮酒,一边大口喝中药。住进医院时他后悔了:“再也不喝酒了,给我五百万也不喝了。”上天却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他了,他再坚强,也强不过死神。对于我的做法,七六叔说,你是在延长你父亲的痛苦,还是让他少受些苦让他快些走吧。他是不理解我父亲啊。我明白,我知道,父亲他不怕痛,一点都不怕,他是眼睛掉出眼眶还能自己捂着走路上医院的人。他只怕死,怕得要命,他从没想过死亡来得这么快。
而我只能尽力去帮他延长他的生命。那天黄昏,父亲在他阴暗的屋里气若游丝,院子里他种下的那棵枇杷却生机勃勃,结了满树鲜黄的果实,夕阳照进院里,树上金灿灿的,像镀了金。夜幕降临,一切归为黑暗,房间里,父亲的呼吸急促起来,又为一口气吸不上来而虚弱地挣扎,喉咙中发出可怕的声音。我大哭着抚摸父亲的额头:“爸,我们已经尽力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那一刻,我在自己的哭声中看到了死神的降临——他是聋子,他是瞎子,听不到哭声,也看不见悲哀。
妹妹也跟着我一起大哭,她也跟父亲说话,可是我听不到了。母亲、姑姑、叔叔、叔娘,还有三哥三姐,听到我俩的哭声都跑进来,他们要我出去,说孕妇不能呆在房里,否则会挡住亡灵的眼睛,使他看不到路。我不知道父亲的亡灵离开那具让他倍受折磨的肉身时,他向屋里的亲人告别时,他看到屋外站在枇杷树下的女儿了吗?他到底是走了,没有看我一眼,没有给我一句话。
那是2008年6月8日,正是枇杷成熟时。那还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棵树的果实,真的好甜,父亲没有吹牛。记得这棵枇杷是母亲从县苗圃买回来的,父亲挖坑把它种下,但它开始结果的那年,我已离家在外,此后虽然每年清明回家,但却不是它的果期。十载光阴,年年错过,谁料到在父亲去世的这个夏天却遇上了呢?人入土化泥,树郁郁地生长,活着的人哭过以后又继续自己的生活,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又好像一切都变了样。
责任编辑 孙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