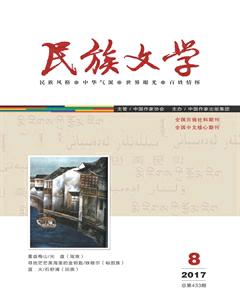亲亲羊羔
马凤鸣
冬季的西海固粗粝硬朗,风中无数寒冷的刀子,不厌其烦地削切着人的脸和手。
老母羊咬住草根,刺啦啦地拔出,飞起来的土遮蔽了它的眼睛,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无限疲惫。这群羊大部分是它的后代。记得父亲当年抱回来时瘦小虚弱,母亲用面汤把它喂活,渐渐长大,毛色洁白纯净,常常跟在母亲的身后,像个拖油瓶,直到有了羊羔才安静下来。
一群羊生生不息。
这个奶奶级别的母羊今年意外怀孕。为了照顾它,母亲傍晚特意端一点面汤给它,把它留在羊圈里喂,但它叫唤个不停,只得跟着羊群上山。嶙峋的屁股落在羊群的后面,分外显眼。
西边山顶上的云层被太阳的余光潦草地照射着,渐渐披上一层淡淡的土黄,最后暗下去,天空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悄悄涂抹着,最后一点儿余晖也被毫不留情地一把抓走了。
暮色逐渐深沉。
清真寺里传来了嘹亮的唤礼声。
那些节奏舒缓、错落有致的呼唤声,在纵横交错的沟壑和静默起伏的峁梁上依次传递,浓烈抒情的咏叹调不断叩问着大地的胸膛和人的心灵。
我凝望着灰色天幕下神情呆滞的村庄,一股蓝烟从日渐苍老的烟囱里钻出来,遇到迅疾的风,呆了一下,仓皇地闪了几闪,逃遁得不见踪影。
母亲正准备晚饭。
羊群在羝羊的带领下急躁躁地往回奔。母羊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圈里的小羊羔,宽广深情的叫声此起彼伏,小羊羔用细小湿润的咩咩声回应着。
老母羊明显体力不支,走走停停,喘口粗氣又往前走,哀婉的眼神让人心里一紧,恐怕要生了。我摸了摸羊的奶头,好像熟透的草莓,轻轻一捏溢出一点儿乳汁。
只能半抱半推着母羊,一步一步往回走,羊走不动了,卧在地上,抱着羊头拉起来,又从羊的胯子上抬着。歇缓了几起子,磕磕绊绊地总算走到了家门口。羊圈里响起吧唧吧唧的吃奶声,羊羔用力顶着母羊的胯下,母羊的后腿被顶得离开了地面,依然疼爱地嗅着羊羔的尾巴,亲切美妙地呢喃着,好像离开了一个世纪才艰难地团聚在一起。
老母羊卧在窑洞里,无力地抬起头看着周围。母亲抱了一抱麦草铺在它的身下,又摸了一下它的头,拍拍它的屁股,它知感地叫了一声。
天的脸色越来越沉重。
吃饭的时候,狗盯着人看的样子真让人难受。把半个洋芋扔过去,它张嘴在空中接住,异常欢喜地呜咽着。猫不高兴了,四只爪子撑住,腰尽力弓成个半圆,嘴里呜里哇啦地吼叫着发威,狗轻蔑冷峻地看着猫虚张声势的表演。
风停了,毫无征兆地缓下了。大地上的一切都匍匐在黑夜无比沉重的脚下。
窗外传来一种细碎深切而又神秘莫测的沙沙声。在细微的亮色中,勉强看到一片隐隐约约的白悄悄铺在院子里。下雪了!雪花落在地上,轻轻地触摸着焦躁的大地。
下雪的夜静谧而神秘。
今晚父亲不在,母亲要独自面对下羔的老母羊。她已经在羊圈里守了多时,可能是人的干扰,老母羊迟迟没有下羔。
母亲刚从羊圈回来在炕上暖了暖,隐约听到擦着雪花飞来的叫声,她迅疾地打开手电,身后是一串慌乱得不成样子的脚印。来到后院高大宽深的窑洞中,羊圈里一阵骚动和不安,腥臊的气息扑面而来。母亲哆哆嗦嗦地打开羊圈的门,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像暗夜里游离的灯泡。
老母羊在麦草上跌绊着,不时扭过头无助地看着屁股后面,这咫尺天涯的距离使它无可奈何。麦草上洒落着鲜红的血,就像开在雪花中的梅花,在雪白的光中冷艳夺目。
母亲结结巴巴地嘱咐我抱一捆麦草,“嚓”地划根火柴点燃,一股蓝烟腾起,火苗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红光照亮了黑暗幽深的窑洞。几只羊羔从母羊身边站起来,好奇地看着老母羊,又嗅着麦草燃烧后散发的麦香,火光一闪,惊慌地回到母亲身旁。寒冷的窑洞暖融融地荡漾着一种十分温馨的画面。
老母羊逐渐安静下来,两只眼睛有气无力地紧闭着。母亲将一只手放在母羊头上盖住眼睛,另一只手放在母羊肚子上,轻柔地向后慢慢捋过去,一次又一次反复着,母羊的肚子随着她的手一张一弛,一次次地用力,一次次地收缩。
我紧张地喊了一声,“娘,出来了。”母亲一看忽地出了一头汗——真主啊!羊蹄子先出来了。
母亲用手制止了我的乱喊,握住滑腻湿润的后腿,轻轻地往后拽,母羊疼得一哆嗦,她吓得放了手。这是典型的倒产,生死攸关,大多数的母羊生不下来,羊羔卡在产道里,母子皆亡。以前,母羊下羊羔,都是父亲熟练地帮助母羊,十有八九都会顺利地保全母子。那时候,母亲只是站在旁边捏着手电,神情紧张地看着生命呱呱坠地的奇迹逐步呈现。
现在,只有母亲能帮助这只母羊了。
母亲将手按在心口上,咚咚的心跳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她强迫自己静下来,撩开湿漉漉的头发,用前襟擦干冒着热气的脸,蹲下身子,按住母羊的肚子,小心翼翼地揉搓,小心翼翼地向后捋。老母羊努力抬起头来,尽力看着屁股后面不可预知的未来。母亲又握住羊羔的后腿,轻轻地拉,随着母羊的用力,羊羔的身体慢慢往外走。这一过程进行得惊心动魄。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用手揉搓着母羊的肚子,向后捋过去。老母羊拼了命地鼓劲,扑哗哗,噗——软囊囊的羊羔掉在地上,羊羔抽动了一下,再也没有声气。老母羊连抬起头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母亲连忙用手抠掉羊羔鼻子和嘴巴上粘稠的液体,倒提着腿,在后背上轻轻拍着,又在肚子上轻轻地拍,“咩——”细弱颤抖的叫声穿透夜空,惊天动地地回荡在朴素坚强的窑洞里。
安拉乎——母亲长出了一口气。
羊羔好像把母羊叫醒了,它吃力地抬了一下头,母亲赶紧把羊羔放在它的嘴跟前,老母羊尽力舔着羊羔,舔一会儿缓一下又继续舔。它的舌头依然光滑湿润,好像少女柔弱无骨的手,千变万化,伸缩自如。先从头上舔,耳朵、眼睛、鼻子、嘴,那么仔细亲切,那么专注深情。母亲把羊羔放在母羊肚子底下,把嘴按在乳头上,羊羔不张嘴,母亲用手指蘸一点乳汁,用大拇指和食指撬开羊羔的嘴唇,抹在它的舌头上,羊羔的嘴动了动,母亲赶紧把母羊的乳头塞到羊羔的嘴里,一点儿白色的乳汁从嘴角流出来,它终于吃上了母乳,这是能否活下来的关键。老母羊吃力地回过头,舔几下,又躺下来休息,挣扎着不断地舔着羊羔,毫不嫌弃地把屁股上粘着的土和草的碎屑统统舔净,羊羔身上的毛色渐渐鲜亮起来,在火光的温柔中好像一团簇新的棉花散发着月里娃特有的奶香。
羊羔卷缩在火堆旁,瘦小赢弱,烤了一会儿,它想站起来,挣扎了几下没有成功。母亲又把羊羔放在老母羊的乳头上,吃了一会儿,母羊又挣扎着重新舔了一遍。
窑洞里拥挤、寒冷,母亲既担心母羊,又担心羊羔。她给母羊身旁围了些麦草,让我回去睡觉,独自守在母羊的身旁。
我迷迷糊糊听见母亲进进出出了半晚上。被羊羔细细的叫声吵醒,睁开眼,天已经大亮了,羊羔卧在被子面下,两只小巧的耳朵时不时动一下,间或细细地叫一声,稚嫩的叫声使人心里无限柔软起来,忍不住把脸贴在它的毛上,一股奇异的奶香扑面而来。它有两个黑眼圈,耳朵上也调皮地点缀着一点黑,肚子上点缀着一抹黑色。这使它看起来不那么单调了。
母亲靠在被褥上,神情疲惫至极,不断地叹气。原来母羊已经死去,在它贡献了青春,年轻的朝气和逐渐壮大的羊群后,又贡献了生命。可怜的羊羔一出生就成了耶提目(孤儿)。
母亲在梨树下挖了个坑,将母羊埋在那里。按照以前的惯例,自死的生灵,因少了那一道刀口,就送给邻村的汉民,但母亲舍不得劳苦功高的母羊,她做了一件违背乡俗的事,心里既难过又内疚。
羊羔大概是饿了,咩咩地叫着,又挣扎着站起来,站不稳跌倒了,我好奇地看看它的腿,原来是个瘸子,前腿上膝盖肿大,不能弯曲。它的这条腿一直在半空中吊着,不能落地,这使它看起来有些滑稽。
孽障(可怜)得很嘛!刚生下来就成了耶提目。母亲难受地說。
她轻轻地抚摸着羊羔的头使它安静下来,羊羔把嘴拱在她的胸前依偎着。把她当做母亲了,她的身上有母羊的味道。
我拉来一只下了羊羔的母羊,母亲把那只可怜的羊羔放在母羊的肚子底下,母羊又是叫又是踢,把我顶了个人仰马翻,母亲只得拉住,我抱着羊羔,把嘴按在乳头上,它吧唧吧唧吃得香甜无比,吃得滋味绵长。
下午又拉着其他母羊给它喂奶。
夜里,我被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母亲点亮了煤油灯,正用奶瓶给羊羔喂奶,瓶里装着白色的麦乳精,羊羔吃几口就吐出奶嘴,不失时机地叫一声,再好的麦乳精也没有母乳好。
早晨,天气异常寒冷,母亲抱着羊羔又来到圈里,母羊惊慌地跑开,唯恐躲之不及。以前它们见母亲来,异常兴奋地咩咩叫着,喝着母亲涮的面汤。现在,母亲的手掌上一把黄灿灿的玉米异常诱人地等在那,往地上丢几颗,被讨厌的羝羊抢走了;又丢几颗被淘气的羊羔吃了,母羊犹犹豫豫地低下头嗅着,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一只母羊的后腿,它拼命地踢打,母亲把它的一只腿抓住,才安稳下来,将羊羔放在母羊的嘴跟前让它嗅嗅,把母羊的奶汁涂抹在羊羔身上,母羊只哺育自己的孩子,靠的是灵敏的嗅觉和母子相依的味道。羊羔显然饿坏了,吧唧吧唧的吃奶声响彻在清冷的早晨。
现在,给羊羔喂奶成了头等大事,父亲笨手笨脚,大多是母亲和我给羊羔喂奶。早中晚各一次,母亲每次都把母羊的奶汁涂抹在羊羔身上,后来她才明白,要专门涂抹一只母羊的奶汁才管用,但母羊灵性得很,好多母羊闻一闻就走开,只有那个今年刚下羔的白头羊例外,它正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时被玉米迷住,悄悄地把羊羔放在肚子底下,羊羔激动地呢喃着,吃奶的样子就像贪吃的孩子,声音响亮,嘴角都溢出来了。如此反复,白头羊也糊涂了,反倒把亲生的孩子疏远了,母亲又不得不把乳汁涂抹在它孩子的身上。
日子细润而漫长,跛羊羔长高了一些,小巧玲珑的鼻子,洁净幽深的眼睛配上一圈黑色别致的眼圈,再加肚子上随意点缀的黑点,使它更加惹人怜爱。
羊羔吃完后,睁着黑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用舌头舔着手,把指头当做奶嘴,弄得人心里痒痒的。它静静卧在炕上,一会儿咩咩叫一声,让人的心里蓄满了暖暖的温情。
太阳出来了,院子里亮堂堂的,羊也从窑里出来吃草,毛色洁白的羊羔夹杂在羊群里,像朵朵洁白的云。
母亲涮了一盆子面汤让母羊喝,只有做了母亲的羊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父亲拉住奶水足的母羊,我把羊羔放在母羊的肚子底下,它闻了闻,不吃,把奶头塞进嘴里,又吐出来。父亲就有些焦躁了,说干脆送人算了,爱吃不吃!
傍晚,父亲拉住另一只下了羔的母羊给它喂奶。但羊羔倔强地就是不吃,气得父亲差点儿踢了它一脚。母亲一把夺过羊羔,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她把那只白头母羊拉来,把乳汁涂在羊羔的嘴上,羊羔一下子噙住奶头,幸福地呢喃着,抽抽噎噎的,好像找到了亲娘。吃饱了奶的羊羔一下子就有了精神,在地上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勉强站住,小尾巴抽象地摇来摇去,黑葡萄一样的眼睛把人的心照得亮亮的。
它的毛柔软得像绸缎,把脸贴上去就嗅到婴儿身上那种好闻的奶香。
把羊羔放到白头母羊跟前,母羊抬起头思索着,犹豫一下就离开了。羊羔不知所措,跌跌绊绊地在后面跟着,异常可怜地叫着,让人忍不住冲过去一把抱起来亲一下。和它同时出生的小羊羔已经活蹦乱跳。它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其他的羊羔围过来,像看一只怪物一样看着它,有的母羊过来用头顶一下。
天气变好了,瓦蓝的天空异常干净,风小了许多,在房檐下铺一块小小的垫子,把羊羔放到上面,微风吹来,白色的毛翻起小小的波浪,淡淡的奶香飘在空气中。过了几天,离开了热炕的羊羔还是吃着白头母羊的奶,一些比它大一些的羊羔在羊圈里撒欢子,它跛着腿,跟在后面,也想跳一下,但一跳就站不稳,险些跌倒,它一叫,母亲扎着面手急忙跑到羊圈看一下,又嘱咐我单另铺些麦草,羊羔乖乖卧在上面。
我坐在旁边,抚摸着它,用手指绞着它的毛。它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静静看着你,看的人心里升起一股洁净无瑕的气息。
虽然白头的母羊给羊羔喂过多次奶,但它还是不认,亲生孩子的味道已经深入骨髓。
羊羔继续吃着百家饭,一天到晚给它喂奶也使我心烦。和其他的羊羔相比,它显得瘦小。那些母羊见了它没有一个亲昵的,就连不谙世事的羊羔也欺负它,羊群生存的法则和人一样。
唯独母亲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它。有一次,狗把它吓了个趔趄,母亲拿着笤帚把狗追了老远,狗晚上也不敢回家,在大门道里蹲着,一定是母亲凶狠的样子吓着了它。
这只跛了一条腿的羊羔在母亲的无限关爱中渐渐长大,白色的毛日渐蓬松起来,常被微风掀起一层层小波纹。
日子慢慢地消融,早上或晚上都要专门喂羊。在槽里拌一些草,撒一些麦麸或者油渣,或者把骑在庄窠墙上的洋芋秸秆扔下来。羊羔们也挤在一起,把头伸进槽里,像调皮的孩子在捣乱。
羊羔们一个月大的时候和大羊隔开喂。把砸碎的油渣和粉碎的豆子倒在槽里,羊羔们争抢着吃起来。跛羊羔也和伙伴们一起吃料。吃了一段时间的羊乳后,它茁壮了许多,毛色洁白,眼睛愈发明亮。我抓了一把油渣放到它的嘴边,它迟疑了一下,嘴皮上下抖动着吃光了。我倒料的时候,它跛着一条腿,呱嗒呱嗒地跟在我身后,把头塞在簸箕里,连底里的渣渣都舔了,真像个饿死鬼!
跛羊羔知道我也稀罕它,一个手势它会呱嗒走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打开手掌,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叫一声,吃得咯嘣咯嘣响。吃完后,偏着头,葡萄一样的黑眼睛认真地看着我,深得把人能掉进去。我摸一下它的头,它摇着尾巴,在眼前卧下来,一会儿就将头枕在前腿上睡着了。它多么相信我!
西海固的春天总是脚步缓慢,其他地方都草长莺飞了,这里的风才暖和起来,向阳的山坡上青草顶开了土壤,欢喜地相互问候着,母羊要上山放牧,羊羔还小,不能跟着大羊满山跑,所以,在羊圈门口要将羊羔拦下来。
没有了大羊的圈里一下子空旷了许多,羊羔们有些惊慌失措,细细的叫声此起彼伏。跛羊羔的叫声更大,而且把尾音拖得长长的,像男人唱出的花儿,颤悠悠地传出很远。
原来它是一只羝羊。
绵羊羔长到三四个月时,毛长二寸,顶端打着旋,拉开后细如丝线,放开后又卷到一块,而且毛色柔润,像绸缎,提起来抖一下,就像润雪飞舞,平湖荡月,这就是宁夏著名的二毛皮。公羊羔在最值钱的时候被卖了,贴补家里的用度和我们的学费,母羊羔留下来继续喂养,只有非常强壮的公羊羔才留作种羊。
除了油渣和麦麸,还要喂青储饲料。青储草是去年的苜蓿,这些苜蓿长得茂盛的时候,拦腰割断捆成小捆立在地上,风吹日晒得差不多了,拉回来摞在墙上。在羊圈里扫一块净地,把苜蓿草撒在上面,羊羔们聚拢而来。
跛羊羔也和伙伴们一块吃草料,它跛着一条腿,行动慢一些,好的位置被强壮的公羊羔占据,它只能在边缘上吃踩踏过的,就连那些母羊羔也用头顶它,它一躲跌倒了,挣扎着爬起来,一脸的迷茫,让人的心里充满了怜爱,索性轰开其他羊羔,让它一个吃。
如果把食物随便扔给牛羊,会招来母亲的呵斥,但只要给跛羊羔,母亲也不追究。跛羊羔的个头明显不如其他的羊羔,肚子上的黑点使它在众多白色的棉花团里显得卓尔不群。
傍晚,母羊们像疯了一样跑回家,老远就发出急不可待的呼唤声,宽广深情的叫声此起披伏,羊羔们在羊圈里用细细的童声焦急地应承着。母羊回来后,羊羔们一下子扑过去,双膝跪倒在地,头用力在腹下拱着,母羊的后胯都被顶了起来。跛羊羔焦急地在羊圈门前叫唤,就像失去母亲的孩子。让人忍不住冲进去拉住一只母羊让它饱食一顿。它使劲顶着母羊的后胯,母羊跳弹着,挣扎着,放开后趁人不注意,就掉过头狠狠顶它一下。
那些提前出生的羊羔身上的毛有两寸长了。尤其是那些有着小羊角的公羊羔,毛不是直溜溜的,好像女人烫的头发。毛尖拧在一起的毛是最美的,这是最好的二毛皮。不仅柔软丰匀,毛穗洁白,质地细润,轻柔暖和,而且非常轻便。
更为可贵的是柔而长的毛穗,弯曲柔折,如起伏的波浪,若将皮板倒提,洁白的毛穗,顺次自然下垂,宛如冰锥叠撞倾倒,平户涟漪荡漾;若轻抖,仿佛是玉簪缤落,梨花纷飞,更觉轻盈动人。
二毛皮不仅用来制作皮衣,还用来制作高档服饰的镶边,色调明快,典雅素致,别具风韵。
如果是公羊羔,刚生下来,它的命运就已经前定了。
只有头大、腿长、后胯宽的公羊羔被留作种羊,其他的大多被卖掉,而母羊羔留下来生生不息,来年产下更多的毛色柔软的二毛皮。
二毛皮成形的时候,羊圈里回荡着凄厉嘶哑的呼唤声,母羊的眼睛让人心碎。母亲总是流泪,父亲和羊贩子在衣襟底下神秘地讨论价格。羊羔拉走了,失去羊羔的母羊把头尽力伸出栅栏,深情悲鸣的呼唤声彻夜不绝,好像巨大的灾难来临时恐怖而绝望的悲声。第二天,母羊的嗓子都哑了,头一直在栅栏门里伸着,眼睛里全是绝望的血丝。
它们的孩子没了。
跛羊羔侥幸留下来,因为它发育得比较迟,羊贩子嫌弹,给的钱少。
羊圈里一下子空旷了许多。那些失去羊羔的母羊不断嗅着跛羊羔,在它身上搜寻孩子的影子。
白头母羊的羊羔也卖了。母亲不失时机地拉住白头母羊,把跛羊羔放在肚子底下,它迟疑着噙住乳头,用力吮吸着,找到了娘一样地呢喃着。
第二天,它一瘸一拐地跟在白头羊的后面,那个留作种羊的公羊羔跑过来又要欺负它,被白头羊顶回去,愣了半天神!
母亲笑了。
跛羊羔长得很快,个头差不多赶上了留下的公羊羔。毛尖打着旋,毛色洁白柔软,手摸过绸缎般光滑,正是卖个好价钱的时候,再过一段时间,毛就长老了。
父亲惦记着它。母亲却极力反对。
母亲说,它是个耶提目嘛!
父亲说,再不卖,就卖不上好价了!
父亲的意思是宰了吃肉,皮子能卖个好价钱。这是母亲万万不能接受的。
父亲找来了羊贩子。一辆吱吱乱叫的自行车,后座的偏面吊着装羊羔的背篼。羊贩子一身腥臊气,眼睛刀子一样在羊羔身上掠过。
父亲说,这是最好的二毛皮,你看毛唦!
羊贩子说,好啥呢!还跛着呢,肚子上有黑毛,值不了几个钱。老马你咋哄人呢?
父亲好说歹说,羊贩子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跛羊羔,还嫌弃着皮子不好,折了本了。
羊羔被捆住三个蹄子,装在背篼里。它的头在背篼外尽力擎着,眼睛异常惊恐,悲鸣的叫声伴随着叮当响的車铃声断断续续地回响在山路上。
白头母羊把头伸出栅栏外,一直悲鸣着,其他母羊也不断地回应着,悲怆的呼唤响彻了几夜。
母亲继续喂羊,时不时地停下发呆。
渐渐的我明白:我读的每一页书,用过的每一张纸,每只笔都浸透着二毛羊羔的鲜血!山上的青草、地里的苜蓿草、院里的树叶和井里的水以自己的形式成就了羊羔的血肉,羊羔的鲜血化作文字在我的笔下不绝如缕地流淌——我迈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母亲和羊羔深情的眼神。
我抚摸着橱窗里柔软光滑的二毛皮,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放着母亲第一次看到二毛皮的情景:她只看了一眼就扭过头去,脚步踉跄地出去了,摇晃的背影,满头的白发,佝偻的腰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