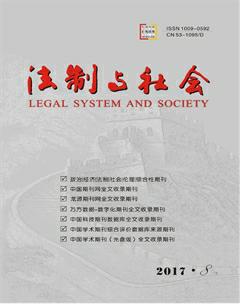先秦时期礼刑关系演进之分析
摘 要 夏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的认知水平的约束,法律形式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奠定了中国初步的混合法法律体系。在这一时期,法的规范形态多样化,是具体的法律规范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礼的规范的综合。多元化的法律形态以及相互作用,构成了先秦时期法律体系的鲜明特色。在这一体系下,法的规范和礼的规范不断融合,成文法和判例法不断作用。
关键词 礼法制度 混合法 礼刑关系
作者简介:苗春刚,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法政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法史。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8.283
在人类法律发展史上,关于法律样式的选择,从终极意义上讲,有制定法和判例法的划分。但从法律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可能是单纯的制定法或是判例法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两种法律样式的综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混合法法系。 正如武树臣所论述的,中国的“混合法”在法律实践活动中表现为成文法(制定法)与判例制度的有机结合, 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 (道德习俗 )相结合。 夏商周时期,礼法制度的发展是一个缓慢成型的时期。
一、礼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夏商
礼作为一种礼节仪式和风俗习惯,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最早与祭祀活动紧密关联,是古人祭神求福的仪式活动。礼(l ),繁体为“禮”。在《说文解字 》中解读为:“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 读与礼同 ”;“豐 , 豆之丰满者也, 从豆象形。”“豆, 食肉器也 。从口象形 ”。 “豊”为“禮”的本字,其甲骨文像在高脚盘(豆)中盛放着玉器以奉神神祇。古人把通灵玉器敬祭神灵以求福,故而,奉神祇之事谓之“禮”。在徐灏注笺《说文解字 》说 :“礼之言履 ,谓履而行之也 。礼之名, 起于事神。”《礼记·礼运》称:“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史记·礼书》也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但中国古代礼的阶级化、国家化则始于夏商。夏礼的內容由于史料的匮乏,无法考证清楚。但在《论语·为政》篇中,有“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的论述,《礼记·礼器》中也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因而可以说明夏朝有礼的规范,并且对商朝的礼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有夏一朝,作为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不仅礼的规范国家化,而且出现了最早的刑事法律规范。礼、刑两种社会规范的出现,为礼刑关系的发展创设了契机。《尚书·甘誓》中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设”,恰恰表明了礼和刑合流的最早的趋向。
殷商时代礼的规范,由于甲骨文资料的整理,可以考据的内容较多。同所有的早期人类一样,殷人非常迷信,大至祭祀、战争,小至疾病、梦幻,都要用甲骨占卜,并将占卜的结果记录在甲骨上。 伴随着祭祀的发展,商朝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祭祀制度。殷商迷信鬼神,重视祭祀,有着特殊的内涵。《礼记·表记》记载: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殷人祭礼,在帝祖合一的时代,祭神就是祭祖,祭祖又是祭天,祭祖、祭天,意味着祈天而永命,让已经到手的王位、社稷永远牢固的保存下去。这就是殷统治者融礼与祭祀为一体的真正用意。 《左传·成公十三年》谓: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表明以祭祀为主要形式的殷礼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确有着规范、训诫的作用。《礼记·曲礼上》说:“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表明殷商通过祭祀占卜的形式进行神明裁判的根本目的在于让老百姓畏法令,实现“以教民侍君”(《国语.周语上》)的目的。
商朝在神权法思想的指引下,进行了较为复杂的立法工作。商代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典、誓、令三种。在这些法律形式中,典是大法,是主要的法律形式,誓、令和其他单行形式则是其补充形式。 商朝初年制定的《汤刑》,又称为“汤之典刑”,作为商朝的基本法律,适用于整个商朝。此外,商朝初年还针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制定了《官刑》,具有针对特定对象专门立法的属性。据文献记载,商朝还有“弃灰之法”的单行法律。 作为商朝法律形式的誓和令,则具有夏朝延续的军法(兵法)的属性。礼刑关系发展到商朝,伴随着奴隶制文明的进步,关系日趋紧密。在礼的统摄下, 商代的刑罚亦表现出细密化、规范化的趋向。
从商朝法律的本质上讲,商代的法律样式是 “任意法”。这里的 “意”是 “神意”和 “人意”( 即统治阶级意志) 的合一。 商朝的法律具有强烈的神权法特色,是和商朝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密切关联的。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更由于统治者刻意运用神权法思想强化对社会的统治,在商朝占卜活动盛行。在祭祀、审判活动中占卜的盛行,为商王朝的决策活动赋予了更多的神秘性,增强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伴随着审判活动的增加,司法官在实践中积累了更多的法律经验,使得对法律的概括能力增强。
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提高,使得审判活动中理性色彩增强,法官更多的运用既有的法律原则判案,减少对占卜活动的依赖,从而实现了“不疑则不必问卜”。
商朝司法活动中法官主动性的提高,使得商朝的法律日益完善,法律原则的增加、司法判例的增多,为商朝的任意法增加了更多的法律限制,从而为西周春秋时期判例法的兴起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礼法制度的完善——西周
西周是推翻了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王朝。周初的统治者从商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从而摆脱了夏商两朝单纯的“天命、天罚”的天道观。天道观的改变,使得周初的统治者一方面在明德、敬德的基础上,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对夏商两朝礼的规范整理补充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巩固奴隶主专制王权的典章制度。由于这一工作主要是在周公旦的主持下完成,后人一般称为“周公治礼”,《左传》中有“先君周公制礼”的记载。
由于周公制禮,既着眼于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又兼顾规范民众的日常行为,因而周礼的内容调整着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个人言行、风俗习惯、礼节仪式等诸方面内容。西周礼的内容,大致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方面内容,这些内容成为维护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继承制度的准则,调整着社会放入政治、经济和家庭关系。《汉书·礼乐志》记载:“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治丧祭之礼具体分为吉礼和祭礼两种形式。吉礼主要调整祭祀内容,在西周包括祭祀上天、祭祀日月、祭祀宗庙社稷、祭祀先祖等十二种形式。凶礼是主要调整丧葬、灾难有关的一系列礼节,要求在办理这些活动时要悲伤、忧思。《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襘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可见,周礼中的凶礼包括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五种形式。宾礼体现尊尊敬上之心,要求在朝聘会见时应当礼貌有礼节,包括春见、夏见、秋见、冬见、时见等八种形式。《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军礼主要用于征伐,要求兴师动众要果毅,包括大师礼(用众)、大军礼(恤众)、大田礼(简众)等五种形式。《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军礼同邦国”。嘉礼主要用于饮宴婚冠、节庆活动方面的礼节仪式,包括饮食、婚冠、宾射礼等六种形式。
周公制礼的内容,首先体现了对夏殷治礼的继承和发展,《论语.八佾》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方面周礼继承了夏商两朝的礼的内容,如对鬼神占卜的祭祀等内容;另一方面周礼针对西周的社会特点,不再把礼的规范限定在祭祀时的礼仪制度,而是更多的调整世俗的社会行为规范,如对宾礼和嘉礼的规定涉及宗法、婚姻等现实的社会关系,体现了西周礼仪既重鬼神、又重人事的特点。对鬼神和人事的共同尊重使得周礼的规范更加成熟。其次,周礼体现了对西周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呼应,增加了“明德、敬德”内容使得礼的内容更具有现实性。德和礼在本源上应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西周统治者在“以殷为鉴”的思想指引下,认识到商纣王暴虐统治导致国亡的教训,强调统治者要修德、敬德,以德治天下,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德和礼的沟通。
西周社会的法制发展,除了礼的规范日益成熟外,也重视与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直接相关的刑律的制定。西周大规模的刑事立法活动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初制定第一部成文刑书《九刑》。《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周有乱政,而坐九刑。”关于《九刑》的具体制定时间和内容,由于刑书已佚失,很难知其详。
第二次是西周穆王时期《吕刑》的制定。《吕刑》制定于西周中期,当时周王朝国库财政空虚、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国力开始衰退,因而《吕刑》在制度设计上便具有了大量的与其时代相呼应的特点,例如赎刑的出现便具有强烈的解决财政亏空的需求。
从整体法律体系上讲,西周的法律样式具有强烈的判例法色彩。其推崇“议事以制, 不为刑辟”。这表明当时的法律仍具有强烈的神秘法色彩。法律的不公开性,使得当时的贵族统治者可以肆意选择已有的判例来为现实的审判活动服务。在这一时期,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制定法规范,但制定法普遍的缺乏体系,更多的是对刑罚的类型的规定。
三、礼刑关系的社会启示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完善而著称,而法律的完善集中表现为多样化的法律形式,这一特点从先秦时期法律的发展中得以体现。在这一时期,既有“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又有法的规范作用,两者相得益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礼刑关系对于古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就当代而言,当今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关注法律完善的同时,同样需要关注道德伦理的积极作用。
注释:
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1997(1).
许慎.说文解字.
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0.
高浣月.夏商西周的礼与刑.中国法律.
胡留元、冯卓慧.夏商周法制史.北京:商务印刷馆.2006.352,54.
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6.
李学功.夏商周三代礼法制度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