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鸡年小说述评
吴平安
百家论坛
晓苏鸡年小说述评
吴平安
鸡年刚过一半,晓苏已在《作家》《天涯》《花城》《钟山》《长江文艺》等各大名刊发表短篇小说8篇,这预示了2017将会成为晓苏小说的一个丰收年。
我跟踪阅读晓苏小说十余载,每当他有新作问世,我都会及时阅读。读了晓苏鸡年已发的八篇小说,我感觉到,作家对中国乡村一隅的跟进式观照仍未停息,对生活的思考和形式的探索仍末停息,对油菜坡这片文学沃土的开掘仍未停息,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饶、更加新鲜、更加深刻的小说“意思”。
“悲喜交集”:写不尽今日农村的人生百态
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究竟该怎样概括?“牧歌”、“田园”的一页大概已经翻过去了,那么像如今经常出现的“沦陷”、“空壳”,是否就足以勾画今天乡村的风景呢?这片风景中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演绎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
读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我忽然联想起有年攀登泉州清源山,面对勒于一块巨石上“悲喜交集”四个大字,恍然间似有所悟来,那是弘一大师的真迹,道尽又道不尽人生的况味。人生于天地之间,百代过客,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无论是就个体、就群体,还是就类的存在而言,应该都是造物赐予的无法逃遁的定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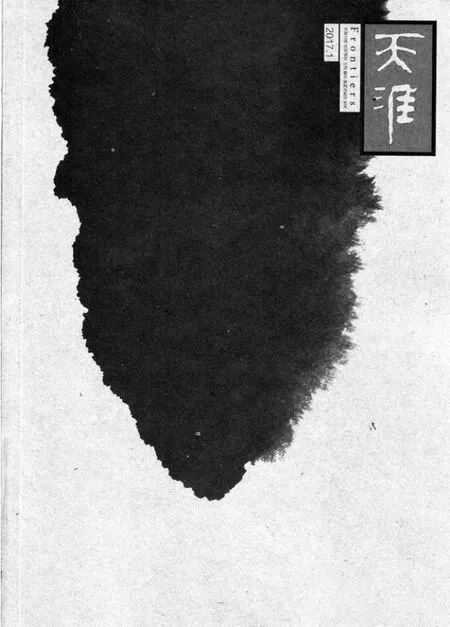
《天涯》2017年第1期
引此联想,并非是说晓苏小说意在谈玄论禅,其所指有二:一是就小说文本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晓苏对当下中国乡村风景的审美把握;二是就读者反应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感受。
且看《推牛》(《天涯》2017年第1期)。一个老农在一辆装有三十八人的客车与一头拦路的老牛相撞的刹那,奋不顾身“推牛”而殒命车下,作为小说的前叙述,以此拉开了一干人物的悲喜剧。这一壮举被主管宣传的镇领导捕捉,旋即打造成舍己救人的英雄,“笨嘴笨舌”,说话“结结巴巴”的儿子作为事发时“正好在场”,“亲眼目睹”了“英雄壮举”的“英雄之子”,一番专人调教,成为口吐莲花的“英模报告团”的主讲。随着宣传力度的层层加大,“英雄”升格为“感动全县十大人物”,伴随英雄事迹的持续发酵,上上下下一干参与其事的人物均沾光获利,各有升迁,“英雄之子”也被任命为副村长。
“当上副村长的那天中午,我爹一回家就进了堂屋,双膝一弯跪在了我爷爷的遗像前,给我爷爷连磕了三个响头。他一边磕一边对我爷爷说,爹,我们家祖坟冒烟了!爹,我当副村长了!爹,我们高家总算有人当官儿了!”“当了副村长之后,我爹就开始反常了,说话让人莫名其妙,做事让人不可思议。他的言行举止,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油菜坡的人,仿佛是一个天外来客。用我妈的话说,他有神经病!我奶奶干脆说,他八成儿是疯了!”
看到这里,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十足的一部农村版的《范进中举》啊,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已深入中国人骨髓血脉中,历千百年而分毫不减,念及此,又不禁悲从中来。然而范进中举之后,得到的实惠是实实在在的,农民范进当上的副村长,不过是因人设岗,“没有任何实权,好比聋子的耳朵,说穿了就是个摆设”,这倒也罢,顶着“英雄之子”光环的副村长,竟被推到风口浪尖,变成一块村民人人想吃一口的唐僧肉,不仅家中钱物被村民以各种名义洗劫一空,连肾脏也被“捐出”以致病入膏肓,无人理睬,直到弥留之际,方才说出事情真相,原来那牛系老农所买,“推牛”不过是保护自家财产的私心而已,为了树典型,博政绩,“上头来人打过招呼的,要我爹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我爹还对上头发过誓,说这事打死他也不会说”。这是晓苏“点式叙事”的又一个精彩呈现:一干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全生发于一个“推牛”的瞬间动作,凭借这个“点”,敷演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荒诞故事。
《两次来客》(《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读者完全可以把这篇小说当作一部喜剧小品来欣赏,它的基调是温情地嘲讽。
勤扒苦做盖起了三层楼的村民金斗,得知表弟赵宽要来油菜坡探望,立即当作头等大事进行了全家总动员,从饭菜、烟酒、餐具到自家衣着,都进行了费心尽力地安排。令人唏嘘的是此举并非出于亲情和厚道,而是意在鸟枪换炮之后的显摆和张扬。然而让金斗始料未及的是,做钢材生意发达了的表弟更是今非昔比,财大气粗,哥俩的见面就变成一场炫富与比阔的较量。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那么顺理成章,也该有“相对富裕”和“绝对富裕”了。如同一种叫“十点半”的牌戏,相对富裕的金斗每出一张牌,都被绝对富裕的赵宽的大牌压下,结果是金斗完败,锐气大折的金斗遂一蹶不振,“巴不得早点死”去,以至于当做药材生意的表哥李帽也前来做客时,金斗不能不心惊胆战。孰知市场风云变幻,阴晴不定,有人一夜暴富,就有人一朝破产,当金斗发现李帽已经潦倒落魄一贫如洗之后,此前炫耀表弟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李帽艳羡不已,此番做客,其实是前来告贷的。金斗在这次比斗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不但慷慨解囊,而且“感到浑身都是劲儿,便直接到地里割油菜籽去了”。

《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
晓苏令人忍俊不住的讲述,揭示了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炫富与仇富。越穷越光荣的荒谬历史终结了,如今是《财富榜》颠倒众生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了,奔小康了,致富了,可是精神的脱贫,却并不像土屋换楼房那么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嘲笑金斗兄弟精神世界的局促,可是反观都市白领对奢侈品牌的追捧,将此作为提升自身品味的标志,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倘若再往远处想想,你看那个西楚霸王,天下未定,便叫唤“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现在时兴的炫富手段是晒在网上诱人围观;魏晋门阀士族中,有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那时候是用铁如意砸红珊瑚,如今的土豪干脆直接烧人民币了。与炫富相生相伴的则是仇富——《两次来客》精彩之处,在这两种心理于金斗身上兼而有之。读到这里,恐怕就不由得叹一声:两千年下来,中国人的财富观,咋就不见有多大长进呢?
梁文道先生在新书《关键词》中,对这种看似对立的心理有深刻的解释:“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如此看来,金斗不正是这样的可怜人吗?
如果要分析晓苏的写作心理,发散性思维应该是特点之一,一类人物(比如光棍汉)、一种社会现象(比如宣传上的弄虚作假)、一个主题(比如高校教师的道德滑坡),甚至是一个字(比如刘富道先生就曾将《花被窝》《花嫂抗旱》《一双绣花鞋》概括为“三花小说”),都可以敷演出一个系列的小说来。以此观之,可以把《看病》(《花城》2017年第2期)和《撒谎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看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一个系列,比起《两次来客》温情的嘲讽来,这“两次看病”的讽刺就要辛辣得多了。

《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晓苏却刻意避开了这个社会热点,他关注的是在两次看病过程中烛照的世道人心,是在商品逻辑主宰下人性的异化。
村民林近山患腿疾行走不便,卖掉年猪,以每天一百一十元劳务费请光棍汉张自榜陪同,花五百元乘李兆祥的黑车,投奔当年村中下乡知青、现任行管局的副局长,赴襄阳看病。有了副局长的关照,林近山看病一路绿灯,张自榜趁势沾光,看了自家的性病,三百多元费用也一并由副局长支付。等候其间,李兆祥为见缝插针多捞外快,将黑车开出拉客,不料因不懂交规且系无证驾驶,被交警队扣留,罚款一千元并拘留七天,副局长派员疏通并代缴罚金,使三人得以返乡。车进自家地盘,李兆祥仰仗妹夫是镇交警队队长,得意忘形喝得酩酊大醉开车赶路,三人为劳务费、租车费又起争执,终于将车翻进深沟,把三人摔成重伤。
《撒谎记》中的农民看病,因为上头无人关照,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我”的儿子摩托醉驾负伤住院治疗,按规定是不能报销医疗费的,在医院院长车前启发下,“撒谎”成打扶贫井负伤,让老实巴交的“我”感激涕零:“车前这个人好。他和我们非亲非故,却能一切为我们着想,这样的好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然而对“好人”是必须表示感谢的,何况合作医疗结账是必须经院长签字的,表达谢意的物品是高档香烟,因为院长“吸的最差的烟,也是五百块钱一条的黄鹤楼”,这是熟悉内情的病友的指点;报销是需要村里出具证明的,而证明也不是白开的,村支书盘存又做笼子让“我”破费了两百元饭钱;证明是需要加盖公章的,而公章却握在书记老婆手中,也是必须打点的。这还没完,眼看诸事停当,村民连赢却借口摩托车碾压了他几十棵油菜秧,以告状“撒谎报销”相要挟,又敲诈了一千元,最后牵走了“我”家唯一的肉猪作抵。围绕一次住院报销,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比起院长的不露声色,支书的启发暗示,无权无势的村民连赢就是赤膊上阵了。连赢和艾蒿夫妇同属最底层的乡民,可是却没有一点惺惺相惜之情。赵弯车祸倒地时,正在现场的连赢冷眼旁观,未见施以援手,只是手机告知赵弯父亲,其时已另有盘算了,这种来自最底层的精神溃败,才是更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鸭绿江》2017年第5期
《妇女主任张开凤》(《鸭绿江》2017年第5期)。这是一幅洋溢着喜剧精神的乡村风俗画,几个女人闹离婚的故事,使通篇充盈着明朗而乐观的情调,令人联想起莎翁喜剧中那些方方面面均高出男人许多的可爱的女性。女主人公张开凤,不但工作能力强,还“像一个时装模特儿”,“又贤慧又孝顺,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小说开端于张开凤受命“密切关注村里的动向”,“把离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免影响“和谐村”建设,并被许诺接任村支书一职。小说的主干情节,是以“一线串珠”手法叙述三个妇女闹离婚,而忠于职守的妇女主任则充当了消防队员,疲于奔命,四处灭火。三个妇女的丈夫,或者懒惰、赌博、败家;或者小肚鸡肠,跟踪盯梢媳妇闹出笑话;或者视媳妇为物件和外人利益交换。全是“两口子也确实有点儿不般配”的婚姻状况。张开凤在“灭火”劝和过程中,不得不现身说法,原来那三个男人的种种劣迹,被其丈夫孙喜九一人占全,且冷漠、自私、吝啬又在三人之上,而堪称人尖的张开凤,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却只能是如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满脑子的大男子主义的孙喜九在屋里可以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甚至故意刁难摆治她。是谁给这位三间土屋里的君王加冕的呢?当然是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国学热持续升温,弘扬传统文化呼声日高的今天,我们似乎无暇分辨和剔除其间裹挟的糟粕,就像昨天无暇分辨和吸收其间的精华而“横扫一切”、“彻底决裂”一样。“在和谐村评选中,离婚是一票否决。上头说了,离婚就意味着家庭不和谐,家庭不和谐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上头”的话音里,分明可以听到封建伦理纲常的余响,而最古老的礼教经一番逻辑推演,又和最当下的社会治理对接起来。令人唏嘘的是,这套高论不仅为“上头”鼓吹,也为“下头”奉行,这里“下头”并非指或不单指村支书王立社之类的基层干部,而是指以肖楚玉娘屋妈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尤其是老一辈人,“你离了婚,我这张老脸没地方搁啊”是句经典道白,它印证了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男女不平等,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均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态是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所谓女权主义理论,就建立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上。中国妇女因为整体上未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女性意识与个体意识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欣喜地看到,现代文明的阳光,也终于照耀到僻处一隅的油菜坡,妇女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再是从一而终了。

《湖南文学》2017年第5期
《推杯换盏》(《作家》2017年第1期)。咋看起来,这是一个寻常故事:包工头王羊勾引了陶贵的媳妇毛英,“看上去一副憨样,实际上精毬得很,比他娘的王八还精”的陶贵,为了从王羊处得到盖房的钱财和钢筋、水泥,采取的策略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装傻”,甚至不惜在王妻寻夫时为之掩护。一待新房落成,怀恨在心的陶贵为了报复夺妻之恨,不仅设计让王妻捉奸而后与之离婚,还放火烧了王羊的老屋,使之居无定所。为了避免公安介入调查纵火案,毛英跟随王羊另投平顶山挖煤,而平顶山的储洞长却很快勾引跑了毛英。
恩怨情仇,尤其是涉及男女关系的爱恨,是文学的永恒题材,想在这方面写出新意,着实不易。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用鄂西北方言土语,采用多元第一人称,把一个原本俗套的故事讲述得妙趣横生,当两个男人为了同一个女人结下冤仇后,却又同时为这个女人带了绿帽子,原来他俩都是受害者,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现在都成了一无所有的光棍汉,互为寇仇的敌对情绪化解了,王羊为夺妻向陶贵道歉,陶贵则对王羊坦白了放火之事,小说在两个难兄难弟尽弃前嫌推杯换盏中结束。这是一篇很能体现晓苏特色的“有意思”的小说,至于“意思”背后的“意义”,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可以人言人殊的空间,就留待读者去填补吧。
《打飞机的傻哥哥》(《湖南文学》2017年第5期)。这是叙述人“我”,我的傻哥哥、地痞杨梆、妓女黑耳几个人的一台戏。在南方打工的“我”千里返乡,是为了按当地习俗,给傻哥哥过四十八岁生日,遇见同在南方某地谋生的妓女黑耳,为了缓解光棍汉傻哥哥的性苦闷,决定花钱请黑耳陪傻哥哥睡一觉。
农村光棍汉是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是晓苏独特的审美发现,而对其性压抑、性苦闷的揭示,则体现了作家的悲悯情绪与人文关怀,晓苏此前已经有《坦白书》、《松油灯》、《为光棍说话》、《送一个光棍上天堂》等等作品,且广受好评,换言之,沿着这条路径走下来,自然轻车熟路,但是会犯一大忌,即自我重复,文学写作的残酷性在于,对一个作家来说,重复自己与重复别人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创造力不足的表现。然而晓苏不过是借用了一条叙事线索,醉翁之意不在酒,兄弟间的手足情深,妓女黑耳的良知善念,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地痞杨梆掺合其间的寻隙滋事,更把这台戏搅动得摇曳生姿,“打飞机”的双关,“花柳树”的隐喻,或浅或深隐藏在文本中,显示着晓苏营构短篇的功力。
《父亲的相好》(《钟山》2017年第3期)。这部短篇在晓苏的小说里颇显另类,甚至在短篇小说体裁中也不多见:它的时间跨度太长,从情窦初开的懵懂岁月写到安详宁静的黄昏暮年,几乎覆盖了男女主人公的一生。或许是因为不合乎教科书设定的美学规范,除了现代白话小说的早期作家偶有涉猎外,一般都不大敢取此章法。然而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优秀的小说,往往就产生在对既定规范的冲撞中。
这是一篇读完让人心生暖意的小说。在“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就像洪水猛兽,一旦暴露就会惊天动地”的年代,这对小学教师因为私情暴露而各受惩处,男的开除回乡务农,女的发配边远学校;光阴流转,岁月不居,虽然其间两人天各一方,见面机会屈指可数,这段深埋各自心底的情愫却并未被时空磨灭阻断,女人爱屋及乌,通过对男人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儿子的热情接待,通过对男人妻子因嫉妒患病的特殊治疗,男人则通过对女人信物的珍藏,彼此恪守了那份珍贵的感情。读毕全篇,方知作者何以要让尺幅短篇横跨三代人了,因为时间是小说里无言的见证人,男人自贬回乡,终其一生都在务农,几十年社会变迁如天地翻覆,两人能白头到老而初心不改,其感情之真挚、之纯净还容怀疑吗?正是这份情感的滋养,使平淡的生活有了滋味,让平凡的生命不再平庸,倘对比当今现世权与物对爱情的高度异化,则无异一遥远童话,小说温暖人心处,也正在这里。至于时间跨度的超长,作者通过叙述视角的精心挑选,即取三代人的中间一代,以女儿的身份,上接老父,下连儿子,再截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便有效化解了时间与篇幅的矛盾,有效调控了叙述的密度。
“出乎意外”:把反转式结局艺术推向极致
“出乎意外的结局”(Surpriseending),是西方评论家对欧·亨利小说形式特征打下的美学印记。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相对“古老”的写作艺术,然而至少就短篇小说而言,这株老树仍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何况即便是枯木,得遇天时,不也还能发出新枝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谓“天时”,即是“慧心”。这种结局艺术面对的挑战,是读者经久积攒的审美疲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反转式结局的基本要求,然而能够将“意料之外”变为“意料之中”的聪明的读者越来越多,作者与读者间的智力竞赛,也就有了朝更精彩处拓展的空间,就像人类对“更高、更快、更强”的极限追求,使固定程式的体育赛事依然精彩纷呈那样。
从这个角度解读晓苏小说,不难看出这种反转式结局,是晓苏营构短篇的常用手法,即便仅以上述各篇论,基本上都能看出这种手法的影子,唯一例外的是《父亲的相好》,年深日久中的不变,才是流行语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印证,它的结尾是无需反转也不能反转的,作者采用的是象征意味深长的收束:“我把一颗糖深深地藏在舌头下面,不动声色,让它一点一点慢慢溶化,然后再让糖汁慢慢进入喉咙,沁入心脾,融入骨髓。”这段精彩的语言,既是男女主人公一生情感的概括,也是滋润读者心田的审美感受。
将其余六篇略加解读,可以得出结论:对反转式结局的小说艺术,晓苏已经操练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在这个过程中,晓苏不但在与读者的智力较量中屡屡获胜,一再彰显了作品的“意思”,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原本属于纯粹形式上的一种写作技巧,升格为小说内容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使小说的“意义”获得催化和增殖,用得上西方当代美学所持有机形式论者的一句话:形式即内容。一旦抵达这种境界,说这种古老的写作艺术在晓苏笔下臻于极致,应该是公允的评价吧。
《推杯换盏》属于经典型也即常规性的反转,其基本要求一是叙述上需要铺垫蓄势,二是情理上必须反常合道,二者缺一不可。小说几乎通篇都在渲染和强化两个男人之间的仇恨,尤其是陶贵对王羊,诅咒其“早就该死了,死了世上少一个祸害”,这就使结尾的推杯换盏、亲如兄弟,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为了使这一突转合情合理,聪明的作者让陶贵对毛英难以割舍,让王羊对毛英日久生情,即揭示了人感情的复杂性,又为两人的化敌为友寻找了心理基础。
《撒谎记》的结尾,是作者在传统的欧·亨利式结尾艺术中以智取胜的典型案例。我相信只要是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会在心里做一番加法演算,并且能大致预见到小说的结尾,因为这道简单的算术题,不外乎三种答案:1.得大于失,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2.得不偿失,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3.得失相当,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就小说叙事可能的三个选项中,其一属“非反转式结尾”,或曰“生活性结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不会做亏本卖买,如此实写,则了无波澜,自然不合小说章法;其二就有了荒诞,有了幽默,有了晓苏所追求的“意思”,因而就属于“反转式结尾”,或曰“文学性结尾”了。估计大部分读者,都会舍1取2,可是晓苏跟读者的期待视野玩了点智力游戏,偏偏选取了介于两者之间,看似最为平淡的3。何以如此呢?个中奥妙,全在最后一句:“艾蒿欣慰地说,总地算起来,我们也没吃亏,多少还占了一点公家的便宜。她的意思是说,这次撒谎总算没有白撒。”劳神费力,折腾一大圈下来,不过得失相当,何苦来哉,当事人怎么还会“欣慰”呢?原来是觉得“多少还占了一点公家的便宜”,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若无这点“欣慰”,我们只会对这对受尽盘剥的底层夫妇抱以同情心,这一“欣慰”,方知在精神道德层面上,他们实在不见得就比院长、支书等人高出多少,区别只在有权无权、在朝在野,细想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看病》不妨称之为“双重反转式”。乐极生悲,醉驾翻车,是一次反转,这是对一心钻到钱眼里的扭曲人格的戏谑,是对自持有交警队长权力庇护而无视规则的鞭挞;副局长被人举报违纪,巡视组与其诫勉谈话,则是另一次反转。前一次反转基本在读者的猜想中,后一次反转就有些出乎意外了,细读才发现前文已留有伏笔:“省里的巡视组那天突然来了,行管局一下子就忙乱起来。”前一次反转意在批判,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后一次反转好在余音绕梁:失去了副局长的庇护,三个身负重伤的人接下来该如何“看病”呢?顺带一提,这个“带病提拔”的副局长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只为下乡插队的房东关系,几十年不离不弃,殊为难得,小说中不过是个穿针引线的角色,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面。

欧·亨利
《妇女主任张开凤》的结尾,可以称为“声东击西式”。经过从头至尾的铺垫,聪明的读者大都会猜到小说会以主人公的离婚,完成反转式收束,小说也的确印证了读者的期待,然而晓苏又玩了一个花样,结尾之反转,看似在“离婚”,实则在“落选”,准确说是不选之选,更深层的内涵,则在“落选”与“离婚”构成的条件关系上。上面是来宣布新任支部书记的。但是,他们万万没猜到的是,新任支部书记不是“读过高中,说话通情达理,办事热心快肠,天生就是一块儿当干部的料”的妇女主任张开凤,而是人人都没想到的村会计。干部任免中变动的随机性、偶然性,是现行体制下的常态,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正是这种“万万没猜到”、“人人都没想到”的落选成就了张开凤,一旦摆脱了体制的枷锁,抛开了权力的诱惑,张开凤就解放了,自由了,无需再隐忍克己,可以听从心灵的召唤,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如果说莎翁时代的女性,追求爱情与自由所面对的压迫,很大程度来自宗教神权的话,那么当今中国,恐怕就来自世俗体制的牵绊了,不妨设想,假如张开凤顺利接任,她的婚姻家庭又该是怎样状态,明乎此,便可知其内心深处,是否也残存着些许官本位的影子呢?虽说不似《推牛》的“副村长”那么强烈。至于另外三个女人是否紧随张开凤之后呢,没有说,留白不是反转,那是留给读者填补的空间。
《推牛》的结局,可以称为“反转+延伸式”。当故事收尾,一场合谋真相大白之后,小说的反转式结局就可以画上句号了。然而作者并未打住,而是略加延伸,写到“我”奔走各系铃人,以求解铃,还“英雄”凡人的本来面目,以免被人继续敲诈时,却屡受恫吓,已居高位的当事人“严肃地警告我说,你爷爷这个典型,是各级党委一起树起来的,你千万不要乱来!”“高云天烈士是我县的一位英雄楷模,他舍己救人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任何人都别想往他脸上摸黑。谁要是想抹黑英雄,那他就是政治上有问题!”不难看出,这一延伸,笔墨不多,却拉开了“故事”与“小说”的距离,将喜剧因素、悲剧因素、黑色幽默尽注其中,呈现了“悲喜交集”的审美质地,荒诞性、批判性遂极大地提高了一个层次。它极具中国特色,因为它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地域;它又超越了特定的地域,因为当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一悲喜剧的源头时,会发现仅仅归之于参与运作的各级领导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些当事人身后还有一种无形的、神秘的力量,像22条军规那样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小说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涵盖面。
如果反转之法,通常称为“陡转”的话(比如陶贵与王羊从恨之入骨到亲如兄弟,张开凤从劝阻别人离婚到自己离婚),那么《打飞机的傻哥哥》的反转,就可称为“缓转”了,那只是小说结尾处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即道出妓女黑耳所患乃艾滋病,粗心的读者可能会不大留意,然而就是这一二十个字,照应了此前的铺垫,不仅点石成金,写活了一个人物,而且使小说的整体意蕴有了质的提升。
妓女的形象在前辈大师的作品里多有现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小仲马、冯梦龙、孔尚任、老舍、曹禺,举不胜举。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口厌肥甘,身嫌锦绣”的妓女形象,西方文学中的妓女,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大致可以框定其原型,“灵魂救赎”可以大致框定其主题,“社会批判”可以大致框定作家的价值立场,黑耳无疑与后者靠得更近一些。“头一次碰到的时候,黑耳还有些怕丑,眼睛东躲西藏,不敢正面看我,脸一直红到耳垂。后来见到的次数多了,黑耳也就无所谓了”。由清纯乡村少女一变而为风尘女子,这是南方特区经济腾飞伴生的寻常故事,人道“繁荣娼盛”,晓苏只抓拍了一两个极富画面感的传神镜头,略去了其间无数的眼泪与辛酸,换言之,黑耳既可以以特有的方式,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也可以心安理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接纳每一个顾客(嫖客),前者属“极端行为”,后者却是“正常交易”。当“我(哥哥)”不明就里,以为黑耳“打飞机”如同奸商买卖时的缺斤短两,“耍了我们”,想找黑耳算账时,方得知其身染艾滋病入院治疗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原来黑耳是不忍心加害于这个畸零人啊,借用杜勃罗留波夫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的那句话——“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的评价,完全可以用在这个善良的妓女身上,因为尽管社会亏欠于她,其做人的良知善念,却并没有在痛苦中泯灭。至于杨梆受害,则完全是咎由自取,黑耳已经仁至义尽,当然就作家而言,那也是晓苏秉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间价值立场的表达。

吴平安,湖北省作协会员,武汉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出版有文艺评论集《听那强弓响箭》,传记文学《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传》等,曾两次获教师文学奖一等奖,以及《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