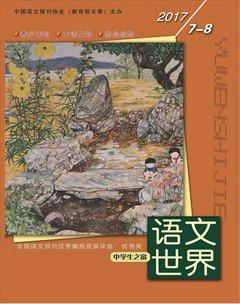大教室
徐殿东
门外,西斜的阳光逆照到地上又反射过来,像金粉一般亮灿灿的。我靠着宿舍的板铺望着外面铺满了一地的阳光。四周清冷如水一般包围着我。帮我上学的大哥和崔雅利都走了,我将一个人在这个离家三十五里路的四中奋斗一年,来改变我的命运。于是,我起身提着书包走进了大教室。
大教室其实就是一排东西走向的旧瓦房,红色的瓦檐下有一排窗口,南面有绿色的木门,门也不大。从南门进去,就吓了一跳,教室被密密麻麻的桌子挤满了。一排摆着八张桌子,南北两边各四张,南北墙边与中间共留三条窄窄的过道。黑板与讲桌在教室的西山墙处,第一排顶着讲桌,一溜下去共有二十三排。每张桌子的上方都贴着写有姓名的小纸条。我从前往后找,在第十八排找到了我的名字。同桌是耿康宁,再右是骞宏武刘雅文,再远就不记得了。坐下之后才发现,南边那一部分全是女生,北边全是男生。最后一排都到三百二十多号了。再后面,仍有一大片空地,空地后的南山墙根下,摆堆着不少卷起来的铺盖和碗筷,地上铺着乱麻麻的麦草。
一周后,觉得这里实际上并没有传闻说得那样好。老师们也没有传说中那样厉害,至于饭食数量少质量差的学生灶,晚上小偷成疯的宿舍,围墙四处倒塌的厕所,还不在话下。但在这个大教室里,却曾一年考过一百二十多名文科大学生。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震撼非比寻常。仅此一点,它仍吸引着大家。
秋天过后,我总是全身冷。晚上睡觉时被窝里冷得跟冰窖一样,要和衣坐在被窝里很久才敢躺下脱衣服。第二天起床时,两脚还是冰凉的。去蹲茅坑,居然蹲了一个多小时,才忽而想起已经有一周多没有蹲了。晚上,听着同学的呼吸声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望着小窗户上的月亮从东边一点一点地移向西边。白天上课,老走神。后来每周总有一天,实在不想听课,总要悄悄地溜回宿舍,钻进被窝斜靠着,木木地一直坐到上午放学。同学们回来了,看见我的样子,也不和我说什么。他们自己总说,去年有一个叫“杨帆”的,每周总有一天会学不进去,头痛得在床上翻滚。但杨帆最后考上西北大学了。还有一个很黑的同学对他的伙伴说,你学不进了,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吧。我闭着眼睛听着,心里很感激他们。
期终考试前下了一场大雪,整个校园白茫茫一片。晚上正上自习,教室突然停了电,先是一片漆黑,接着大家就乱哄哄地吵闹。忽然讲桌那里有了亮光,大家都朝那亮光看去。讲桌上的蜡烛后站着一个低个子的人,这人身旁站着我们的班主任。低个子人开始讲话了,声音不大,却很清晰。“我们学校以前有个女生,家里很穷,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花花衫子,冬天就套在棉袄上,春天温暖了,就脱下棉袄,单穿这件花花衫子,一直再穿到冬天。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屋里黑着没有电,她就到外面雪地里看书。最后考到西安上大学了……”身边就有人小声说了,“张八路”一会儿准又讲他的那个大牛东考不过小牛东了。但这次他却教我们鸡蛋的吃法。他说,鸡蛋冲着喝营养最好。先把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搅成糊糊,再用开水冲成絮状,最后用大碗扣着捂一会儿,就可以喝了。据传,他真名叫张士英,是我们四中的校长,一年四季总穿一件黑蓝色的中山装,个子较低,腰板总是直直的,学生们就戏称他为“张八路”。早上五点多跑操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在最前面领着我们跑。我们心里认为,张士英校长,跟我们学生是一心的,他总在想办法激励我们吃苦奋斗改变命运。大教室里黑黑的但很静,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白亮亮的雪光。
过年回家,翻到一本叫《武林》的杂志,上面介绍有孙思邈的“三口气”,还有谁的“五脏震荡”。我回到学校,赶在大家起床前,一个人到校外的田地里,将“三口气”与“五脏震荡”结合到一起练。一星期没出,便秘就好了,饭量还大增,却总是饿。更多的时候周末回不了家,就与其他同学到学校东南角的教工灶房里挤着看那小小的黑白电视。《霍元甲》正在热播,听着打得很激烈,但总是看不清楚。电视里有什么就看什么。有一首歌在电视里唱,“……热爱冬天的人们啊,他就是坚强的人。像那冬雪覆盖的大地,他就是我的父亲”。这些歌词和那旋律,像暖阳一样温暖地照亮着我们那长久以来被压抑着凄冷的心。后来我就四处打听这首歌,有同学说,那首歌是日本的《四季歌》,但不会唱。去问老穿着黄军装的那个男生,他会吹口琴。在乒乓球案旁,我问这个当时我并不熟的同学:“你能给我吹一下日本的那首《四季歌》吗?我很想听。”黄衣服同学沉默地看了我一会儿,就靠在案子边,张大嘴对着口琴吹开了。听完我才明白,其实黄衣服同学并不会吹,但他为了满足我,就用口琴做扩音把歌给我“啊”了一遍。在我们最苦的时候,这首歌,不知给了我多少熨帖啊。后来就和同学一起抄歌词,抄《北国之春》,抄《橄榄树》等等。这一年,在语文学习方面,功夫下得最多的是两个。一是抄歌词,二是写日记,包括拟订宏观学习计划,包括遇到难处时的写诊断分析。这些抄写,不仅提升了语文能力,最重要的是帮助我度过那一段艰苦的岁月,完成了学业,坚强地成长起来。
春后的预考一下子让大教室里的气氛紧张起来。预考过后,将会有不少同学被刷掉离开大教室。早上五点多,历史杭老师总会出现在我们宿舍,一边咳嗽着一边喊“起来了起来了”,还用手摇着我们的脚。余下马营的王同学就说,杭老师今年七十多岁了,他是民进会会员,曾发过愿,要把最后一滴血洒在教室里。地理王老师也开始兼带我们的政治课,大家觉得他的哲学讲得就是不一样。数学邱老师仍神情庄重地上课,常常有传言说他昨晚上又备课到一二点。课堂上只是看到邱老师的脸好像刚洗过,他常常用辩证法讲题,题讲得很深很慢。“张八路”和班主任到我们大教室来的次数也多起来,他们常常不太说话,总是在看头顶上的灯亮不亮。要么就对着某个正低头写作业的学生说,你是秦镇的,要好好努力啊。
预考后天气就热起来。我们在大教室里可以享受一人一张桌子的待遇。各科老师都在尽心地教着,数学邱老师就在周日上午自动加课,定向训练我们的恒心和毅力。譬如把最难的题放在开头,容易题放在后面,说这叫“门帘卷”,练耐心;把最容易的题放在开头,难题放在中间,叫“埋伏卷”,治浮躁心等。最后复习的日子,我常常离开教室,带一块塑料布,到校墙外面的田地里,按自己的计划复习着。有时候在路边树下,有时候在田地的水渠边。玉米已经很高了,忽然走过一个扛着铁锨戴着草帽的农人,他会大声地说:“好好学!一定能考上!”等我明白过来他是对我说时,他已经消失在玉米地里了。抬起头,我看见了远处我们大教室红色的瓦,以及学生食堂屋檐下的钟。
为了让晚自习有效率,晚饭后要全身心放松着散步。在无数次散步后,有一个叫许忠良的同学便固定下来,他一直陪着我散步到高考,也总是在我想发脾气的时候忍着不说话,只默默地陪着我走。周日下午也会偶尔去附近的牛东。住在宿舍拐角的王时习,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收音机,可以放入上衣口袋的那一种。我们出了校门,慢慢地走着,望着行人村庄,随便说着话,那小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电影剪辑《啊,野麦岭》,要么就是《远山的呼唤》,收音机里传来风的声音、水的声音,还有静默后人们的对话声。我们到了牛东,也没有什么事做,就转了一圈,花了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根带糖的油麻花,掰成两截,两人拿在手里吃着走回来。我觉得那真是一年里最为惬意的幸福时光啊。大教室里,我身边走道的南半部分坐着一百五十多个女生,但这一年里,我都没有与任何一个女生说过话或者认识。她们只给我留下黑鸦鸦一片的模糊印迹。
1984年7月底,高考成绩出来了。等我从家赶到学校时,已经过了中午12点。天气热得很,我们班主任王老师戴着草帽站在大教室门口给围着的同学发分数条。大家看見我都纷纷问,第一志愿报了什么学校。这一年我以489分的成绩考了全校文科第二名。全省的本科线是460分。王老师给我成绩单的时候,特意拉了拉我的胳膊,说,祖庵这娃学得瘦成啥了!我问,老师咱班考得怎么样?他说,大概有一百三十多名吧。语气淡淡的。
临走时,回头望了一眼大教室。一排旧瓦房,红砖墙,不大的木门。在这个大教室里,曾凝聚着一群又一群苦难中想改变命运的农家孩子,也曾凝聚着真诚帮助我们的许多师长的心。我想,我们县被称为教育大县,并不仅仅因为全县每年考取一千多名大中专学生,更重要的是全县其他的人们,都跟苦难中的农家孩子一样,拥有的是一颗渴望着改变命运的上进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