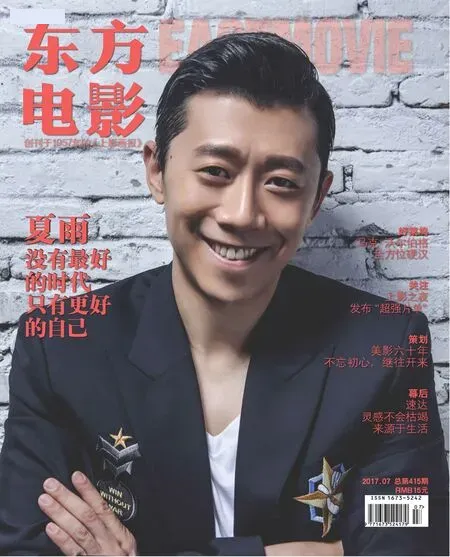胡兆洪美影厂推动着我不断前进
胡兆洪美影厂推动着我不断前进
主要作品:《西岳奇童》《八十天环游地球》等
胡兆洪在美影厂学习的过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被分配到美影厂之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刷新着自己的创作高度。《西岳奇童》《八十天环游地球》……无论是描述传统东方文化的作品还是那些与中西方主题碰撞的作品,美影厂每次不同的创作要求都驱使着他不断前进,尝试接触新的事物。

TALK 对话胡兆洪
Q: 当时是怎样一个机缘加入到美影厂的?
A: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我是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的,被分配到美影厂。我刚进去的时候对美术电影的创作、技术是一窍不通的,到了美影厂之后是从头学习的。我最先是被安排到木偶片这个部门,当一个摄影助理。带过我的老师不少,有蔡正常、钟立人等等一些老前辈,他们都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后来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Q: 您是一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一路创作到今天,回望过去,您觉得美术片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A: 在成为工作人员之前,我们都看过一些美术片,首先就是觉得它好玩,对它有印象。正式接触美术片后,我被这个作品形成的过程所吸引,它需要那么多有专门技能的人来合作,最终呈现出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这本身就是一种魅力。当然在工作中,在周围老师的影响下,我越发觉得美术片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表达工具。我们常常会讨论一些国外的作品或者动画流派,围绕形式、技法、选材各个方向,最终归结到一点,他们是怎么表达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有魅力,哪怕再麻烦,你也乐此不疲,因为你内心有表达的欲望。
Q: 后来您接拍《西岳奇童》这部作品,是怎样的一个缘由?
A:《西岳奇童》说起来有一点感慨,当时靳夕老先生已经退休了,但《西岳奇童》这部片子拍到一半,他希望我能把影片的下集拍完。我当时听到挺惶恐的,我想这是老先生您的作品,如果要拍,也是在您的指导下我们把准备工作做好,请您来当导演。但他说这不是在开玩笑,那我一听,马上就非常郑重地表示我一定会把它做好。其实续貂的事情历来就很难做,在讨论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时的放映技术和制作上集的技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还必须考虑放映条件,最终讨论下来,我们还是重新制作一个完整版的。前半部分原则上重复了靳夕老先生的上集,当然有一些改动,比如人物的出场关系有一些改动。而下集,其实靳夕先生早就准备好了剧本,但我们做了较大的改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孩励志成长的故事,在拯救母亲的过程中得到了历练,收获了成长。但原先的主题是比较复杂,多样的,包含着对抗封建礼教这类思想,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就比较简单了。
Q: 您认为木偶片的特色是什么?它的艺术价值在哪里?
A:木偶片的细节很吸引人,它是一个实体。相对平面的动画来说,木偶片充满细节,这些细节是构成审美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比如我们拍(木偶片)的近景或者特写,它充满细节感,所有的材料、纹理、手工加工的痕迹,哪怕是粗糙的、蹩脚的,都体现在造型上。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看点,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来运用在创作、表达形式上,那这个片子就一定有生命力,一定有表达的魅力。我觉得木偶片核心的魅力就在这个地方。
Q: 我们知道美影的很多片子是从中国传统工艺里吸收养分的,那木偶的工艺是从民间艺术里面汲取的吗?
A:有的,这肯定是来源,比如我们电影的表演是脱胎于舞台的表演。木偶片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最先版本的电影里,从艺术片的角度对木偶片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用摄影机把木偶表演拍下来,还有一种就是指现在我们专门制作的木偶,然后用逐格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两者之间有很明显的传承关系,就是说最早这些创作人是从木偶的舞台表演中,受到这种艺术表达的感染,然后想用电影的手法把它记录下来,然后逐渐演化出这样的工艺。
Q: 您认为的美影精神是怎样的?
A: 在我看来,美影的精神,就是要执著、要专注、要排除所有的干扰。这不是一句空话,这对一个组织机构来说,其实涉及方方面面,很不容易做到。都说现在是拍电影的好时候,票房爆炸式增长,我们作为几代人传承的这样一个团队需要在这其中有所表现,有所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到今年已经有60年了,在这60年当中,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美影未来会更美好,创作出更多大家喜欢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