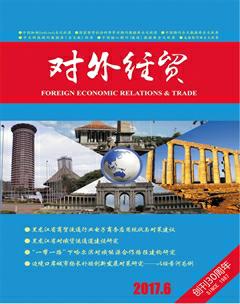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分析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欠发展问题
[摘要]失地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日益得到社会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发展还存在一定的欠发展问题:物质资本丧失严重、人力资本更新不足、社会资本积累有限。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重视失地农民物质资产积累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国家和社会力量介入以引导失地农民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建设和积累。
[关键词]失地农民;欠发展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6-0138-05
[作者简介]刘晓丽(1971-),女,汉族,江西吉安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5YB07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失地农民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群体。在欠发达地区,基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现实因素,对失地农民一般采取一次性现金补偿(补偿标准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等构成)。手握一定资金的失地农民本应在失地后逐渐完成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却出现了一些欠发展问题,而这可能成为其成功城市化的阻碍。
一、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失地农民面临的欠发展问题
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并非完全始于工业或者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政府主观提速推进的城镇化。因此,欠发达地区城镇化之中的失地农民发展问题更应引发社会关注。从已有研究看,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面临资产受损以及资本准备不足等欠发展问题。
(一)土地丧失,其他物质资本和家庭资产不足
已有的调查研究表明,[1]失地农民在土地征用后,最为重要的自然物质资本土地丧失程度最高,受损严重,导致收入数额和水平降低,虽然有一定的货币补偿或其他方式的补偿,但因采用综合补偿方式,补偿项目少且补偿标准低,大部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比不上城市居民,而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趋势中失去的土地资本并不能失而复得;欠发达地区拥有房屋、店铺、厂房、大型机械(汽车、吊车、挖掘机、摩托车等)等可以增值的物质资本的失地农民家庭比例偏低,其带来的收入比重不高;存款、利息等数额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偏低;租金、红利等金融资本情况分布不均,两极分化;股息在失地农民中并不被熟悉和接受,比例特别低。
农民失去土地后,拥有的其它可以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本并不充足,个人和家庭资产长期积累也无法实现,从而无法促进失地农民个人、家庭、社区的长期发展。另外,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面临现有资产或财产保护以及保值增值的问题。因为较少接触现代投资和现代生活方式,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补偿金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投资或使用渠道,又面临一些不良诱惑,涉毒、涉赌和奢靡消费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失地农民及其家庭面临一些重大的发展风险。
(二)面临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困境
国家陆续出台了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2016年后各省陆续取消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在养老、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与社会保障;《国务院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指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主要筹资方式是由个人缴款、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待遇有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构成,支付终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十三五”规划要求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和居住农民为重点,鼓励持续参保,完善并落实多缴多补、长缴多得、助残扶贫等政策,适时提高最低缴费档次;《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号)要求整合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这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所有城乡公民纳入了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内[2]。
但是,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相比有土地收益的农民和一般城市居民而言,其持续参加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险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十分突出。另外,部分失地农民安排集体宅基地,集体迁移新居,住房有保障。而有些失地农民获得补偿金后自行安排住宅和生活,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有租房、自购房、自建房、廉租或公共租赁房等,住房保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人均土地补偿费用的不足,可支配收入低;部分失地农民后续收入不稳定,持续缴费能力弱;参保的筹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有个人和政府补贴承担;失去土地后的生活方式和就业压力使得失地农民日常生活消费开支项增多;补偿费用资金的保值增值水平不高。
(三)就业安置相对不力
国家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拓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构建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学习工作终身、适应劳动者和市场需求的职业培训制度,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劳动者自主选择、政府购买服务和依法监管的职业培训工作机制,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但由于国家提供的就业保障缺乏切实法律保障和资金不足,欠发达地区本地区城市接收劳动力就业能力弱,政府能提供的再就业岗位比较有限,无法满足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需要。现有就业培训体系以政府办学为主,覆盖了省市县三级,但较少推广到乡镇及农村基层[3];培训内容丰富性不足,无法满足失地农民向职业化农民转化的需要以及和非农就业需要;培训师资配备单一及培训方式较为陈旧;培训实践设施老化,以课堂和视频为主,鲜有实践机会。培训客观上对失地农民没有吸引力,加上失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参加培训的主观积极性较低,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竞争乏力,极易陷入半失业或无业境地。
(四)风险防范与利益表达行动能力较弱
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权益难以保障的根源在城乡二元结构,现有国家土地征用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失地农民面临的可持续生存风险在现有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就业制度强化下无法得到有效防范,容易面临资产风险、收入风险、福利风险等,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另外,在征地过程及社会保障的利益博弈中,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集体行动能力和资源不足,一般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利益保护和风险防范能力十分弱小。
(五)适应性、社会融合、心态危机等问题持续存在
失地农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断裂式变化,从农业生产到亦农亦工亦商再到完全非农职业,最终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生产方式,或依靠自身技能外出务工、开店,或本地从事小生意、保洁、维修,或无所事事; 从自由安排生产生活的安逸农村生活过渡到备受约束的较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从诸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到所有吃穿住用行处处花钱的市场经济生活,从独门独院到许多公共空间的安置小区房,从方便走家串户的农村住房到由物业管理的封闭独立的高楼套房等,不仅生活成本提高,许多失地农民行为习惯和心理上更面临诸多不适应。[4]
在征地利益受损体验后,失地农民又感受到的非农生存以及融入城市的困境与不安。在整个社会结构场域中,失地农民感受到了明显的“比较落差”以及在结构中的无力感,这些感受体现在对于自身处境的悲观以及改善可能性的否定,以及对于导致这种社会分化的原因的否定与不满。已有研究也表明,失地农民群体存在普遍的焦虑、不信任、群体性怨恨、负面情绪等心态危机。[5]
二、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看失地農民欠发展问题的根源
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视角看,在较低水平的国家社会保障条件和较低的失地农民自身能力素养的实际情况下,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融入城市是有限的,其带来的社会风险将深远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失地农民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有限。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要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策范式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人们开始形成了共识,即福利的提供既不能完全依赖政府,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需要构建一种积极性社会政策,使社会各个成分都能够在福利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发展型社会政策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
1强调人力资本在社会福利中的比重。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代表吉登斯认为,建设社会投资国家不仅可以解决福利国家本身的问题,还可以增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的竞争力[6]。建立社会投资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而不是给予直接的经济援助。提供费用较高的普遍福利已经成为不可能的选择,社会福利支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增加个人参与经济的机会才具有可行性。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投资应该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
2强调促进个人资产长期积累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的重点不应再放在传统的收入再分配上,而是应该促进个人资产的长期积累,以推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社会投资”理念被另一位发展型社会政策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迈克尔&谢诺登教授进一步发展为“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在《穷人与资产》一书中,他首次提出了“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观,主张社会政策的重点应该强调授权于个人,促进个人资产的长期积累,以推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构成社会整体的长期发展。迈克尔&谢诺登认为拥有资产除了能维持消费以外,还可能产生其他积极的影响,如更确切的未来观、更稳定的家庭、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妥善的财产管理、更积极的社区参与、增加个人效能感、增加社会影响等。[7]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需要个人资产支持个人、家庭发展的人力资本和社区发展等社会资本的投资。
3强调社会资本作用的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思路从以消费和维持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能力、投资于民、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8]。发展型社会政策包含一些重要理念: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社会干预和集体行为;普遍主义、平等和社会包容;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等。美国社会政策学者米奇利认为这些理念在实践中体现为系列“社会投资”行为,如投资于人力资本、就业和创业计划、社会资本、资产发展、社会计划;消除经济参与屏障等[8]。处于弱势的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满足维持消费,更可以倾向于为其进行“社会投资”。
4强调提升社会质量水准的社会政策。“社会质量化理论”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社会质量”被界定为“民众在提升其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为了达到可接受的社会质量水准,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们必须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就业还是来自社会保障,以便使自己免于贫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剥夺;二是在劳动力市场之类的主要社会经济制度中,人们必须体验社会融入,或使其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最小化;三是人们应能够生活在以社会整合为特征的社区和社会中;四是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被赋予一定的权能,以便在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面前有能力全面参与。这四个基本条件决定了社会关系朝社会质量方向发展的机会。满足这四个条件,人们才能获得社会质量能力。[9]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质量”还远没有处于可接受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享有应该的福祉和成果。
(二)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欠发展是人力资本更新不足和社会资本积累有限的结果
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面临的资产受损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准备不足等是影响失地农民及其家庭、社区长期发展的核心要素。提高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使失地农民得到公正充分的市场化补偿,是解决失地农民欠发展问题的重要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效果。但提高补偿费并不能必然支撑失地农民持续生计和适应发展的双重需求,且土地征收补偿的公平市场化也要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性保障。
1失地农民个体和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缺乏与社会制度性保障不足和社会排斥问题的弱性循环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对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也即与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 “特定行为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大小,取决于他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网络规模的大小,或者与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依靠自身的身份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符号的)资本的大小。”[10]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其信息功能、影响功能、社会信用功能和强化功能而在行动者的工具性行动和表达性行动中获取预期收益。[11]
从失地农民个体和群体本身看,社会资本是具有失地农民身份的“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是与失地农民群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失地农民能有效运用和占有社会资本很小,因而再获得制度性保障的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也就小,形成一个弱性循环,在各种紧急情况下,能够获得或者将会获得社区或网络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从正式制度上获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
失地农民制度关系和制度结构的社会资本贮备不足。首先,对于土地征收补偿市场化的法律制度保障严重不足。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地征收法律,有关征地的法律规定仅限于《土地管理法》中的部分规定,且规定不够详细具体,尤其是征地补偿为综合性补偿,补偿项目没有进行细化,在征地事件中引发一些不满和抗争。其次,失地后的福利制度性保障不够。失地农民有一定的失地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当前及以后相当长时间生活暂时不存在经济困难。国务院2006年4月10日就出台过《关于建立被征地农民培训就業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意见》,但因为地方经济水平和财力不足,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教育培训就业也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这些不足又和失地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集体行动等方面的社会资本是密切相关的。
失地农民的社会信任、道德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关系性社会资本少。欠发达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化社区建设不完善;失地农民面临生活方式现代化和城市化,很多生活习惯在城市不被认可,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城市小区被市民认为是不宜居的,对这一群体产生不信任和落后没文化没教养等标签化认识。由于失地农民没有充足人际交往及社会融合空间,对失地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就是说,失地农民关系性社会资本占有很少,因而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失地农民个体及其家庭、集团型社会组织之间所拥有的社会信任、道德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关系性社会资本无法有效增加。
失地农民参与不充分,采取有效集体行动不足。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因共同面临失地问题,在处理土地补偿、具体安置等实际问题时失地农民有一定的参与机会,但因为文化素养等限制,参与能力并不强,再加上居住和就业多样化,异质性日显明显,组织化程度低,相对弱小的失地农民群体在面临公共问题和追求共同利益时参与并不充分,采取有效集体行动不足,因而无法有效争取获得个体和群体性社会福利保障。
总体上看,失地农民的欠发展问题不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更是观念、规范、制度、信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资本的赤字造成的,同时,欠发展问题又强化了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不足。
2失地农民人力资本不足与就业、医疗健康和收入保障的不确定性的相互强化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主要指凝集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表现为人的智力与体力的总和。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物的资本所发挥的作用。[12]人力资本不仅包含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包含时间、健康和寿命。根据人力资本内涵,人们一般会从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来测量人力资本情况。
失地之前,农民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经验丰富,体力劳动能力强,吃苦耐劳,但其拥有的非农产业的人力资本是有限的。失地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相当部分是被动参与城镇化,是在非农产业发展不足以支撑失地农民收入来源及数量不减少的情况下的被迫失地。从主观意愿上看,失地农民的失地行动不是其自主理性选择的结果,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人力资本准备和积累。失地后,农民处于对以后生活的无准备的慌乱和迷失中,并不充足的土地补偿费一般用于必要的生活消费型开支和家庭资产的积累,没有理性计划和切实安排用于教育培训和健康保障上的人力资本支出。
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的年限偏少,学历水平不高,有非农职业一技之长的比例、参加技能学习与培训比例很低,获得非农职业从业资格的比例更低,从事农业之外的其他职业的工作经验有限。相当多的失地农民因为环境恶化、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等原因,身体健康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在非农职业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由此引发其收入保障和持续参加社会保险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强化了失地农民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和付出的不足。
综上,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欠发展问题就是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从而社会质量低下的体现,是其在提升其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欠缺、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不足的表征。
三、解决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问题的路径思考
国家和社会以及失地农民自身应认识到不断争取保障和更新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积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同样重要。
(一)提升失地农民社会质量
使失地农民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就业还是来自社会保障,以使其免于贫困或一定形式的物质剥夺;在劳动力市场等主要社会经济参与中,考虑失地农民体验社会融入,或使其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最小化;能够生活在以社会整合为特征的社区和社会中;给与失地农民群体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并赋予其一定的权能,以便其在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面前有能力全面参与。
(二)健全征地法律,保障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建设的物质基础
土地是失地农民曾经最重要的发展资本,土地征用时应科学公平考虑土地的增值功能,进行合理估价,提高征地补偿水平。通过制定专门的征地法律,保障失地农民在货币财富有所补偿,使其生存与发展有物质基础作保障,同时在征地补偿中增加人力资本培训和发展费用项目,提供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物质基础。
(三)社会力量引导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建设
失地农民个体最基本的需求是可持续生计的需求,就是保障各种收入来源的需求,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发展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发展,最终要通过失地农民自组织建构,缓解自我排斥,促进社会融合;要通过社区能力建设和失地农民自身能力建设,获得自我发展机会与能力。在优势视角下,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发掘失地农民社区和农民的资产和能力,使得社区和民众成为当地农村发展的主体。这种内生力对于当前的失地农民来说还不够,可能需要一定的外在力量的介入和帮助。通过有效的教育培训等行动干预失地农民个体、群体和社区进行积极干预。开展失地农民社区教育,提高其城市适应性,培养其现代性,以满足其现代化需求,提高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质量”。
总之,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视角看,在较低水平的国家社会保障条件和较低的失地农民自身能力素养的实际情况下,缺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失地农民融入城市是有限的,其带来的社会风险将深远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型社会政策视野下,以社会投资为导向,国家应该在政府主导下发动各方力量对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发展进行积极干预,尽量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而不是给予直接的经济补偿和援助;尽量投资和积累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提高其适应性,培养其现代性,以满足其现代化需求。其中,对失地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进行教育与培训成为这种干预的主要渠道。
[参考文献]
[1]黄建伟.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76-87,107—108,109—110.
[2]赵定东,袁丽丽.村改居居民的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困境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6(12).
[3]孙建家.做好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的对策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6(21).
[4]周毕芬.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失地农民权益问题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5(4).
[5]胡鹏飞.社会底层:结构机会与心态危机[J].福建论坛,2016(11).
[6][英]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2.
[7][美]迈克尔&谢诺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M]. 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7—217.
[8][美]米奇利.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A].张秀兰,徐月宾,米奇利.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C].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163—175.
[9][英]艾伦·沃克.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生活质量?[J].社会政策评论,2007(1):3—27.
[10][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02.
[11]林南.社会资本——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8—20.
[12]西奥多· 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22—43.
[13]李惠斌.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2).
[14][美]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 木子西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2).
Abstract: Land loss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land-lost farmers still have some underdevelopment problem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loss of material capital, the lack of human capital renewal,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limite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perspective provides beneficial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blem of land-lost farmers: the importance of land-lost farmers physical asset accumulation.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land-lost farmers to construct and accumulat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by the state and society.
Key words: land-lost farmers; underdevelopment problems;the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責任编辑:郭丽春)
——评杨盛海《城市化推进中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