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子午岭考察手记
文图/冯玉雷
环子午岭考察手记
文图/冯玉雷

义渠王都深藏何处
2017年4月27日上午,参观宁县博物馆时有两大惊喜:
其一是偶遇德高望重的考古专家郎树德先生。近年来,他多次参加我们组织的学术活动。叶舒宪、易华等先生也与郎先生相识,都对他充满敬意。2016年我们进行关陇道考察时,到过位于镇原的常山下层文化遗址,在博物馆欣赏了该时期的大量陶器。郎先生在《镇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序言中说:“以镇原为中心的陇东高原是常山下层文化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今年初,镇原县博物馆王博文馆长联系我们杂志社合作编辑出版一期镇原文物专辑。我将这些情况与先生交流,并从他那里首次学会如何识别戎人使用的“铲头鬲”。
其二是发现并还原了被误作为石斧的玉钺的尊贵身份。这件玄色玉钺器形优美、温润,没有任何砍砸痕迹,显然是礼器而非工具。它堪与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出土的两件玉钺相媲美。灵宝、杨官寨、宁县三地以鸳鸯玉质的玉钺、玉铲为媒介,通过渭河、泾河及其最大支流马莲河联结起来,像一条戴在子午岭南部及东部地区的墨绿色项链。
庙嘴坪遗址位于马莲河、城北河(古称大小延川)、九龙河(九陵水,据传因从公刘开始到古公亶父的先周九个王陵墓所在地而得名)及水磨沟交汇形成的三角形台地上,背山临水,视野开阔,确有王者之气。难怪公刘曾在此建邑,当地人也认为义渠王曾在此建都。有学者认为“义渠”系羌语,意为“四水之国”。不管事实情况如何,这里毫无疑问曾是多种文化的重要舞台。遍地陶片足以说明问题。文物部门为保护遗址,栽了各种花树,清香弥漫。考古学家张天恩研究员在20世纪90年代攻读博士期间,就常常背着干粮,乘坐班车跑田野。现在虽然退休,但见了“田野”就立刻兴奋起来,矫捷似兔,在树林里寻找折射历史文化信息的陶器碎片。叶舒宪教授也捡到一些陶片,摆在地上,请张天恩先生进行现场讲解:它们距今6000~4000年,分属庙底沟、仰韶晚期、客省庄文化。历史文化如此丰厚,但同样具有深厚意蕴的名字“公刘邑”却被近代的“庙嘴坪”遮蔽。张天恩博士建议恢复原名。
下午,在前往正宁县途中,顺路考察两处遗址。位于早胜原西头村中正在考古发掘的宁县石家墓地初步确定为春秋早期,出土文物显示为秦文化边缘,与北方草原和中原周王朝都有密切联系。考古证明这里也有常山下层文化存在。考古队长张俊民研究员率领工作人员和当地农民工在烈日下作业,非常辛苦。博物馆看到的光鲜文物大多都是考古人员长年累月默默发掘、整理、修复而成的,他们是伟大文明碎片的拾缀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殉道者,因为他们把大量时间都献给了野外。
现场考察中,我与叶舒宪先生返回杏树下休息,交谈。忽然,易华兄像兔子一样从工地那头狂跑而来,卷起一道烟尘,近前,他满脸惊喜,气喘吁吁地说:“张队长说了,允许我们看看出土的文物!我推测这里是马家塬之后的第二个重要春秋早期遗址,将有重大发现!很有可能进入十大考古发现!”
关于义渠王都城所在地,陇东地区目前有四种观点,其中一个观点认为其在孟家村。几经打问,终于找到遗址,天高地阔,禾苗青青,油菜花灿然。向正在劳作的当地村民胡志孝先生(67岁)了解,他说世代称其地为“城台”,传说中的“吃喝孟家城”(不知因何得名)方圆240亩,因为地势较高,又曾是王地,平常人不敢建房屋,人们仅种植粮食,发现过秦半两钱、铜剑、铜镜、箭头等,至于瓦片,“一车一车往出拉”。

从庙嘴坪俯瞰宁县县城

考察庙嘴坪遗址
从现代人的视角回望历史,混沌不清,其发展却都井然有序,“非虚构”,遗落在大地上的各类证据不管如何解读,都不能改变其本质。我坚信,随着多学科专家、学者以及科学家的深度合作,越来越多的历史谜团将被解开,越来越多的误读将被还原。
一脉相承的“大传统”依然时尚
《诗经·豳风·九罭》诗句“我觏之于,衮衣(古代王侯穿的刺绣有卷龙图纹的衣裳)绣裳”和《诗经·豳风·七月》诗句“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鴂,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反映出3000年前北豳刺绣业的兴盛,同时也佐证了北豳古地心灵手巧的妇女创作的“针线活”刺绣艺术作品。
27日晚抵正宁县,发现宾馆大厅赫然悬挂着一幅色彩艳丽的刺绣作品《五毒螃蟹》,我与叶舒宪先生不约而同地想到《诗经》中这两首诗歌,同时也由螃蟹、蝎子、蛇、蜥蜴、蜘蛛联想到彩陶纹饰中的同类动物图案。这个螃蟹头部形象与杨官寨遗址中出土的仰韶时期彩陶盆中的“蛙图腾”何其相似!
早在文字叙事之前,这些先民集体创造的“大传统”就开始传递内心信息,表达善恶、理想、追求。正宁刺绣作品中,五毒动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青蛙可能会被螃蟹代替,蜘蛛或被蜈蚣代替,也可能被屎壳郎代替。正宁远在黄土高原,本不产螃蟹,但刺绣中出现了,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的军屯和移民。而屎壳郎是古埃及信仰的图腾物,或许最早在青铜时代就随着游牧民族穿过苍茫辽阔的欧亚大陆,到达西北高原,被土著居民愉快接受,并且通过青铜针与当地丝线刺绣到绸布上。至今流行的正宁香包《金鱼》《人面青蛙》《绣龙鱼枕》《虎头针扎》《莲花双鱼》《双鱼枕》等都取材于动物,寓意深远。尺幅之间的刺绣作品,却蕴含着古老悠远的文化交流历史,何等壮阔!
蜥蜴与蛇是东、西方史前文化器物上都能见到的动物图饰,两者是否存在交流互动的关系,目前还在探讨与研究中。

正宁县博物馆藏仰韶文化黑彩双耳人面纹葫芦口陶瓶

考察麻暖泉遗址
28日上午,姚博、秦博文陪同我们参观正宁博物馆时,又意外看到一件仰韶时期的人面黑彩葫芦陶瓶,人像线条清晰,笔法古拙,风格写真,并不夸张。彩陶人形器并不鲜见,多与巫术和原始信仰有关,也属于“大传统”范畴。其实,即便发明出文字、进入“小传统”以后,漫长的“大传统”时代中孕育、产生、发展、变化的图像叙事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们以“六瑞”、画像砖、石刻、雕塑、纹饰等形式继续配合着文字表情达意,在波澜壮阔的文明大海中,始终扬波起浪,并且还引领着时尚文化。例如,现代企业的logo、QQ中的企鹅形象,甚至微博、微信中丰富多彩的表情包,还有俊男靓女的晒微笑、晒撒娇、晒深沉、晒幸福、晒美食、晒风景,哪个不是省略文字的图像表达?追根溯源,都能看到与“大传统”一脉相承的发展痕迹!“大传统”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原来所有能够焕发生机的时尚都根植在深远悠久的大文化传统中!
柔远河的波光远影与遗响
马莲河两条支流——柔远河与环江河交汇之处切割成形似凤凰的台地,山环水抱,古人因势筑城,形似凤凰,又名“凤凰城”,自隋开皇十八年(598)析置弘化县,经过多次变更,现为庆城县。28日下午,考察团抵达庆城县后,与当地文化局副局长赵启迪、博物馆馆长贺兴辉等对接,马不停蹄地参观名胜遗址与博物馆。文化信息如壶口瀑布,飞流直下,激昂饱和,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吧。
29日,考察目标地主要在柔远河流域,先撷取几多浪花,折射石峁文化越过子午岭对陇东地区的影响。
第一站麻暖泉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柔远河西岸傍山台地上,梨花刚落,杏树正绿。此前麻暖泉村村民将台地平整成三级田地,种植玉米、小麦及黄花菜。这里曾采集过泥质红陶黑彩敛口钵、绳纹双耳鼓腹尖底瓶、素面敞口折腹罐及夹砂红陶绳纹、附加堆纹罐等残片。在断崖下寻找,很容易看到夹在土层中的陶器碎片,张天恩先生是彩陶研究专家,现场讲解,受益匪浅。我想抓拍这动人的情景,打算爬上被杂草覆盖的土崖,结果抓了两手刺,虽然逐一拔掉,但体验了大半天的灼痛。童年时代在野外玩耍,小心翼翼躲着这种刺,偶然不慎被扎了脚,最多不过两三枚,现在年届五十,却意外被扎,满满两手,望之眼花缭乱。这种特殊方式让我对麻暖泉遗址加深了记忆。另外,让我记住的还有忠诚质朴的优秀文保员石有军(64岁)及妻子庞会荣(60岁)。他们看护遗址已经38年。
张多勇教授说这里曾是郁郅县城址,还有一条从定边驮盐的古道——“车厢峡道”,现在仍可通车。可惜这次不能实地踏勘。
第二站是位于柔远河东南岸一级台地上的吴家岭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出土有泥质红陶敛口钵、素面盆、线纹尖底瓶、绳纹夹砂陶罐、缸和灰陶环等。1975年,文物部门采集到其地出土的小口葫芦瓶,造型精美。这个遗址地势比较平缓,柔远河安安静静地在山脚下的川道里流淌。清风习习,麦浪阵阵,还有几声野鸡沙哑的朗诵。大家沿着田地边的断崖寻找灰坑、灰层、窖穴等暴露遗迹和散布地表的陶片。虽有收获,但没找到标志性的齐家白灰层。
逆流而上,继续前行,中午到达柔远河上游的华池县城。稍作休整,即参观位于山顶的博物馆。非常感谢原博物馆馆长倪树隆、现任馆长罗志才及馆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放弃“五一”小长假的休息时间,陪同参观,并且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问题。我们意外看到一件朴拙的尖底陶瓶,张天恩喜不自胜,激动地说:“距今大概7000年,是仰韶尖底瓶他妈!”形制独特的大玉刀与我们此前看到的齐家文化玉刀都不同,有可能与石峁文化有某种联系。一件虎噬牛铜牌饰反映出鄂尔多斯草原青铜器向南渗入子午岭西侧高原的信息。憨态可掬的大腹陶熊是神话学研究难得的实物素材。近几年考察,叶舒宪先生写过三篇关于“熊图腾”的文章,后来每个博物馆几乎都能见到熊崇拜的痕迹,就习以为常了。
能够徜徉在如此丰富多彩的文物“森林”中,也算人生幸事!但愿我们国家各个级别的学校教育都能够充分利用博物馆,这不但能够充分发挥文物价值,也是对考古学家、文博工作者乃至文保人员尽职尽责劳动的最大尊重。
当然,最根本的是,柔远河从远古流淌至今,有交响,有激荡,波光远影,生生不息,在陶片、玉器、青铜等物质实体中注入很多绵延而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它们会告诉人们有关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尽管这些信息层层相叠、盘根错节,但只要用心领会,其脉络就会越来越清楚,而柔远河的涛声也就释放了,还原了。
洞洞沟引发的随想
4月29日下午,天清气朗,山风如茗。汽车在子午岭西侧雄阔古塬中驰骋了大约一小时后,到达位于华池县王咀子乡银坪村银坪河畔的洞洞沟遗址。与很多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发现的文化遗址不同,这个出土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的地方显得有些寂寥,就像镶嵌在坚硬沉厚地层中的远古动物化石,承受着几百万年的负重和挤压。发现者法国人桑志华功成名就,在近一个世纪后随着鄂尔多斯台地南缘水洞沟遗址被开发成遗址公园而广为人知。2016年9月,我在去往鄂尔多斯开会的途中专门拜诣水洞,大为震撼。因为交通和地缘优势,遗址公园车水马龙,游人如织。附近的明长城、烽火台也成为强调缀饰的旅游文化符号。相比之下,被层层古塬围拥的洞洞沟遗址则显得有些落寞。桑志华能够意外发现,确实是一大奇迹!

发现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的洞洞沟遗址
根据华池县博物馆新旧两位馆长的指认,大家登上陡坡,遥望峡谷中当年人们挖“龙骨”的洞洞。甘肃大地富藏远古动物化石,其中有的裸露于野,可用于入药治病。记得父亲曾说“龙骨没假的,虎骨没真的”。“龙骨”是民间对所有古动物化石的统称,到甘肃的和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看看,就知道陇原大地上曾经有多少“巨无霸”统治横行过。华池博物馆里展出半截蛇化石和一条完整的鱼化石,鳞片闪闪发光,似乎上百万年的时空阻隔只是一层薄纸。但到底过于遥远,内心难以泛起“沧海桑田”的感慨。
据地层显示和专家研究,先是这些古生物由于地理环境变化而消失,然后覆盖上深厚广袤的黄土,为孕育古人类提供了必需的温床。经过漫长的时光跋涉,古人类演绎的生存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最终学会制作石器,积累了辨别各种石头的经验,因此,“石之精华者”美玉才可能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承载华夏先民信仰的圣物。时光悠悠,岁月苍茫,还有多少个“洞洞沟”“水洞沟”遗址被深埋、被遮蔽?
略作踏勘,又往相隔约1公里的郭咀子遗址考察。山谷幽静,时闻野鸡叫唤。我们沿着缓坡前行,发现较为完整的白灰层面、古窑洞痕迹及大约龙山时期用来盛灰烬(也可能是保存火种)的灰陶鬲,已经破碎。
环绕大半个山腰,忽见前方有两处世外桃园般的古朴院落。门前有两棵古槐,嫩芽新绿,萦绕如烟,轻笼三个鹊巢。喜鹊不知去哪里了。两只狗极不情愿被搅扰,狂吠不止。倪馆长敲开门,男主人不在,“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向女主人打问男主人搜集到的一堆陶片下落,说是撇掉了。
刚才在车上打盹时恍惚听得倪馆长讲,前些年这家男主人依靠文物生存,再想想看护麻暖泉遗址38年的两位老人,感慨颇多。

考察树洼遗址
岁月悠悠,时光匆匆,一切很快都成为过往。龙山时期古窑洞与现代居民旧窑洞都难逃被废弃的命运。“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呈现在大家视域里的花树、青草或许与龙山时期的景象并无二致,能沟通古今人类心灵的是凝聚各种文化意义的器物。例如,郭咀子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环,虽然质地无法与美玉相比。但是,透过它,似乎看到悠远时空里游玩的少女,头戴花环,手持柳枝,正向我们恬然微笑。
树洼遗址,夏朝初年的王者之地
早晨沿柔远河北上,不久即进入子午岭西坡缓山丘陵地带,道路转弯多起来。首次穿越子午岭,心情颇为激动,努力寻找秦直道痕迹。按常例,道路修筑在山岭最高或较高处才能保证取直、捷径。汽车盘旋一阵,节节攀升,到达打扮梁。据传此山岭因王昭君出塞时脱掉中原服装换上胡服而得名。当年昭君日渐远离中原,必然在秦直道洒落一路悲愤忧伤的眼泪,与现代人寻古探幽的心境大不相同。子午岭的桃花色彩格外浓烈、艳丽,惹得张多勇教授感叹不已。
这条道路看不到秦直道痕迹。下车远眺巨涛般滚滚而去的山丘,拍照,留下悬念,继续前行。
有学者说,横穿子午岭的道路大约有10条。我们走的这条路在东坡下有白豹镇,曾是宋朝与西夏角逐的边境重地。白豹城保存较好,我们特意登上白豹河南岸紧邻马路的石山,从高处向对面观察,遥想金戈铁马。顺着河谷北行,路上时见山上耸立的宋朝、明朝烽火台。其中一座明朝烽火台形状极像宁夏海原墩墩梁烽火台——2015年2月、3月,我因缘两次造访,岂料4月就被“有关部门”用大铲车夷为平地,令人痛心!
白豹河在金汤汇入北洛河,道路也交给北洛河谷。逆流而上,到达吴起县。找博物馆,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转了几个圈,走了不少冤枉路,颇为郁闷。张多勇教授打电话询问朋友,志丹县博物馆也没开。我想还是直接去今天的目的地延安,但叶舒宪先生不愿“空”跑,坚持要看马明志博士主持发掘过的树洼遗址。用午餐时对着地图确定路线,只有25公里。于是,简餐后,匆匆出发,西北行。汽车沿北洛河河谷南岸台地上的吴定路前行,问了两次路,村民详细告知我们:“有条河流拐弯的地方,向右拐进去不远就到了树洼。”果然,这种地形出现时,问路口闲聊的两位村民,其中一人哈哈大笑:“我就是树洼人,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就坐上车带路!”我们热情欢迎他和两个孙子上车。他叫冯志东(64岁),两个孙子分别叫帅帅、瑄瑄。路边的小河当地人称为“暴城沟”。谈话间,车已经驰到保护碑前,老人指着前边说:“这一架山全是遗址保护范围!”并自告奋勇作向导,带路。
此前考察的文化遗址大多在河流或河流交汇处的二级台地上,灰层较为明显,并且容易到达。这个遗址的保护碑虽在路边,考古发掘地却在山顶,似与白云试比高。冯志东老人带路,狗吠声伴奏中,我们穿过依坡而居的村舍,开始爬山。坡地上,往往有一树杏花、桃花或梨花寂寞开放,虽无蜂蝶渲染,但光彩耀眼。越往上,山势越陡峭,坡度非常大,难怪当地人称这架大山为“崖板梁”。我们沿“之”字形羊肠小路躬身而行,有时不得不侧身“横行”穿过荆棘林。半山腰,一位打柴的聋哑老年妇女冲我们微笑,质朴自然。我向她和手致礼,她挥挥手,灿然笑着。
走一阵,回望一阵。眼前境界逐渐开阔,像气势磅礴的巨幅画作徐徐展开。“移步换景”,每升起一个高度,眼界都有新内容。虽然汗流浃背,但被“风光在险峰”的永恒真理鼓舞着,也被不时闪现的不知名的花儿诱惑着,不知疲累,登上与崖板山相连但更高的营盘山山顶,平坦的地面上有座圆形台地,中间清晰可见齐家文化白灰层。爬上圆形台地,举目四望,眼界开阔,群山逶迤连绵,呈环绕状、臣服状。东、西远山上都有烽火台。据此推测更东、更西的山上应该也有烽火台彼此呼应。根据考古学家公布的资料,这座台地北部的大草梁、小草梁出土玉器、陶器,以龙山时代至夏初文化遗存为主。身临其境,遥想在此生存的夏初先民以某有功王侯为首领,以营盘山为中心,襟带群山,定期用大禹赏赐的玉礼器祭祀天地,祈求福祉。
这个下午,我们感受到了夏朝初期昂扬向上的宏阔气象。将来,考古文物若能够与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对应起来,该是多么美丽的田野故事!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龙山”不是玉
延安芦山峁遗址是我们此行重点考察的目标地之一。因为有树洼遗址成果铺垫,我们对这个位于延河流域的文化圣地充满信心,充满期待。5月1日早晨8点半,延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杜林渊教授同延安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准时到宾馆等候。大家寒暄几句,即驱车出城。路上传阅叶老师壮怀激烈、铿铿锵锵的抒情长诗《树洼怀古》,同感。昨天,易华兄本来打头阵,被村口大黄狗挡回,结果,“偷懒一时,错失千年”,未抵山顶,便领略不到群山环绕的壮美,估计也很难领会这首诗歌蕴含之神韵。

从芦山峁遗址远眺延河
说笑间,汽车进入杂草丛生、树林密布的深沟。简易砂石道路在山间盘绕回环,坡陡弯急,汽车行进很困难。地势层层抬升,最终到脑板梁与营盘梁相连的平缓哑口处。这里绿树滔滔,山色清新,地表植被优于新寨树洼遗址。下车,大家自然排成一队,迤逦走“之”字形路。双腿沉重,还带着考察树洼遗址时遗留的酸痛,行路颇难。随着周边群山辽阔苍茫景象的呈现,满怀欣悦,精神大振,很快就到营盘梁较为平坦的山顶。
杜林渊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主要工作是教学研究,但因缘时会与延安考古所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直接参与考古发掘。经多年熏陶,其气象明显与书斋式教授不同。大家萍水相逢,却毫无陌生感。杜教授滔滔不绝地介绍,恨不能将积累多年的考古感受和研究成果和盘托出。该遗址20世纪70年代首次被村民发现,因交通困难,文博部门难以管理,玉器大量流失。现在,遗址仍是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村民仍然耕种。土地上,去年收割玉米后留下的根茬俨若冷兵器,霸气、坚挺、狰狞,与曾经蕴藏的红色玉玄玑、玉璧、玉琮、玉璋、玉刀等玉器气质大相径庭。
目前,营盘梁功能还不十分清楚,但综合所在位置、坚硬夯土层及遗址保护范围内大量玉器出土等信息推测,芦山峁要早于石峁遗址。尤其另一处相对封闭独立的台地上、面朝延河方向敞开的状若城门之缺口,让人与史前古城产生联系。如果这个缺口是龙山时期的城门,那么,那些夯土层就是城墙遗迹。当年的城墙有多高?有多少龙山人参与了夯筑?它们执行了多久的护卫功能?又是如何被岁月分解的?
接着,大家又登上对面脑坂梁,即可观览营盘梁全貌,又能看到马家洼旁边状若巨大象头的芦山峁——保护范围多达300万平方米的该处遗址就是以其命名的。马家洼是一处向阳山坡,据说前些年“玉器一筐一筐地出”,大多数流入民间,延安考古研究所征集到20多件。
下午,我们被允许进库房一睹玉容,大为惊诧。保管员有条不紊地展示青黄玉璧、青玉刀、玉璋、玉圭、玉琮,忽然,外面雷声滚滚,大雨倾盆。在雷声、雨声、惊叹声的伴奏中,我们以朝拜的心情逐一观摩、欣赏、品读。雷声、雨声酣畅淋漓,我们心旷神怡,大快朵颐。这些玉器玉料优良,做工精美,器形浑朴,反映出龙山时代玉器的辉煌成就,也折射出龙山先民对玉文化的痴迷程度,可谓“感天地,泣鬼神”。
这些玉器仅仅只是龙山玉器文化很小的一角,但透射出的信息却非常大,令人震撼。例如,青玉圭可能是二里头文化源头,57厘米长的青玉刀让人望而生畏。富有鲜明良渚文化特色的玉琮表明,史前海滨与内陆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且有道路相通。如果说是良渚的玉礼器作为交换礼品通过北洛河、延河、无定河甚至黄河到达陕北高原,但玉质令人生疑。良渚文化玉器中至今没有发现过类似玉料制作的玉器。红山文化中也没有。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上好的玉料,但做工无法与龙山文化玉器的细致精美相提并论。因此,可以夸张点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龙山”不是玉!根据目前专家研究和科学测定,制作这些玉器的玉料极有可能来自甘肃、青海或新疆。玉石之路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青玉璧在发现之初,曾长时间被村民用作暖水瓶垫。文博工作者得知后,花8元钱买两个暖水瓶,换回来。这段经历如果被当年的龙山“朝野人士”得知,肯定会暴跳如雷、七窍生烟。
参观后,离开库房。雷声阵阵,大雨如注,似乎要洗掉那段不虞记忆。
石摞摞山上望黄河
2016年7月中旬,我们考察渭河峡中张天恩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关桃园前仰韶文化遗址,时隔近一年的今天,又考察先生发掘的石摞摞山遗址。能够与考古学家一同考察其主持发掘的著名史前遗址,是福分,值得自豪!
石摞摞山遗址为陕西境内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堡遗址(见《文博》1997年第3期),保存相对完整,对研究史前城市形成、城垣建筑方法及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等有着重要的价值。

考古学家张天恩研究员站在石摞摞山石城墙边
从佳县出发,先过葭河,再过其支流五女河,行车约一小时,便到石摞摞山遗址。这是一座巍然独立的高山,五女河曲曲折折,从东边绕过。山顶开阔舒缓,有两处较为明显的城门痕迹和外城(6万平方米)、内城(3000平方米)两层城墙遗址,颇为壮观。我们走在酥软的草山上,绕城一周,探看石墙遗址,俯瞰五女河,远眺周边低矮连绵的群山,又临崖感受古城“孤悬半空”的雄强气势。踏勘时,我看到一行石块连成线,经张天恩先生考证,竟是第三道内城!2003年发掘时,他还没有发现。大概当年被尘土和杂草覆盖,经过10多年风雨冲刷,终于露出真容。令人惊讶的是,山峰最高处有一座方形台地底座,中间又凸起长着灌木的小土丘。如此结构,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祭祀台,而祭祀中最重要的“道具”就是玉礼器。然而,截至目前,石摞摞山遗址还没发现玉器。但龙山时期玉文化盛行,作为功能如此完备的史前“王城”,不可能没有玉礼器。何况,张先生调查到这个城址并非孤立,其附近还有规模较小的石城遗址。据朱官寨镇书记薛晓华、朱官寨石摞摞山文物管理所所长张爱明及石家洼两位村民讲述,紧邻石摞摞山的另一处“回水城”遗址10多年前曾出土大约50厘米长的玉刀和玉璧,流失民间,下落不明。
无论如何,这座王城绝非等闲之辈。根据目前考古结果显示,石摞摞山遗址早于同样位于黄河流域的石峁文化遗址。虽然其规模远远小于后者,但当年龙山人从五女河里采集到石块后背到山顶,和上草泥,堆砌城墙。或许“堆砌”太费事,它们只在城墙内外两侧精细累砌,中间则随意丢上大小石块。经过几千年风雨洗礼,大部分坍塌陷落,乱石滚落,散落山坡。大家从石堆中找到一个直径超过15厘米的石盘和半截留下人工痕迹的青石。它们可能是玉璧、玉圭雏形。
山下有张先生带队发掘过的城壕护坡遗址。护坡堪称优质工程,至今坚固。近几年,国家开始重视工匠精神,并且号召向德国等国家学习。其实龙山人早在数千年前就践行了,现代人捡起来即可。
石摞摞山遗址地势高巍,山水相衬,风景绝佳。尽管山与山之间被深沟险壑隔开,但通过对出土文物的考察,可以证明,史前人类并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孤立发展,而是存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伫立山顶,遥望黄河,视线被逶迤山脉阻挡。加之昨夜突起沙尘暴,天空朦胧,更增添了很多古老文化遗址的深邃感和神秘感。
黄河是如何影响这些石城的?玉文化为何在龙山时期兴盛起来?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早已出现,只待人们细心去解读了。
环灵大道上的“玉门关”——青冈峡
5月5日上午,参观完靖边博物馆之后,沿青兰高速到盐池。找到一家做“剁荞面”的小饭馆打算用午餐。店中只有一主妇忙碌得团团转。为赶时间,叶老师亲自帮厨,意外发现卫生不佳,就帮助洗碗。我大窘,遂转到旁边较为干净的小店吃炒刀削面。
餐后,上定武高速前往环县,顺路考察青冈峡。这次考察前期准备期间,叶舒宪先生提及陇东北部与宁夏交接处有个叫青冈峡的地方值得注意。《旧五代史·康福传》记载,五代后唐天成年,康福被唐明宗调往镇守灵州时走环灵大道,“至青冈峡,遇雪,福登山望见川谷中烟火,有吐蕃数千帐,不觉福至。福分其兵为三道,出其不意袭之。吐蕃大骇,弃车帐而走,杀之殆尽,获其玉璞、绫锦、羊马甚众,由是威声大振”。当时我不知道青冈峡的具体位置,打电话咨询祖籍环县、在甘肃石窟研究院北石窟寺研究所履职的朋友吴正科。但他因长期在河西走廊工作,对家乡文化不熟悉,推荐环县博物馆文博工作者沈浩注所撰《唐宋时期青岗峡与青岗岭之地望考辨》(《西夏研究》2015年第03期)一文。查阅,果然有很大收获。沈文认为“兴平城遗址就位于今环县洪德乡赵洼村赵洼组。其地处环江、清平沟、王小沟三河交汇的台地,南距洪德乡10公里。遗址现残存部分城墙,遗址内可捡到宋代耀州窑的青瓷片。确定出兴平城的位置,也就明确了唐宋时期的青冈峡口就在今环县洪德乡赵洼村”。
史载青冈峡为环灵大道必经处。环灵大道是唐末、五代和宋代长安通往灵州的交通要道,是灵州道重要组成部分。《新五代史·康福传》中记载的“玉璞”令人眼睛一亮,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它们购自何地,但可以肯定吐蕃人要销往中原,据此推知吐蕃人也是玉帛之路上的主要贩玉大户。定武高速横穿盐池荒漠地,《武经总要》中称“瀚海”。沙尘蒙蒙,沙碛茫茫,时见“沧海一舟”般的烽火台在远处沉浮。现在它们颓然来去,当年却是指引方向的生命灯塔!汽车高速行驶其中尚且感到移动缓慢,当年行旅穿行何等困难!若遇烈日、酷寒、暴风等恶劣天气,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断东西、南北友好往来。五代时期,党项人经常出入这片枯寂“瀚海”,劫掠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当然也不会放过载满货物的商队。康福本为唐末五代时期沙陀族将领,擅长骑射,通多种蕃族语言,他到任一年多,西域诸国纷纷前来归附。后唐长兴三年(932),朝廷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康福将步骑7000人讨党项。五月,康福将劫掠的党项人全部消灭,余者请降归附。可见康福为开通青冈峡道起到过重要作用。通常说到汉朝以来的丝绸之路北道,大多只说通过弹筝峡、瓦亭、固原的路线,极少提及沿马莲河及其上游支流环江北行的“青岗峡”。严耕望先生认为唐代长安与灵州之间交通线路主要有三条,“而邠、宁、庆道尤为主线”。据陇东学院张多勇教授考察研究,陇东地区至少有七条线路通往宁夏,它们之间互有联系,形成路网。这是丝绸之路的真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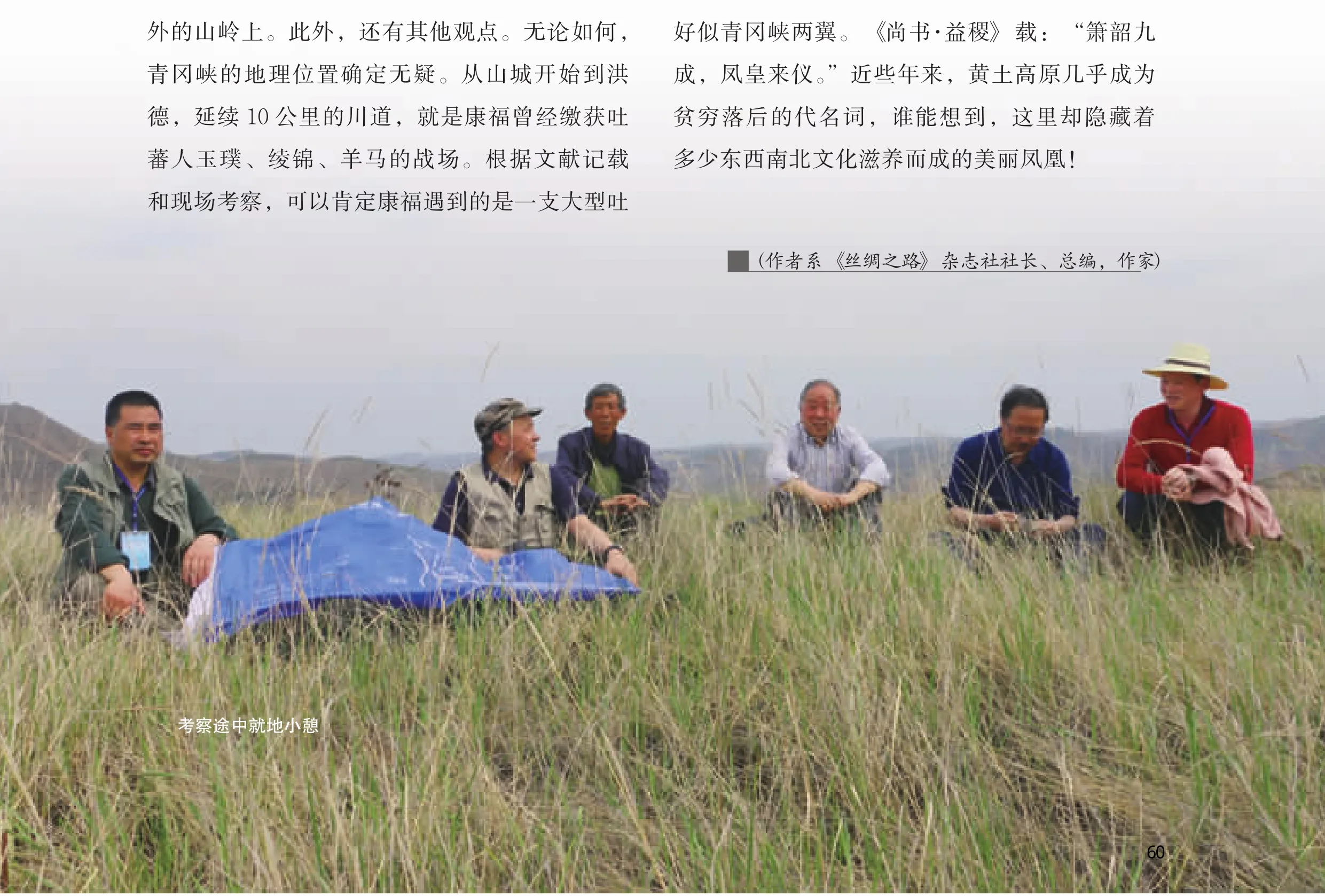
考察途中就地小憩
汽车在马儿庄下高速,沿304线走大约18公里,在惠安堡进入211国道。自4月26日考察杨官寨遗址后,我们沿大致与泾河平行的211国道西北行,现在,经过10多天的艰苦奔波,又从北边绕回,到这条贯穿渭河、泾河、马莲河、环江河的南北大道。看地图,211国道其实就是唐五代时期环灵大道的再现。
惠安堡向南,连续有隰宁堡、萌城堡、甜水堡、山城堡、洪德堡等重要堡寨,尤其自山城乡进入东川河谷川道后,两边山头的烽火台密集布置,彼此呼应,彰显出这条峡谷在峥嵘岁月中的重要性。这就是几乎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青冈峡。有学者认为,位于山谷口西高地上的山城堡就是当年扼守青冈峡的“青冈堡”,张多勇先生则认为“青冈堡”在相距大约5里外的山岭上。此外,还有其他观点。无论如何,青冈峡的地理位置确定无疑。从山城开始到洪德,延续10公里的川道,就是康福曾经缴获吐蕃人玉璞、绫锦、羊马的战场。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场考察,可以肯定康福遇到的是一支大型吐蕃商队而非军队,否则他们不可能“大骇,弃车帐而走”;或许,吐蕃商队误以为是党项人来袭击,因为他们以劫掠为要事。当然,这些都是猜想。不过据此基本可以认定吐蕃人是玉帛之路上的使者。再往前推,大月氏、羌族、乌孙等少数民族都曾热情高涨地向东方中原输入美玉。
目前,尚未找到记载回鹘人贩运玉石的史料。
将青冈峡谓之环灵大道上的“玉门关”,未尝不可。或许,这条峡谷输入美玉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汉唐玉门关,而子午岭东西两侧的黄土峁梁山洼间蕴藏的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常山下层文化等史前文化的玉礼器,也可能与这条长达10公里的“玉门关”发生联系。
青冈峡中还有两条重要支线:其一是从洪德向东北沿归德川直达陕西定边的古道,其二是从虎洞沿虎洞河往下马关的宋韦州路。它们好似青冈峡两翼。《尚书·益稷》载:“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近些年来,黄土高原几乎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谁能想到,这里却隐藏着多少东西南北文化滋养而成的美丽凤凰!
(作者系《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