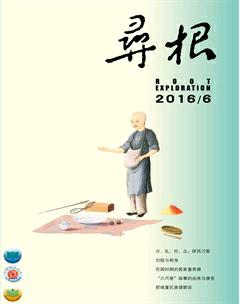兴、乱、狂、众:陕西刀客
王旭
刀客是陕西地方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自清中期始,原有社会秩序严重失控,等级阶层不断变化,灾疫频发,经济亦趋于衰微,流民大批出现,甚于以往,成为社会痼疾。闲散民众和流民无法被正式的社会组织吸纳,刀客之滥蔚然成风。道光之际,随着刀客数量不断增多且地区分布范围逐步扩展,最终形成了刀客会。
刀客之名的由来,与刀客们手持临潼关山镇(今属阎良区)所造的关山刀子密切相关。此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形制特别,极为锋利。因大多数刀客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关中地区,故又名“关中刀客”。一般来说,清季官书称作“刀匪、莠民”,有的地方官统称其为“匪徒”。随着刀客势力的坐大,与各色地下势力不断勾连,加上陕西部分士绅、民团、哥老会首领及后来新军势力的拉拢照应,他们成为一股重要的区域武装力量,纵横捭阖,在地方多次政治变迁中均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大伙横行官不知”:
早期刀客的零星记载
刀客之名约莫出现于乾嘉之时。道光年间,刀客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至光、宣之时,其组织及成员已然遍及三秦,并在周边省份如河南、山西、宁夏、甘肃、湖北颇有活动,各处地方官亦有捕获刀客之记录。
嘉庆末年,陕西泾阳人徐法绩,时任太常寺少卿,因守制家居,其家遭遇盗匪劫掠,在徐氏与泾阳县令毛有猷的私人通信(《复毛明府书》)中言及刀客:
鄙意以为最可恨.者,惟蒲城刀客,逗留乡镇,交通路役,招场窝赌,昼则为匪,夜则为盗,实为地方大害。刀客有头目,有绰号。若暗中访闻,严其究治,则其党自散而之他,前者郭兰坡明府访拿多名,出示招告,纷纷逃散。彼时在家丁忧,曾亲见之。
刀客立根于基层社会,严拿则四散为民,不仅与匪甚难区分,与民也混杂处之,令地方官束手无策,难以一次性肃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徐氏又作诗一首:
同州刀客昔无之,近日成群市上嬉。
夜间作贼日间赌,大伙横行官不知。
刀客从往昔无之到近日成群,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延展性,从小股到大伙横行,绝非倏忽之间。徐法绩根据居家所见所闻,直言刀客的猖乱。嘉道之际陕西刀客之兴、狂、乱、众,地方社会风气之崩坏,于此已可见一斑。
刀客出现在清人记载中,不是孤例。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江苏华亭人朱大源迁知蒲城县,据《清史列传》记:
蒲城多盗,有刀匪,其首日王敢鸣(改名),聚众屯井家堡界,蒲城、富平、临潼、渭南四邑间,匪坚壁深,濠备火器拒捕,民与匪往来自保。
民匪交杂,已成事实。林则徐巡陕之时便说:“陕省刀匪最为间阎之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陕西朝邑人(今大荔县)李元春给护理陕西巡抚杨以增(1787-1856)上书,就陈述了朝邑“有刀客李牛儿之抢案”,饥民“或聚众黑夜抢劫,或结伙白日乱扰”,袭击炭厂,夺取财资诸事,刀客之声势,甚于以往。道光之后,“刀匪”名有组织,实为流寇,此起彼伏,聚散无常。清代陕西各级地方官员,自督抚至县一级,对此甚是焦虑,颇费事功。叶伯英、邓廷桢、林则徐、曾望颜、谭仲麟等名臣干吏,俱不同程度参与过“肃缉刀匪”的活动,甚至不惜重典,将之“就地正法,施以重刑”,然而效果很局限,“未尽根株”。
与历史上的“侠客”不同,刀客显然不具备“侠盗”“游士”应有的品质,他们中大部分无疑是基层秩序的破坏者,手持关山刀,交接捕役,些许刀客类同匪徒,烧杀抢掠,为害一方。至清末,在地方已构成“刀害”。在受到官府抓捕之时,他们成股流窜,游荡地方,居无定所,同时为谋生计,四处抢掠,劫富济贫,引发地方士绅的“可恨”,普通百姓亦深受其害。
异歧纷呈:刀客之源流
据多种文献考证刀客群体发轫于乾、嘉年间,成熟于道、咸之际,而后盛于同治“回乱”、清末“民变”风潮与辛亥革命。
有一些学者认为,刀客是汉代之“朱家、郭解”、唐代之“五陵年少(英少)”的“流风余韵”,历代相传流为风气,重侠崇信,是秦文化尚武、任侠之气的留存。此种说法将刀客与古风相对接,具有强烈地区文化情结;也有学者认为,刀客兴起于清道光、同治年間西北“回乱”之时,陕西汉民为求自保,聚集亲族,招兵买马,组织自卫团体和堡寨护卫,从而形成刀客;还有学者认为,刀客是鸦片战争之后,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经济衰微,乡村危机严重,流民增多,刀客群体由此发轫。
另外,作为一支秘密社团,由于民间由来已久自发的交流,在川陕、晋陕、豫陕、陕甘、鄂陕之间进行渗透和整合。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山东乐陵人史谱职掌陕西巡抚,十二年(1832年)五月奏言:“陕省界连川楚,向有匪徒,自名刀客。睚眦细故,拔刀相向,民莫敢较。屡经惩创,未尽根株”。史谱认为,陕地刀客形成与“接连川楚”相关。刀客的起源与四川啯噜、哥老会、豫西红枪会、陕西地方信仰亦颇有关联。晚清刀客遍及省与省之间,与传统区域之间的交杂息息相关。如宣统三年(1911年)河南巡抚兼河工事务臣宝蕖所奏报:
河陕汝一道,南阳一府,刀匪蔓延几同流寇……从前贼匪以刀为利器,故名刀匪。今则多携快炮,犷悍更异于前,不惟乡民望而生畏,莫敢谁何,即队役亦多退缩。
以往的各种观点,令人莫衷一是。实际上,刀客形成与近代复杂的社会环境是同步的,其产生遵循多力论,不是线性、单一的因素所诱发,是多个因素交合羼杂的产物。基层破败与乡村危机是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是清中期以来错综复杂、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矛盾催生着民间诸种力量和各色群体的暗中组合与结社,成为正式社会结构和等级划分之外的社会存在。
刀客作为武装力量,不仅纠葛于地方秘密势力之间,还常常于政治风潮紧密相连。刀客逐步形成刀客会,其支派与哥老会、唱噜类似,因地区差异且无统一组织,规模小于哥老会、啯噜。
刀客会成员大多投师拜友,游行于同辈之间,义气交往。在此过程中,由于亲缘、地缘、业缘诸关系,团体帮派意识也由此发轫。这些组织及其支派组织不断吸纳着成分复杂、动机各异的流民——失业者、亡命之徒、乞丐、地方零散兵弁等,逐步发展壮大,自觉与不自觉的地介入地方社会生态和格局,成为塑造地方社会风貌多元力量的一个环节。
游荡地方:刀客的组织模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湖南人李星沅奉旨授陕西巡抚,二十三年抵达陕西任上,在其《行述》中如此记载:
同、凤一带多刀匪,带刀游荡,名曰刀客。又有红钱、黑钱等名目。忤法肆劫掠,民苦之,乃出示申言禁约……檄行各属粘贴,赏罚随之。是以陆续擒获巨匪二十余人。
可见刀客组织在道光年间,已有了红钱、黑钱等名目。刀客会存在一个类似于首领的人物,一般都称之为“某某哥”、刀首或其他有地方特色的绰号,颇具匪气。大荔县李牛儿(满盈),朝邑刀首甲午儿,兴平县刘三,富平县王寮镇刀客段学义(四煽狼)、杨鹤龄(白煽狗)、段三多(草上飞)、柳红(红老九),宫里石象坤(仄楞子)、严锡龙(野狸子)。这些刀客的绰号,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在“刀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班子”,不细分等级,平素围绕着他活动。他们自称“孝义家”“凭信家”等,形成“一摊”,结伴营生。某些刀客首领亦收“义子”,如王狮子(振乾)收严飞龙为义子。刀客首领来源广泛,有贫苦下层民众,也有不少地方士绅豪强。刀客组织与地方团练关系密切,其成员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他们不满清政府,参与民变,俨然成为正常社会结构中另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朝邑县著名刀客,后为陕西东路刀客之首的王狮子曾中武秀才。辛亥革命中,对白水光复起到重要作用的刀客高峻,便在当地组织过团练武装。
从结社初衷讲,刀客成员们崇尚侠义,采取“开山立堂、叩拜宣誓、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会众,在组织结构上还是传统封建大家长制下的映射,同时他们虚构会党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尚义气,忘生轻死,鼓吹义气至上,替天行道,具有一定道德预设。部分刀客成员浪迹民间,路遇不平,勇于拔刀相助,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且不索代价,事息只供一席茶饭而已。因而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扬与爱戴。在地方社会,刀客颇有群众基础,某种程度上参与地方治理。
在传统社会形态下,刀客及其组织者多为聚集地中心周边村落的村民,有显著的亲缘与地缘表征。而小手工业者、工人及其他失业者的自发联合,基本具备“业缘”特征,彼此之间存在互动与认同,形成一种地域与组织认同。大部分刀客游居不定,无正式职业,其谋生之行业,大致有盐客、镖客、赌客、土匪或游寇四类。
刀客会组织规模大小不一,分散在关中各处,总会与支派之间无绝对统属关系。分布空间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渭河沿岸较多,关西(宝鸡)和陕南亦有散布,整、鄂、乾、武、扶、郿、岐、凤、宝、陇、华、潼等十数县皆有分布,少数刀客与豫西、湖北会党有结连。会众广泛,散居各处,集体行动以成股的形式出现。
刀客虽无哥老会、天地会般成熟的组织及等级关系,但也具备一个初步的权力架构和组织结构。根据史料记载,刀客会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嚴密的纪律,他们对于自身组织及走向未形成完整的认知和构建,关于组织结构、等级观念、指挥调度、进攻退守、内部管理、发展吸收会众、财务收支及各级分工的概念相对是模糊的,具有朦胧的平均意识,是比较原生的组织状态,尚无成文的制度设计和纲领,惯性习俗是行为方式和处事模式内在规范,处于一种比较分散和游离的架构体系之中。
泉涌风发:刀客们义旗高举
刀客成员入会初衷大多为生活所迫,而缺乏真正的政治与组织诉求。武昌起义之后,陕变继作。辛亥革命自开始到结束,在进步团体的引领下,刀客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们引领民众,“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湃动”,平地波澜,酿成社会激变。著名刀客王一山、高峻、王绪朝、党玉琨、党海楼、白喜、马豁、崔式卿、杨衰、王兴奎、曹育生、李兆祥、胡彦海就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
不少刀客组织及支派在革命前喂养战马、制造炸弹、积蓄军备,为起义做先期准备。西安起义前担任陕西陆军军械官的陈树藩联络朝邑刀客严飞龙(孝全,字子青)、渭南刀客严纪鹏(绰号白翎子)两个标,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部及胡景翼联络富平刀客王守身(绰号黑脊背)、胡彦海(胡老六)、马正德(马老二)、石象仪(绰号冷馋)及零散刀客等营,参与了辛亥革命。胡景翼创建的“渭北复汉军”,其来源大多是富平刀客。朝邑、富平、潼关、同官、礼泉等多地光复,均与刀客有莫大关系,不少刀客首领也在革命中牺牲。
爱国将领杨虎城,自幼因其父亲杨怀福被仇家诬陷遭官府杀害,与同乡成立“孝义会”(丧葬互助合作组织),并愤而投身于刀客组织。后与一批志同道合者新组“中秋会”,所部纪律严明,不扰民间。辛亥革命时期,率部参加革命队伍。陕西靖国军成立时,第一路军郭坚(振军)与刀客会过从甚密,他的兵源编组就主要以“刀客”为基干,在之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刀客群体来源庞杂,成员广泛,农民、铁匠、煤炭工、地方胥吏、士绅、私塾教师、道士、艺人、民团乡兵等,都有可能转为刀客,群体的多元来源决定了群体的组织追求的多元化。刀客群体中不全是“仗义行侠之流”,部分刀客因乱而起、趁火打劫、为非作歹并横霸一方,亦非仅见。
阎良的刀客“老五”(张兴五),为“牛刀客”张明轩之弟,成为当地一霸,在乡里网络爪牙与打手30多人,横行不法,拼命敛财,抢霸田产,破坏乡村秩序。在阎良镇有商号6座,经营棉花、粮食、百货等日用商品,操纵着阎良镇的经济。同时,在乡镇大摆赌场,见十抽一,大发其财。民国后期,基本控制了阎良镇公所。又有,1918年的韩城民众合力击毙“野狸子”严锡龙,严氏时任王银喜的部下,常下乡派款。民间有“委员到县,百姓打战;委员下乡,百姓遭殃”。至十二月,南乡民团袭击严氏,其当场死亡。高士龙作《严锡龙见毙于韩民论》,言“身之亡也,以作恶亡,亡有余责”,地方文人以文论警示后人。这一类人,富江湖流氓习气,渭北地区普遍存在。他们蛮横无理,歪邪凶残,不受陕民待见,当地人憎其行径,称为伪侠、贼棱子或仄楞子,严重影响了刀客的声誉。
民初政局的变更,因地方各色势力(包括刀客会)纠葛而导致涣散动荡、规矩丧失,刀客群体亦难出脱于此。他们从来不是正义的化身,也不是秦文化流为风气的遗存,是清中期以来地方社会激变的结果。刀客群体及其组织萌芽、形成、成熟,其原因相当复杂,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危机逐步加深、多因素互动促合的产物。刀客会属于边缘化组织,他们游离在传统社会格局,在地方社会各色势力之间斡旋,生计与生存策略与道德诉求往往难以统一,也是清中期以来复杂社会存在的生动反映。
组织革易:刀客的结局
民初政局稍定之后,作为变动时代的刀首及刀客成员成为过渡时期游离的群体性象征。除个别刀客首领及其追随者,大部分刀客都通过战争形式,逐渐转化成新军或地方军阀。曾任陕西督办的李虎臣,其绰号“径儿老四”,便曾是刀客一员。未能被“正式组织”吸纳者,一部分转化为散兵游勇,唯利是图,武断乡曲,服务于地方社会各色势力;另一部分刀客上山入伙,落草为寇,其中不乏流氓地痞,抽大烟,抢家掠货,欺压无辜,威胁治安,蚕食疮痍的地方社会,撕裂基层秩序,危害大于零星散匪,成为陕西匪患的一部分。
以地方社会作为舞台,刀客的勃兴,与基层秩序失范、社会转型暗合,刀客在暴动革命之间纠葛不清。民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环境变易,刀客逐渐失去存在根基与条件,这一社群也蜕化变质。刀客之行径,不能单纯用正义或者非正义囊括论之。跳出革命史观叙事范式和地方文化情结,对于刀客的评介,在这一视角上,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也没有必要进行强烈的价值判断。
刀客这一群体,是我们观察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刀客们手持关山刀、练武习拳、立足地方诸事,成为陕西民间的历史记忆,也是近代以来陕西社会变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