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留学的日子
何子维
近几年,“去国外受教育”成为一种趋势,那么,这是刻意而为,还是理性选择?当把留学作为一种个人成长的期待,成为一种人生标签,比较中西方教育的异同,是做出这个决定的前提。而谈论教育的最好办法,是回到教育本身,从经历者那里寻求证明。
批判性
我在国内本科毕业后申请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读硕士。我遇到的第一难点,是导师每周开出的不计其数的阅读清单。我总想快速读完却总处于欲速则不达的状态,这让我倍感压力。私下偷偷询问那些公认的学霸,怎料他们也有同感。
导师劝导说,慢下来,速度并不意味着一切,让我这个已经习惯而且以追求快为目标的人有些懵。导师介绍我学习了快速画出思维导图法,还建议我找一位学习伙伴,分头阅读,交换信息。这种互助式的学习情况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我遇到的第二难点,是开口讲话,参与讨论。我熟悉的情景是,老师提出问题,课堂基本沉默。偶尔有人讲,也是力图使用标准的或者趋于一致的答案来回答。在英国,导师根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具有可选择性,比如“这个作者是左派还是右派”、“欧洲还有未来吗”。这时候,中国留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上网搜索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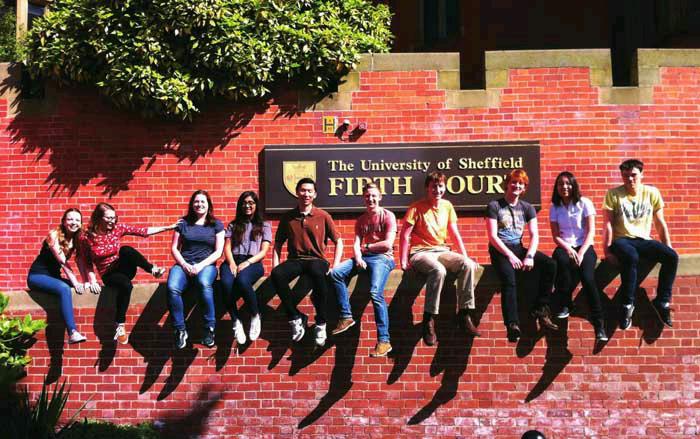
上网搜索这个动作不是不好,至少反映出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优越性。由于互联网,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知识已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普通信息,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知识总和”。但是直接等待“人类知识总和”给出答案,实质上与选择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与一路追逐满分的望子成龙教育理念是一个逻辑。在这样的条件下,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反而变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知识贬值”现象。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对危险的互联网深恶痛绝,刻薄地写了《最愚蠢的一代》,结果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其实他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希望下一代变得更聪明、更渊博。他所讨论的“愚蠢”并非是智力上的指摘,而是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这个过程,利用互联网,本能够获取了丰富庞大的知识信息资源,但缺乏信息的自我内化,这是愚蠢的。
我遇到的第三个难点,是导师要求用2000个单词来论述一个问题作为半期的考试,评分的唯一准则是:批判性思维。导师花了半节课的时间来阐述什么是批判性。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在鼓动学生胡说八道,但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直到教授说:“无论在哪个年代,对自由的争取,以及自由、批判的思想都是艰难的,但从未止息。在今天的教室里,集体负罪感和集体胜利的概念都是荒谬的。”
批判性写作并不是新鲜概念,但是像我这样的学生,至少在上大学之前是没有经历过相关的训练的。同样,中国学生的雅思写作成绩全球最低,并不是因为大家词汇和语法能力不好。如果你去书店里看看,与写作有关的畅销书大致是《佳句分类集锦》《满分作文范例》之类。一直以来,我们对满分漂亮的句子、文章、结构趋之若鹜,恨不得一本本压缩在脑子里,在写作的时候复制出來,选择性都少有,更谈不上多少批判性。
比如诗歌作为教材的经典,在国内学习的时候,我们只需朗读背诵,然后就是听老师讲写作背景,逐句分析内容含意。整个过程学生完全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做点什么,听着、背诵,就可以了。
迈过这三个难点,我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从一个只听别人讲话、追求标准答案的人,向有怀疑、有追问、要批判的方向转变了不少。但是,我仍怀疑,难道听话错了吗?追求标准答案也错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新的创造,都是在前人确立的标准上建立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思考就是有目的地将各种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进行归纳整理,通过分门别类把知识记在脑子里。比如把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作品拆散成为“笔记”,使之化为自己便于记忆或者运用的材料,这是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必经之路。这种方法,在现代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钱钟书的《管锥篇》、顾随的《顾随历史笔记》。
不同的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就不喜欢“信息的知识”,他认为:“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按照爱因斯坦的标准,教育传授的不应仅仅是信息的知识,而是引导受教育者盯住那些闪亮的灯塔,向他们学习,通过思考、理智、判断,理解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成果据为己有,向更远的方向进发,使自己在这个过程获得进化。
由此来看,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是具有非常意义的。否则就像陈丹青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只需要听话的人。”如果把培养教育对象听话、顺从变成了教育的终极效果,是值得思考,也值得警惕的。但是,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养成,单靠学校这种有限的教育资源是办不到的。换言之,培养这些能力不是学校教育的全部。从小学到大学,学校教育能够给予学生的知识,对于以后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能力来说,十分有限,这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好奇心
黄草草是我的高中同学,她高中毕业后去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读本科,然后读研究生,现在已经在西雅图定居了。
去美国之初,黄草草对自己能否继续保持学霸地位没有足够信心,但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她所在专业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美国同学根本不是对手。黄草草一直认为她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应试教育在美国竞争的胜利,她高度认同国内的老师,他们敬业甚至很卖命。正是由于他们扎实地抓知识点、基本功和思维训练,才造就了像她这样的新一代移民。黄草草坦言,将来自己的孩子会在国内读到高中毕业,然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
对于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批评国内所谓的应试教育的人来说,黄草草的肯定显然不是刻意拔高,而对于国内急于把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家长,无疑具有很大的参与价值。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并不比美国差。给中国的教育扣上应试教育的帽子,是因为大家认为现在的教育无非就是为了高考这个唯一的目标,学生被教成了考试的机器。
在黄草草看来,从华盛顿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来看,要修满180分的学分,专业课只占45分,另外135分要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中去选课,才能毕业。这种分布必修型(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教育设置体系,是倾向于让学生以自己为中心,对整个知识领域有所探索,把积累知识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是重点。
这不难理解,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西方人的知识理想是类似于“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人文主义者推崇的典型代表就是达·芬奇,他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作家,还是运动员。达·芬奇曾写道:不是数学家,请不要阅读我的基本著作。姑且不谈要理解达·芬奇的观念必须是一个博学达人,但是尽可能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是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向。
现在,通识教育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接受,在课程设置上也趋于多元化,尽量让学生们保持综合性发展。这种设置的好处,是能让学生们了解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我有个住地下室的英国室友John,他的梦想是“拿诺贝尔物理奖”。平均两到三周做完一个实验,写一篇报告,但他从不觉得辛苦。与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完美不一样,John每次做实验时都认为“我不可能做到完美”。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前者可能抑制了一份勇气,后者保留了一份冲动。
相比这位把物理当作“灵魂伴侣”的英国室友,现在国内学生念大学的理由,大都是借此期望扭转命运,缓解就业压力。如果再往上读研读博,其目标首先是进政府机关,其次是进高校,谋求一份稳定、体面的职业,而因为好奇心的做学问不多。所以说,“有教无类”,是个理念问题,现代国家的基础教育基本都做到了。但“因材施教”,还是个技术问题,仍然值得思考。
在英国坐火车的时候,我拍了一张几乎满车厢的人都在阅读纸质书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国内的朋友不无感慨地问,英国的交通怎么这么陈旧,网络覆盖这么差,可怜的英国人只得以书来充斥时间了。
这的确让人奇怪。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也说他喜欢坐火车在北欧旅行。白岩松也发现,他在国内坐火车的时候,经常是三五好友坐在一起,等火车一启动就把座位转过来,大家对坐着开始打牌,高兴之际大声嚷嚷,像饭堂里喝高了酒。后来白岩松坐火车在北欧旅行,火车启动后,发现一车的欧洲人都在读书。这对于一个爱读书的白岩松无疑是一种精神享受。
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相信白岩松的描述,觉得白岩松矫情。其实在国外不是没有流水线上生产的明星八卦和社交暖文,但是他们对于书籍的爱好的确远远超过了明星八卦和社交暖文。
从教育的有效样式来看,能不能培养一个有好奇心、有探索欲的人,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进行持续终生自学,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后来我在列车上想拿出iPad看地图,反倒突然觉得有点不入流了。正如艾略特的一句诗:“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生存力
“知识守护生命”在国内是被重复很多的话语,但我在留学期间接受到那些书本以外的知识,却是全新经历。
我的第一堂课是在教室外开始的。没有老师,学生会几个成员带着新生在没有围墙的校园依次浏览介绍,特别叮嘱新生要盯住墙上的消防安全通道指示图,然后就开始消防演习。
新生们嘻嘻哈哈地按照套路演练了一遍,新鲜感一过,就把演习的内容扔在一边了。没想到,之后一周里消防演习成了常态,校方时不时拉响警报,弄得新生们觉得自己都快成职业消防队员了,在国内哪会受这份罪?有人愤怒到嚷嚷着要去校监处告状了。
接下来的戏路还有参观警察局、邮局、银行,讲各种办事流程。我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同学曾经感叹:“我在国内那么多年,别说去警察局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因为出国需要信用卡,我根本不会和银行打交道。这些杂事一般都是父母包办的,他们怕因此耽误我学习。”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开学第一课》,第一次播出是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以《知识守护生命》为主题,对全国的孩子进行应急避险教育和生命意识教育。但是这样的选题到目前仅有一次,之后的几期都像在做形势任务教育讲座。
统计数据显示,在急救知识普及率上,欧洲高达80%,其中北欧普及率最高,美国普及率70%,但在中国,这个数字不到1%。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唱响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现在,因为我们爱钱、爱权,教育则随着世俗的价值取向而制定、增加、改变课程,各种商战、权变的东西包裹着国学、EMBA的外衣不断在增加,就是都没有把保护生命、获得生存的基本技能列入必修科目,其实是遗忘了所有行动力的主体本身。
为了获得持续的“高等级”价值,“加快建设”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整个社会都在高速运转。我们快活,快富,一日胜百年,在成功的同时,顾不上尊重生命本身,甚至顧不上尊敬长辈、拥抱父母、陪伴孩子、亲吻爱人和关怀自己,在这样的速度要求下,整个国家都在经受“不能老、不能穷、不能失败”的煎熬。速度开始是我们的骄傲,后来成了我们的原罪。
成熟的教育体系,都是从理论设想到初步实践,再到反复更正,最后使大部分人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工程。成熟的教育,都是把人的生存置于第一位,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的生存能力,让人生活得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