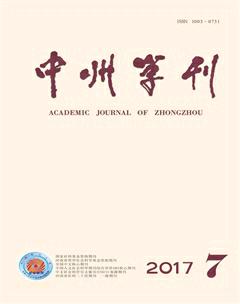汉魏洛阳城阳渠遗址与古代都城的生态水利建设
摘要:阳渠是伴随着汉魏洛阳故城的营建、改造、扩建而产生的水利配套工程,通过对周边河流的开发利用,并经过不断地增修、完善,其功能日趋合理,形成了独有的城市水利系统。在城市生活用水、防御、灌溉、泄洪、漕运及环境美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洛阳的城市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城市水利设施发展的典范。
关键词:汉魏洛阳故城;阳渠;城市水利
中图分类号:K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7-0110-05
“居中而治,四塞险固,山河拱戴”是中国封建王朝建都选址的既定理念。纵观历代都城,几乎无一例外地依山傍水而建,说明古代都城的选址对于以山川河流为载体的水源的高度依赖,其中还有对河流、池沼进行疏浚、截流、导引、改造等工作,使其能更好地满足都城对水源的需要。汉魏时期的阳渠就是伴随着洛阳城的营建、改造、扩建而产生的水利配套工程。有关洛阳故城阳渠的修造、改建及其功能,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①,但关于阳渠的建设对汉魏洛阳城市民生活和城市生态方面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本文拟对此方面做一讨论,以说明人工河渠在古代都城建设中对城市生活和城市生态所产生的影响。
一、汉魏洛阳故城的修建与阳渠的开凿
1.汉魏时期洛阳城的修建
汉魏洛阳故城修建始于周朝,周成王时期,先后命召公和周公规划营筑雒邑。“成王在丰,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②“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周公“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③。经过占卜,在涧水东、瀍水西之间和瀍水东的洛水之滨皆卜兆大吉。遂在涧水东、瀍水西、洛河北岸修建王城,作为周之东都,周王居之。周人又在王城东四十里处建都城,以迁殷民,史称成周。郑玄《诗谱·王城谱》称:“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今洛阳是也。”④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的洛阳城址在洛水以北,邙山以南,瀍水以西的地带。这也是汉魏洛阳故城建城之始。
近年来,有关考古工作者也对西周时期的成周城(洛阳城)进行了勘测,认为成周呈东西长方形,位于汉魏洛阳旧城城址的中部。其具体范围大约北到自东墙上东门至西城上西门的东西一线,二门附近南北向城墙有东西向小转折;南到东城墙望京门和西墙广阳门北侧各自的城墙转折处一线。经测量大致约合当时东西六里,南北五里。⑤
秦灭周后,洛阳城有所扩建,“洛阳城,周公所制,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侯,大其城。”⑥吕不韦向南扩修洛阳城,使其初步达到“九六城”规模。
东汉时期,洛阳城又有大规模的修缮和营建,东汉中期在北宫以北修建苑囿,直抵北墙,形成南、北两宫对峙。“(洛阳)城东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⑦东汉末年,洛阳城遭到严重破坏,献帝初
收稿日期:2017-05-19
作者简介:贾璞,女,河南省博物院研究部文博馆员(郑州450002)。
平元年(190),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于长安”“悉烧洛阳宫庙、官府、居家”⑧。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迁都洛阳后重修洛阳城和宫殿,建百官朝堂,营立太学,形成了都城的基本轮廓。到魏明帝时,开始了全面建设。《三国志·魏书》载:“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筑阊阖诸门”“于芳林园中起陂池。”⑨元帝咸熙二年(265),对洛阳城进行了增辟和扩建,增辟了国子学、明堂、辟雍、灵台,扩建了一系列园林别馆。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迁都洛阳。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决定在东汉、魏晋时期的宫城、内城基础上修建外廓城。“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⑩经大规模改建,都城形制为之一变。北魏之后,随着隋朝都城的迁址,汉魏洛阳城遂渐荒废。
由以上文献可知,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可从东周算起,直至北魏天平元年(534)废弃,时间累计达540多年。但由于东周考古资料缺乏,因此,习惯上多称之为“汉魏洛阳故城”。
2.阳渠的开凿及其称谓变化
汉魏时期的洛阳城位于伊洛盆地,其四面环山,地势北高南低,盆地内有伊、洛、瀍、涧(谷)等河流。洛河自西而东从盆地中穿过;瀍、涧(谷)二水于盆地西部纳入洛水;伊河于盆地中部会流于洛河。出于战略的考虑,成周选址在伊洛河之北,依山面河,由山麓至河岸,海拔高度缓缓下降,平均海拔在120—140米。洛水虽流量大,但河床海拔低于120米,因此,想要河流自主流入洛阳城很困难。而且由于季节性因素,洛河水量不稳,汛期水量增加,极易对洛阳城居民生活产生威胁。谷水和瀍水虽海拔相对较高,注入洛水前海拔高度达150米,但谷水距洛阳城较远,且穿越地段地势较崎岖,减弱了谷水的流量。因此,为了满足成周城用水的需要,势必要对周边河流、池沼进行疏浚、截流、导引、改造。阳渠就是伴随着成周的营建而产生的水利配套工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韦昭说:“洛水在王城南,谷水在王城北,东入于瀍,至灵王时谷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由此可知,周公旦营建王城和成周时,曾引谷水(涧河)从王城北(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北)向东,越瀍河至成周,再向东南流入洛河。此渠当有供王城、成周用水的作用,即为周阳渠。“城(洛阳城)之西面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偪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吕不韦。以是推之,非专周公可知矣。”《水注经·谷水注》载:“故李尤《鸿池陂铭》:鸿池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阳渠)左合七里涧”“阳渠水流经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阳渠水又东经亳殷南。”从中可以看出,李尤認为鸿池陂北岸的阳渠是圣王规划的。李尤、陆机、刘澄之、郦道元的观点吻合,进一步证实阳渠的始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西周、东周时期的文献对阳渠的名称没有明确描述,至东汉时期文献统称“阳渠”。曹魏、西晋时期,阳渠的称谓,分为城东、城西两部分。城西部分有“千金渠”“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等称谓,这些都是在原来阳渠基础上新修造的,当属阳渠的一部分。而城东部分,有“阳渠”“九曲渎”的称谓。北魏时期,城东、城西统称“阳渠”,环城阳渠和城南漕运渠道有“谷水”之称。
阳渠的修建为历代洛阳故城的供水、防洪、城市防御、农田灌溉、水运交通(漕运)、环境美化等提供便利条件,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功能及社会效益。
二、阳渠的功能
1.阳渠的供水、灌溉、防御功能
修建开凿阳渠主要是为了解决洛阳城城市供水的问题。前述对洛阳故城地理位置的分析已足以证明这一点。阳渠与洛阳城的建设相辅相成,是营建成周城之初就有的必备工程。此外,阳渠还在农田灌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战国策·东周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充分说明自西周、东周时期,阳渠已经作为农田水利设施来使用。为当时该地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灌溉条件。
东周时期,随着洛阳城的向北扩建,阳渠也在西周时期沟渠的基础上不断改造。《洛阳伽蓝记》记载:“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可见至少从东汉建武二十二三年起就已经可以“谷水周围绕城”了。至北魏,《水经·谷水注》记载了谷水(护城河)在洛阳城周围的流向,“谷水于雒阳城西北枝分,一东流迳金墉城北”,“迳洛阳小城北,又东历大夏门下”,“又东迳广莫门北”,“又东出屈,南径建春门石桥下”,“谷水自城西北枝分,其一水南注,自阊阖门而南”,“迳西阳门”,“又南迳西明门”,“谷水又南,东屈迳津阳门南”,“又东迳宣阳门南”,“又东迳平昌门南”,“又东迳开阳门南”,“谷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迳青阳门东”,“又北,迳东阳门”,“又北,入洛陽沟”。此记载已为现代考古勘查证实,此时洛阳城的护城河已非常完善,渠道四面绕城,既宽且深,其走向与城垣平行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宽约18—40米不等,这也使城市防卫能力有所增强。
2.阳渠的漕运功能
阳渠的“堰洛通漕”功能在东汉比较显著。东汉建都洛阳后,随着洛阳人口的不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同时,洛阳坐落于关东地区,接近粮食产区,周边河流众多,具备大规模漕运的条件。因此,东汉建都后立即着手解决京都的供水和水运问题。据文献记载,东汉时为漕运而对阳渠的修建至少发生过三次。
建武五年(29),从周王城故址以北(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北),筑堰开阳渠,“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当时引谷水东流,经洛阳城下,在今巩义市附近东注于洛,但因水源不足、渠道太浅等原因,未能成功。现代的考古勘查对此进行了证实,“城东阳渠东段,渠浅且窄,底部无淤泥流水痕迹,当是此次工程的真正遗迹”。建武二十三年(47),对阳渠进行了第二次修建,“建武二十三年,纯为大司空,‘明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水经注·谷水注》也记载此事:“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是渠今引谷水,盖纯之创也。”从文献可以看出,王梁开渠所引的河水为谷水,张纯引的为洛水。王梁开的旧渠,从洛阳城北流过,在东北城角再南流,至建春门石桥下。张纯开的新渠经过城西白马寺东,南流从西南城角向东折,再由东南城角折向北,也至建春门石桥下。两渠汇合,再向东经过偃师城南,注于洛水。张纯这次穿凿阳渠,达到了堰洛通漕的效果。为京都范围内的灌溉和运输提供了方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城东阳渠段是漕运畅通的关键,但由于地势较高,常淤积严重,影响水流。因此各朝都十分重视对城东阳渠的疏浚。阳嘉四年(135),汉顺帝下诏书兴修上东门外的漕渠和石桥。“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撰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阳嘉四年,在阳渠的旧址上,城东阳渠再次进行改造,渠道被加宽、加深。此记载已被现代考古勘查证实,发现“城东阳渠西段比东段宽而且深,中途与鸿池陂北侧打通并汇入”“且鸿池陂北壁自然冲刷的痕迹扩大”“从此可以看出此次阳渠的改道,利用鸿池陂与洛阳城南的渠道汇合,非常成功地打通了一条重要漕运渠道。”
阳渠经数次的修造之后,其城东、城西的行经路线及功能已基本确定。城西阳渠主要为引谷入洛工程,以保障洛阳城城市供水、农田灌溉所需;城东阳渠主要为堰洛通漕工程,引入谷水过城东,南经鸿池陂,再向东至堰师东南入洛河,从而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通过阳渠连接黄河、汴渠、淮河的一条水运航线。把洛阳同中原、江淮等农作物的主产区更紧密地联结起来。彼时洛阳水运商路已相当畅通,“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也对洛阳到江南水路商运有过记载:“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阳渠的“堰洛通漕”使洛阳成为当时最大的漕运中心,促进了洛阳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巩固了洛阳的政治中心地位。
曹丕称帝定都洛阳后,为恢复、发展因战乱破坏的经济,先后派王昶、桓范、司马昭、司马望、侯史光、毋丘俭等主持洛阳屯田,“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因此,当时的水利修建多与屯田及漕运相关。比较著名的是重修千金渠和五龙渠,再开新堨,修代龙渠(即九龙渠)。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陈协凿运渠从洛口入,经巩县至九曲渎,又西至洛阳东阳门,会于阳渠。”魏明帝太和五年(231),都水使者陈协在原来阳渠的基础上凿通了千金渠。用千金渠的渠道,引谷水东流经洛阳城北,分一支入城,然后自城北转城东和阳渠会合,由偃师入洛,以增加洛水的水量。此外,陈协还主持了千金堨的重修,引水溉田,取得很大经济效益。《洛阳记》云:“千金堨旧堰谷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筑此堨,更开沟渠,此水冲渠,止其水,助其坚也,必经年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记之云尔。盖魏明帝修王、张故绩也。堨是都水使者陈协所修也。”此中提及的“王、张故绩”,即指东汉初年王梁修建的“引谷水以溉京都”之洛阳渠和张纯主持修建的“引洛水为漕”的阳渠。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那时洛阳城东太仓附近的码头是当时中国大型内河航运港口之一,停满了各地至洛阳的漕船,可见当时漕运规模之大,经济之繁荣。西晋永嘉元年(307)李矩等又重修千金堨,“以利漕运,公私赖之”。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继续对千金渠进行修浚,仍引谷水经阳渠绕城四周。
3.阳渠的防洪功能
阳渠还兼具泄洪和防洪功能。《水经注·谷水注》云:“千金渠为谷水经流其下,开沟渠五,而南出者曰五龙渠,泄瀍暴涨之水,大则五龙渠不及泄,故更于西开泄,名代龙渠,是五龙、代龙皆与千金相属。代龙渠即九龙渠也。”魏都水使者陈协修千金渠(阳渠),分五个之渠,南面的五龙渠就有泄洪的作用,但水大时,五龙渠泄之不及,遂在西面增开代龙渠,又称九龙渠。可见当时的千金渠(阳渠)的修建者已经充分考虑到其防灾的作用。据统计,从汉至北魏四朝都洛的333年间,洛阳共发生16次水灾,平均21年1次。水患最频繁的是东汉建武七年(31)至熹平四年(174)的144年间,有水患11次,平均13年1次。但自魏明帝太和五年(231)重修了千金渠(阳渠)之后,至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的37年之间洛阳城无重大水灾见于文献记载。可见,千金渠(阳渠)的修建极大地缓解了洛阳城的水患。
4.阳渠的环境美化功能
阳渠的修建也为宫廷和城内外公私园林提供了充足水源,起到了城市环境美化的作用。东汉时,通过阳渠把水引入城内,利用水资源以及洛阳的地势特点,修建了多座富有特色的苑囿、园圃。如上林苑、灵囿、芳林苑、西苑、鸿德苑、显扬苑、长利苑、灵琨苑、菟苑等,皆为帝王、贵臣郊猎之苑。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城内又兴建了许多园林,如,西游园、华林园等。此时的阳渠经过修造分出几条支渠,从洛阳西城的阊阖门、西明门,北城的大夏门等流入城内,与城内的泉池,如翟泉、天渊池、绿水池、九龙池等沟通。从西城门和北城门流入城内的渠道,又穿城而过,从南城门和东城门流出城外,仍与环城的阳渠水相通,形成了全城环水的美丽风光。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太仓南有翟泉,周回三里。”“水犹澄清,洞底明静,鳞甲潜藏,辨其鱼鳖。”“泉西有华林园,高祖以泉在园东,因名苍龙海。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魏)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华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蜕阁,乘虚来往。至于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驾龙舟鹚首,游于其上。”“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凡此诸海,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连阳渠,亦与翟泉相连。若旱魃为害,谷水注之不竭;离毕滂润,阳、谷泄之不盈。至于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三、阳渠的弃用与汉魏洛阳城的荒废
曹魏之后,西晋和北魏各朝也多次对阳渠进行修造。据《水经注·谷水注》记载:“水积年,渠堨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西晋秦始七年(271),洛阳发洪水冲毁原有渠堨,遂对阳渠再次整修,将谷水之上的千金堨加固、加高。《魏书》载:“太和二十年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历代对阳渠渠道的频繁疏浚,一方面反映了各朝政府对阳渠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汉魏洛阳城引水渠道不断淤积不够畅通的事实。这一点已被现代考古证实,洛阳城城东建春门外,深达10米之处,仍为淤土。
为解决渠道的淤积问题,除了疏浚外,还需要不断增加洛阳城南堰坝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把洛水引入地势较高的上东门阳渠渠道。高筑堰坝虽然便于引入洛水,但同时被抬高的洛水也使得洛阳城,尤其是洛阳城南面更容易受到水患的威胁。段鹏琦在对洛河故道进行现场勘探之后指出,北魏在洛河之上修筑堰坝甚至造成洛河河道脱离原来故道,转向东北流向洛阳城南。为了躲避水患的威胁,洛南居民纷纷搬离。北魏后期,洛河泛滥更为频繁,造成洛阳城南了无人家的局面。
此外,从汉魏洛阳城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存在战乱等因素,但从东周到北魏,洛阳的人口总体是呈增长趋势的。特别是到了北魏全盛时期,洛阳城的人口达到了最高峰。“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这主要得益于北魏迁洛后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政策和安定生活环境。但是,日益增加的人口使得洛阳城原有的供水面临极大的考验。迁址以寻求更多的水源已成为城市管理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隋朝时城址两移至今洛阳市区一带,汉魏洛阳城遂渐荒废。隋的迁都,除了战乱对洛阳的破坏外,水源的困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迁址后,伊、洛、瀍、涧四条水系均汇聚于隋唐都城洛阳,成为整个洛阳盆地水源最丰富的地区。
洛阳城的生活用水和漕运等主要是通过以阳渠为代表的城市水利设施的开发利用来解决的,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城市水利系统。阳渠通过历代的不断增修、完善成为维持和延续汉魏洛阳故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阳渠与洛阳故城的共生互辅关系成为我国古代城市水利发展的典范。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与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察》,《考古》1993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与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王学荣:《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7期;五井直弘著,姜镇庆,李德龙译:《中国古代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3—173页;周剑曙,陈华州:《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河洛春秋》2008年第3期;等。②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清人注疏十三经附经义述闻》第5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70页。③马将伟:《尚书译注》,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1、161页。④马骕著;王利器整理:《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4028页。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⑥桑永夫著:《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页。⑦皇甫谧撰;陆吉等点校:《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第59页。⑧王钟麒编:《三国史略》,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7页。⑨陈寿撰:《三国志》上,中华书局,2011年,第88页。⑩魏收:《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4、180页。周勋:《论千金堨与魏晋时期洛阳城水利关系》,《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洛阳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交通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康仙舟,高献中,王西明著:《偃师风土》,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40、52页。刘向编集;贺伟,侯仰军点校:《战国策》卷一,齐鲁书社,2005年,第3页。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6頁。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72、26页。孔祥勇,骆子听:《北魏洛阳的城市水利》,《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周剑曙,陈华州:《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河洛春秋》2008年第3期。段鹏琦著:《汉魏洛阳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赵永复著:《鹤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3、182、175、176、176、176页。范晔:《后汉书上》卷四十九,岳麓书社,2008年,第594页。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中国水利史稿上》,北京水利出版社,1979年,第269页。嵇果煌:《中国三千年运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中国水利史稿上》,北京水利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郦道元:《水经注疏(中册)》卷十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81页。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88页。杨衒之撰,韩结根注:《洛阳伽蓝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58、20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察》,《考古》1993年第7期。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05页。
责任编辑:王轲
Luoyang City Ruins of Han and Wei Dynasty and the Ecologic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Jia Pu
Abstract:Yang Canal is a hydraulic engineering accompanied by the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extension of Luoyang city in Han and Wei dynasty. Its fun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easonable to form a unique city hydraulic system,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urrounding rivers, and continual alteration and improvisation.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water for life, defense, irrigation, flood discharge, water transport of grain to the capital and Landscaping,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city, and became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ity hydraulic engineering.
Key words:Luoyang City in Han and Wei Dynasty; Yang Canal; City Hydraulic Engineering
中州学刊2017年第7期略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2017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17
第7期(总第247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