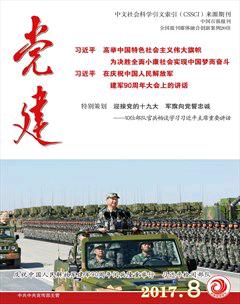国魂在上
贺捷生
2017年5月下旬,回到母亲的故乡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热心的父母官和朋友们想我所想,在修葺一新的烈士陵园帮我举办了一个庄重而又简朴的祭奠仪式,祭奠我在80多年前牺牲的两个亲舅舅蹇先为和蹇先超。
实话说,我此行最大的动力和愿望,正是虔诚地站在两个舅舅的墓碑前,向他们深深地鞠三个躬,再亲手给他们敬献一个花环。
1

过了80岁,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在一天天衰竭和枯萎。春节期间因肺部出现阴影,大年初二就住进了医院。49天后出院,医生反复叮嘱要好好静养。谁想到我足不出户,在自己的卧室里还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有多重呢?我住四楼,连住在三楼的人都听见了我的脑袋嘭咚一声磕在地板上。从此我说话经常卡壳,一些关键词,话到嘴边怎么也想不起来,说不出来。保健医生摸着我后脑勺留下的一个大肿块,心有余悸地说:“老年人最怕摔跤了,许多人都是一跤摔下去再也起不来了。近期哪儿也不能去,更不能出远门。”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的故乡慈利来人了,说他们重修了烈士陵园,特地为我的两个舅舅蹇先为和蹇先超烈士各立了一面大理石墓碑,希望我回去看一看。再就是,省里在慈利溪口镇我写过文章的那棵千年古樟下(载《人民日报》2012年9月5日《去看一棵大树》),举办“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启动仪式,希望我前去为徒步健儿们授旗。
听见这话,我坐不住了。80多年前,离开我外公蹇承宴和故乡出去革命的儿女,共4个,他们是他的二女儿、我的母亲蹇先任;他的大儿子、我的大舅蹇先为;他的三女儿、我的幺姨蹇先佛;他最小的儿子、我的小舅蹇先超。不幸的是,我的大舅和小舅全都牺牲了,一个牺牲在残酷的湘鄂西斗争时期,一个牺牲在长征途中;而分别嫁给原来的红二、六军团,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再后来的八路军一二零师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的我母亲蹇先任和我幺姨蹇先佛,这对著名的“红军姊妹花”,却不仅盼熬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且雙双进了北京,并活了很大岁数。如今,活到96岁的我母亲已不在人世了,但我幺姨蹇先佛依然活得好好的,足足103岁了;可惜她最近病了,她的独生子、我的表弟萧星华必须守在家里照顾她。这样,能抽身去慈利参加两个舅舅祭奠活动的,就只有我这个82岁的老太太了。因此,我对母亲的故乡人说:“我去,谁让我是慈利的外孙女呢!”
2
慈利县烈士陵园坐落在零阳镇南部的一座山冈上,由白帆一样两根修长的水泥柱组成的烈士纪念碑,像一支耀眼的箭射向苍穹。上刻县委书记邱初开亲笔题写的“慈利县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纪念碑左面的山坡上,310面仰天而卧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整整齐齐、层层叠叠地从山脚铺上山腰。远远看上去,一排排按统一规格的长廊和墓碑修筑的墓园,就像一排排书架,陈列着一部部浩气长存、肃穆而又厚重的典籍。莽莽苍苍浓郁得好像随时能滴出绿汁来的树木,从左右和上方三面簇拥着墓园,突出“青山着意埋忠骨”这样一个深邃的主题。
因为唇齿相依,同我父亲的故乡桑植一样,我母亲的故乡慈利,也是一片峥嵘的大地,光辉的大地。我父亲贺龙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从事革命斗争长达8年,无数次出没这片土地,在它的村村寨寨穿梭、战斗、隐藏,一批批征集兵员和粮食,先后建立了广福桥、溪口、国太桥、三官寺等革命根据地和江垭、三合口、杉木桥、龙潭河、高桥等大片游击区,使其成为湘鄂西、湘鄂川黔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盘,红色区域达63%。县第五区官地坪,长期成为红军休养生息的秘密营地。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木黄会师后,发动湘西攻势,部队直插作为湘西腹地的慈利溪口镇,建立了著名的大庸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省委溪口苏维埃政权。在溪口镇澧水河边的那棵千年大树下,我父亲一次就收编了当地民间武装李吉儒部达上千人,在群众中传为佳话。我父亲带领长征的红二军团,就是由桑植和慈利为主的湘西子弟组成的。《慈利县志》记载,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慈利有6万人参加革命,5000多人参加红军,上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460名,其中在湘鄂西、湘鄂川黔斗争和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占1091名。让我骄傲的是,在这1091名烈士中,就包括我的大舅蹇先为、小舅蹇先超。
面对烈士纪念碑的祭奠仪式举行完毕,一路搀扶我的县委书记邱初开昂起头,指着半山腰一排排烈士墓碑上方竖着的两幅分别写着“缅怀先烈爱国魂”、“幸福不忘英雄史”的巨大标语牌,对我说:“将军大姐,认得清那两幅巨大标语牌上的字迹吗?您两个舅舅的墓碑就立在‘国魂二字下面最高一层碑林里。不过,从我们脚下攀到他们的墓碑前,有100多个台阶,您这么大年纪,要上去吗?”

我说:“当然!我就是奔着两个舅舅来的,哪有来了不往上爬的道理呢?”那天阳光灿烂,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陡峭的被雨水洗得发黑的水泥台阶晒得滚烫滚烫。我在众人的簇拥下爬了十几个台阶,汗水像雨滴那样落下来。虽然我是被人们架着走、推着走的,两腿也止不住发软、发颤。细心的邱初开书记早让人为我准备了塑料凳子,只要我累了想歇口气,凳子就塞在我的屁股底下。记得我坐下来休息3次,才终于攀到我两个舅舅静静斜卧着的两块黑色大理石墓碑前。
3
大舅蹇先为是慈利县较早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1926年春,只有15岁的他被外公送去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受到比他年长11岁、也曾在兑泽中学读过书的溪口镇同乡张一鸣的影响,踊跃加入青年团,第二年转为共产党员。当他有了自己的信仰,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立刻给在县里读书的二姐、我的母亲蹇先任写信,鼓励她参加革命。接到信后,我母亲也离开家乡,到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大舅成了她入团入党的当然介绍人。
1927年春,大舅少年老成,组织上放心大胆地派他去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学习。5月21日晚,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亲眼看到反动军队血洗省工运讲习所等革命机关。鉴于许多党团员对事变措手不及,兑泽中学党组织负责人周惕让凌晨跑回学校的大舅担任交通员,走街串巷传递情报。不想他的身份也暴露了,党组织通知他带领我母亲回乡暂避。
那时,我外公的生意做得有模有样了,在街上开了两个作坊和两家铺子,回到慈利的大舅理所当然做了家里的账房先生。实际上,大舅是利用家在城关镇的特殊条件,密切联络失散的党员,积极进行组织活动;同时以帮助外公经商为名,趁外公和外婆不注意,从他们的钱柜里筹措经费,上交给党组织。1927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派津市特支书记李立新夫妇来慈利恢复党组织活动,他一次从柜台提走一百块大洋,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交给这对夫妇。外公开的作坊和铺子毕竟是小本经营,发现上百块大洋不知去向,严厉追问大舅钱的去处。大舅不回避、不躲闪,坦然对外公说:“父亲,你从小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难道会相信我拿出钱去做坏事?你老人家不是天天反对苛捐杂税、盘剥压榨吗?儿子从长沙回來,做的事就是和那些人过不去。”
外公算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听完大舅的话,还是吓了一跳。他默默地望着大舅,知道这个从长沙回来的儿子参加了刚刚血流成河的被国民党镇压的那个政党,然后拍拍他瘦弱的肩膀说:“先为啊,你做的事既然于国有益,那就大胆去做吧,爹不拦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做这种事是要掉脑袋的,应该处处小心,步步小心。”大舅点点头说:“父亲放心,儿子会保护自己的。但我既然认定了这条路,就会走到底。”
1928年春节前后,大舅和我母亲在险恶的秘密斗争中,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耻、残暴和无可救药,从一介文弱书生,彻底变成了拥护并热情参与武装斗争的战斗者。在这个严寒的冬天,姐弟两人不辞而别,毅然投入到石门南乡年关暴动的行列,公开举起了“打土豪杀劣绅”的旗帜,声势涉及慈利县境。驻防常德的国民党军迅速开到了石门,包围了农民和进步学生占据的石门中学、石门女校和第一完小,逮捕杀害了17名共产党员,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石门惨案”。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开到慈利,到处抓人杀人。在这种情况下,大舅和我母亲在家中无法待下去了,不得不分开逃离县城。大舅逃到了太浮山,参加了慈利著名的共产党人袁任远等人领导的暴动队。这支队伍过了数月,遭到国民党军队反复“围剿”,只好化整为零。大舅接着到了桑鹤边界,参加了我父亲贺龙创建的红四军;我母亲则隐藏在相对平静的杉木桥镇舅舅家,继续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
大舅参加红军后欣喜地发现,他在长沙兑泽中学投身革命的引路人、慈利早期的共产党人张一鸣,正出任红四军第一师党代表,已成了我父亲贺龙的左右手。大舅有文化,脑子灵活,又有地下斗争经验,自然受到张一鸣的器重,很快被提拔为书记官,两个人从此形影不离。
1929年8月,我父亲贺龙和张一鸣率领红四军主力由桑植出发,向大庸、慈利推进。25日,红军占领慈利江垭,27日进驻杉木桥。在欢迎的人群中,大舅与藏身在杉木桥镇民间的我母亲意外相逢,姐弟俩喜出望外,久久拥抱在一起。张一鸣在地下斗争中与我母亲多有接触,知道她是远近闻名的女才子,又是湘西难得一见的女英雄,提议把我母亲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我母亲学不上了,家不回了,立志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此时有了直接当红军的机会,可以真刀真枪地同反动势力在战场上见,自然求之不得。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她从地方转入部队,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成了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红军指战员们包括我父亲贺龙在内,亲切地称她“蹇先生”。
我母亲蹇先任绝没有想到,就因为她在长沙读过书,见过革命斗争大世面,人又长得漂亮,在当年红军打下慈利县城后,便成了贺龙的夫人。6年后的1935年11月,啜饮着战争的血雨腥风,他们一个成了我父亲,一个成了我母亲。
大舅参加红军后,亦文亦武,英勇善战,让在革命斗争中发现、培养和提拔他的张一鸣对他呵护有加,行军打仗总把他带在身边。大舅也对这位兄长般的领导心悦诚服,甘愿在我父亲和他的指挥下冲锋陷阵,赴汤蹈火。1930年7月4日,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我父亲为总指挥,张一鸣被任命为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这年的9月,红二军团攻打沙市,敌人依据坚固的堡垒和城墙坚守不出,死死顽抗。红军打进沙市东街又被猛烈的弹火挡回来。我父亲命令张一鸣率红十团从后街发起突袭,但敌人的增援部队从天上和地面赶到了。从天上飞来的两架飞机在一阵狂轰滥炸后,对从后街发起冲锋的红十团展开低空扫射,致攻城战斗陷入僵局。9月5日,张一鸣到前线视察,一串子弹飞过来,他应声倒下。大舅冒着枪林弹雨发疯般地冲上去,把他背下来。让大舅痛心的是,一颗子弹击中了张一鸣的头部,他再也没有醒来。
1931年春夏之交,已是湘鄂边红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大舅,调任鹤峰特委巡视员,转入地方工作。次年6月,国民党军对苏区发动凶猛的第四次“围剿”,川军重兵向湘鄂边进攻,驻鹤峰的红军独立团战斗失利,鹤峰县城落入敌人手里。大舅和中共鹤峰县委书记伍伯显带领县委、县苏维埃机关30多人,向祥台转移,那里与县城仅一山之隔。在转移途中,不巧与一营敌军遭遇,队伍被冲散。此后,他隐蔽在一个叫曹家沟的村子里,但没几天,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第二天,被团防杨卓堂杀害于鹤峰赤树坪枇杷树台,时年21岁。
新中国成立后,大舅的遗骸被找到,迁葬于鹤峰县烈士陵园。
4
写到这里,我不禁悲从心来:大舅蹇先为虽然早在1932年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牺牲在湖北鹤峰的异地他乡,但他毕竟还有掩埋尸骨的一个坟茔,一个供亲人和后辈前来吊唁的地方;而我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小舅蹇先超,却连一个土丘、一块墓碑都没有。
小舅蹇先超与幺姨蹇先佛一块参加红军。那是1934年12月26日,父亲贺龙率领红二军团与萧克、任弼时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两个月后,第二次攻克慈利县城。父亲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我外公蹇承宴;同去的还有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等红军领袖。
当天中午,父亲在一家餐馆邀请岳丈,也就是我外公蹇承宴及其家人,由萧克、任弼时、关向应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阿姨作陪。父亲问起家中境况,外公忍不住笑道:“女婿啊,先任、先为姐弟二人都跟你当了红军,丢下老四、老五两个,在家也待不住了。”意思是,我幺姨蹇先佛、小舅蹇先超也想参加红军。我父亲和几个红军将领忙不迭地点头,陈琮英阿姨这时还跟我外公套起了近乎,她说:“陈老倌,你这话当真?可不能反悔啊!”后来人们才知道,几个红军将领欢迎我幺姨和小舅当红军,是红军急需扩大队伍,每天都在招兵买马。再说,我幺姨和小舅都是读过书的人,我幺姨还上过长沙衡粹女子艺术学校,能写会画,是红军紧缺的宣传鼓动人才。至于陈琮英阿姨和我外公套近乎,是想到我幺姨与素有红军才子之称的萧克将军天造地设,想给他们牵线搭桥。虽然这是后话,但不出几天便成了事实。
嫁给我父亲贺龙5年,跟着他从血里火里走来的我母亲,听着外公又要把幺姨和小舅往红军队伍里送,忍不住躲出去哭了一场。因为我母亲知道国民党反动势力太强大了,参加红军无异于以命夺命。而且,她的大弟、我的大舅蹇先为,此时已经牺牲两年了,连尸骨都不知道埋在哪里。母亲不晓得外公是否得到了大儿子的死讯,但听见他又把幺姨和小舅送去当红军,她太为外公感到骄傲和心痛了。
小舅蹇先超只有15岁,还是一个绒毛未退的小孩子,他是看見哥哥姐姐当了红军,哭着喊着也要去当红军。到了部队后,经过短期医护常识培训,被分配到红二军团医院当护士。长征出发前,为充实和加强一线部队的医护工作,他被调到卢冬生任师长的红二军团第四师野战医疗队任战地救护员。部队出湘西,穿云贵高原,一路喋血前行,他单薄的身影无数次在弹火纷飞中匍匐和穿梭,越来越成熟。
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支与慈利蹇家的命运休戚与共的队伍。因为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我的父亲贺龙,是蹇家的二女婿;这支队伍的副总指挥、我的姨父萧克,是蹇家的幺女婿。跟随着这支队伍跋山涉水前进的,不仅有蹇家同胞三兄妹蹇先任、蹇先佛、蹇先超,还有蹇家刚出生和未面世的外孙女和外孙子。都知道,当时我作为蹇家的外孙女,生下来才18天,就被父母放在背篓里,背着去长征;而我的表弟萧堡生,此时仅仅作为一个小小的胚胎,孕育在我幺姨蹇先佛的肚子里。
长征有多么艰难困苦,我没有必要再形容了。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外公的蹇家,加上我父亲的贺家,我们两家参加长征的亲人,合起来达十几口,但即使都在同一支队伍里,走在同一条路上,也难得见一面,更谈不上受到特殊保护和照顾了。具体地说,我父亲贺龙和姨父萧克,他们两人重任在肩,分别带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斩关夺隘;我母亲边做宣传鼓动工作,边背着我,跟着红二军团赶路;我幺姨挺着一天比一天大的肚子,运用她写得一手好字的特长,沿路写标语,艰难行走在红六军团的队伍中;担任战地救护员的小舅蹇先超,与红二军团四师的战友们形影不离。母亲三姐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只能在遇到熟人时,相互捎个口信,或者写一张便条辗转带给对方。
1936年4月25日,红二军团以我小舅所在的红四师为先锋,从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连续奋战三昼夜,红二、六军团近两万人全部到达江对岸。接下来,就要翻越海拔5396米的中甸雪山了。虽然部队及时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但从长江以南的湘西走来的部队,谁也没有翻越西南大雪山的经历,还以为打个冲锋,哈几口寒气,就能爬过去。许多人在抢渡金沙江时,把随身背着的棉衣棉裤和毯子泡湿了,长途奔袭时又大汗淋漓,索性穿着单衣轻装前进。想不到担负在雪中开路的红四师,在雪山上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寒冷,行进中不少官兵因为疲倦、劳累和饥寒交迫,一坐下来就被冻僵了。
我母亲背着我于4月30日翻过中甸雪山。5月初,红二军团到达得荣县县城,先期抵达的红四师师长卢冬生向军团参谋长李达报告部队减员的情况后,专程找到我母亲,向她检讨说:“先任同志,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弟弟。我身为师长没有尽到职责,在过雪山时全师减员一百余人……我向李参谋长表示,愿接受军团首长的处分。”
卢冬生是我父亲南昌起义后一直带在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与我父亲母亲情同手足。听说红四师过雪山时减员严重,母亲心里一沉,不由颤声问卢冬生:“卢师长,你就直说吧!是不是我弟弟也牺牲了?”卢冬生哽咽道:“是的,先超同志虽然年纪小,但他身为战地救护员,在雪山上跑前跑后救护战友,最后因体力不支,冻死在雪山顶上。”
听到这个结果,母亲久久无语,两眼泪水夺眶而出。许多年后她对我说,我外公把幺姨和小舅交给红军,当然希望她这个当姐姐的怎么把他们带出去,再怎么带回来。而她作为这支军队总指挥的妻子,也有能力保护年幼的弟弟妹妹。但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如果在艰难时刻护着自己的亲人,怎么把来自天南海北的官兵团结起来,带领他们去冲锋陷阵,向死而生?因此,对于小舅的死,母亲虽然感到痛心、内疚,心里想,将来怎么向外公交代?但她知道红军不分亲疏,必须冷静接受这一事实。她最大的遗憾是,小舅太小了,而且牺牲在红军一去不返的雪山顶上,尸骨无存,连一抔土、一块碑石都没有!
许多年后,我以父母亲背着我长征的亲身经历,为解放军出版社写了以《远去的马蹄声》为题的大型绘本文字,特意请著名画家沈尧伊先生为我小舅画了一个坟墓:在苍凉的雪山上,小舅被埋在一个突兀的雪堆里,雪堆上压着一顶红军八角帽;我父亲牵着马,我母亲用背篓背着我,在猎猎雪风中,低着头,恋恋不舍地向小舅告别。画面表达了我对小舅蹇先超的深切怀念,希望80多年前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小舅,有一个温暖的雪堆安息,有一顶红军八角帽作为他埋葬在雪山的标志。雪堆上那顶有着红五星的八角帽,也算是他的墓碑吧。
5
大舅蹇先为和小舅蹇先超牺牲80多年后,得知故乡慈利在新修烈士陵园的时候,为他们双双立了碑,让两兄弟的英灵穿过80多年风雨沧桑,重新相聚,毗邻而居,读者能想到我有多么激动和欣慰!
更让我感动的是,县里的有关部门别具匠心,不仅把大舅和小舅的墓碑立在一起,让他们从此能日日夜夜回顾和诉说兄弟情谊,而且把他们的墓碑立在陵园的最高处,让他们从此每天高高地俯视着故乡一天天的繁荣和富足,走向他们在生命最后一息曾经苦苦憧憬的未来。巧的是,兄弟俩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正好顶着“缅怀先烈爱国魂”那块巨幅标语牌的“国魂”二字。我觉得这应该是革命烈士们在冥冥之中,对我们的一种昭示,一种启迪,一种期待。
是啊,国魂在上!我们这支军队诞生90年了,新中国诞生也近70年了,当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歌猛进时,谁都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初心,忘记那些为了今天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所以,当我拖着80多岁衰竭和枯萎的躯体,千里迢迢回到母亲的故乡;当我在烈日下来到有我大舅和小舅陵墓的烈士陵园,再辛苦,再疲倦,我也要自己走;再高,再陡的阶梯,我也要自己往上攀……
80多年后,我的两个舅舅的事迹,通过《党建》杂志与读者见面,是蹇家的福分,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应该知足了。
题图:沈尧伊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