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客
张怡微
春丽随丈夫何明在这间社区照相馆工作已经第七个年头了。要说挣到的钱,几乎都做给房东。要说是感情,无非是交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知道了一些社会上的奇闻异事。何明是个保守人,许多事看不惯,他一直帮老人做旧照翻新,直到他们猝然离世,才发现照片里的女生根本不是老人的原配夫人,赊的账也不好去要了。尽管如此,何明还是将这些青春里的爱或是暮年里的慕统统归档放在抽屉里。春丽喜欢看照片里的客人四目有情、暧昧八卦,何明却常常对自己照相馆的“受众群”感到失望,他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和自己当初从贸易公司离职创业的初衷是不太一样的,他一直以为自己爱好摄影多过于包容眼下这些千奇百怪的摄影对象。但偶尔也有温馨的慰藉,如独生子出洋留学多年,何明看到相仿年纪的男孩子过来店里拍护照照片,到底还是移情,心里想得很。怎么送他走的,机场怎么道别,甚至憋着尿都要目送儿子直到通道尽头,历历在目。但春丽知道,丈夫宁愿少收顾客十块钱,都不愿意用APP给儿子传一段语音。男人就是这样犟。
春丽其他大小事都不管,什么打灯、修片、裁照、覆膜、贴相本,她自觉年纪大了、笨手笨脚,统统都不想理会。她只管账,顾客们满面春风夸老板娘又年轻又漂亮,她也客客气气送往迎来,笑说:“我儿子都在美国读硕士班咧,他都靠成绩拿奖学金的。”得意的利剑一石二鸟。但是议价这种事,无论说多少好话,在她春丽这边都是行不通的。为此,她和何明经常争执,又数度和好,本来也就是十几二十块的事。因而社区中,想还价的客人都要趁春丽不在的时候到店里找何明,不想还价的客人反倒是觉得还是春丽笑盈盈比虎着脸的何明态度好。这个奇异的平衡就这样默默维系着,春丽和何明心里都明白,谁也不说破。
每周,春丽还要抽两天时间早起去看独居的老母亲,和这间不赚钱的照相馆相比,还是时日无多的母亲要紧。她出门时,何明会睡眼惺忪在床上喊一声:“慢点走,坐捷运。”春丽则大声回答:“早饭在锅里哦。”为了省下车钱,又为了排解无聊,春丽都坐公车,顺道看看风景、想想心事。捷运黑漆漆又喧嚣,让人喘不过气。春丽想过,即使将母亲接到身边来住,睡在儿子的空房间里,也是无用。他们夫妇俩还是要出来店里守着相机维持生计,何明年纪还轻,又没有退休金。自己虽然已经退休,但到底钱不经花。两人要上班,全凭生意好坏,没有固定薪水,房租倒是一个月都不能欠,还有一个在美国帮人家麦当劳点餐勤工俭学的儿子。于是,还是没有人能二十四小时在家陪伴母亲。春丽一直对何明说:“等妈妈眼睛看不见了,不能自己做饭,我就接她过来住吧。”
何明自然希望老岳母眼明心亮到永远。
春丽暗地里知道,何明也想接自己母亲一起住。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店又不赚钱,他指望春丽提出来。但春丽总放不下自己家。如今两个老妇人尚能生活自理,一切就杠在未知里,也是无奈的平衡。
想到他们的老顾客秀芬去年沉着脸来店里,春丽照例寒暄:“上周看到你爸爸过来公园散步呢。”秀芬说:“春丽,我来就是为他。”她于是从包包里取出一张黑白照片,春丽心里一紧。
“我爸爸没了。”秀芬说,“最后一次麻烦你们,做个像,配个框。”何明也透着老花镜向外打量憔悴的秀芬。
“春丽,多去看看你妈妈。真的,我一个礼拜看爸爸两次,上次我刚走,只有两天,再开门,房间已经有味道了。他摔在客厅里,没站起来……我很内疚,原想追思会要叫你们一起来,我们家亲戚少。现在也不办了,我怕人家说我照顾不好……”
秀芬像是要哭,但比哭更严重的,是她后来真的再也没有来过照相馆。她的内疚看来是很重的。春丽挺想念秀芬的,尤其是每周两次看望母亲的路途中。
“这种事怎么说呢,真的怪不到秀芬。她已经算是孝女。”何明说。他也是顺便在劝慰春丽。男人的感情和女人不一样,何明从来不会和母亲耳鬓厮磨,也不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话。但对春丽来说,这种故事最听不得,隐忧是永恒的愁云。
如今时代变化太快,大部分人都有家用打印机冲洗照片。更多的人拍摄千万张数位照片都不会想到要洗出来。但也有例外,有老妇人就带着SD卡里上百张旅行照片,对何明说:“我眼睛看不清楚,你帮我挑十张吧,我相信你。”如果生意不忙,这些繁重的活,何明也耐心帮着做,顺便还要听老人说自己子女多孝顺,可再孝顺,就连帮忙挑照片这种事,竟都要外人做,春丽听听就笑笑,不忍心伤害老人家。
其实何明的主要业务,接不到婚纱、接不到婚宴,倒是帮老人旧照翻新、制作遗像,或者是帮老人带的孙辈拍百日照、全家福。只要能制作一本相册,何明修个十八张相片,就能有千余元利润。至于证件照,或者冲印照片,反倒是不赚钱的,全当做便民、做好事。
生意冷清,春丽有天看不惯说气话:“人家老公创业是发财以后再做好事,我老公目光高远,直接不去赚钱尽做好事。”说得何明有点不悦,也给她戳回去:“人家老婆是二婚温良恭顺抬不起头,我老婆是二婚凶得很,倒活像我是二婚。”春丽被他气到,一时语塞,想到年轻时候被前夫欺负、千辛万苦把儿子抚养大又送去美国、老母亲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眼泪就哗哗掉下来,做人真是没意思。这时老贾推门进来,看到这一幕,惊了,又想退出去。尴尬得要命。
“老贾啊,来,没事的。”何明说。
老賈是店里的老客人,也是春丽最不喜欢的那一种爱聊天、不做生意的闲客。开店时日久了,春丽和何明各有自己的“拥趸”。春丽喜欢秀芬这种,来就是要做成一笔生意、且不讨价还价、顺便还能聊一点煽情的家长里短的客人,而何明倒是不讨厌像老贾这样每个月只拿一张旧照来修、一年只做一本相册的顾客。老贾是退伍老兵,一生传奇。心里走过的万水千山,老来什么都看不出来,好在老照片会说话。老贾倒是不太提及自己的当年勇,一些关键的时期过后,他也不说政治,总说老婆孩子。他拿来修的照片,有的有人,有的没有。如大女儿念小学一年级算术比赛的奖状,他会拍一张,要何明帮忙做到相册里,中学毕业,又是一张,都标好了时间、地点。去公园划船有一张,爬山要一张,有山有水,他都有道理。五六年来,他一年给一位家人做一本相册,做完了老婆、儿子、女儿,甚至还做了一本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从年轻时鬈发白裙子,到老来一头银发依然旗袍披肩。老贾说:“她人好,但一生没有嫁。”
春丽早就看出苗头,于是那一本神秘女士的,做之前就把相册的钱收好了。但收完她又后悔,因为明显这一本,老贾的要求多而反复,解释照片的时间也长,心意纠结,语焉不详。男人的友情,是不会当着内人的面问到细微处的。何明虽然心里也略知一二,但从来不会探听。老贾会说:“这条裙子是奶咖的,不是白的,也不是黄的,你帮我调一调。这条裙子当时要四十块钱。很好看的。”何明于是就用Photoshop调一下,对他来说其实是举手之劳。
“那本相册,你还记得吗,我给她寄去了。她很喜欢。谢谢你,完成我一个心愿。”老贾对何明说。
“我们何明真是对你好得不得了,翻来复去修了十万八千遍,只算普通的钱哦。”
春丽觉得老贾代表了再老实的男人心里也是不老实的,再爱子女的父亲心里也是有“奶咖”裙子的。老贾的心愿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但他的这个心愿和那个心愿又是矛盾的,怎么也摆不平。何明却说:“他都老成这样了,对自己坦诚一点,又能坦诚几天。”
“说不定明天就死了。”何明补充道。
春丽知道何明又发倔脾气,真是受不了他。其实谁又能比春丽更懂得何明的好,当年儿子只有两岁大,第一声“爸爸”叫的是何明。二十年来,何明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天意弄人。但说到底,他想穿了,做做自己的爱好,也对春丽儿子用了真感情。更何况憋尿是假,目送是真。其实儿子离台那日,何明胆结石作祟,他一直忍着剧痛,直到最后都帮儿子拖着登机行李。儿子的身影一消失他就哭了,整个人软在地上,扶着春丽说:“老婆,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医院。”
“这里是机场啊,到哪里找医院啊!”春丽脑子一乱,血压飙升,反倒是像个白痴一样愣在原地。何明看春丽六神无主,满脸急汗,疼得一句话说不出,硬撑着拖着春丽的手,上了机场大巴。那一刹那春丽的心都碎成饺子馅,她还没来得及从告别儿子的伤感中恢复过来,转而又被这位憨傻的丈夫感动了。二十年来,她第一次有了他们这辈子是要永远一起受罪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一点也不幸福,她觉得人活着怎么那么麻烦啊!没有一分钟可以喘息。
“蛮好叫个车的。”事后春丽对何明愧疚地说。何明则淡淡说:“下次吧。”
春丽知道,何明是不想让儿子担心,也不想让她多花钱。
也就是那次生病以后,何明性情变得柔软了一些,常常会在家里看电视时握住她的手,或者在早起看母亲的时候揉揉她的腰说:“不然晚点走。”春丽一直以为自己连夜照顾这位疼过十支吗啡的“二道丈夫”,终于劳苦功高地获得了相濡以沫的报偿,殊不知何明排泄出那颗米粒大的结石之后,依然对生活是有脾气的。
“人家老婆是二婚温良恭顺抬不起头,我老婆是二婚凶得很,倒活像我是二婚。”
这话说得那么重,春丽才意识到原来一直以来,何明不是口拙不会讥讽她,而是在让她。体悟到这一点,春丽也不知道是喜是悲。这一切尴尬的局面,竟还被老贾看到,他们两家也算扯平了。
是年老贾七十八了,他说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八十三,所以最后一本留给自己的相册,他打算慢慢做。
“慢慢做”这三个字听在春丽耳中就是“奥客”的代名词。如果来的全是老贾这样的客人,他们全家都要喝西北风去了。老贾也知道春丽心里对他不欢迎,他年纪虽大,到底脑子很清楚。一般来说,他会问何明春丽哪天到母亲家去,他找春丽不在的时候来。春丽则说他是“老鬼,以前做匪谍的出身”。
何明努力在老婆和老贾之间平衡,其实他也知道不该那么顶撞春丽。春丽是一个本分的老婆,若不是生活艰难,也不会把自己打造成小市民。她爱美、喜歡听好话,心也软,照相馆里挂满了春丽各个时期的照片,但顾客总是很不会讲话地问春丽:“这照片里的女生好看的,是谁呀?”
春丽也不动气,只说:“是呀,年轻女生就是好看。”
何明帮春丽翻新旧照,从来不问她笑得那么明媚,镜头对面是谁在拍。
生活里总是有很多秘密,何明经营这间不成功的照相馆以来最大的收获,便是知道了人的一生都会有过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完全不影响生活。过时的秘密是青春里最值得回味的东西。
老贾拿出了自己的百日照、和父亲母亲的合照、上小学的照片、参军的照片、退伍的照片、恋爱的照片、结婚照、抱着新生儿的照片、第一次带孩子去日本玩的照片……太多了,一本做不下,于是做第二本。做第二本时,何明对老贾说,不用先付钱了,做着再说。
老贾说:“我还想做第三本……这第三本,我要先付钱的。我给你写一个地址,你记得去找这位小姐。如果我走了,你帮我送给她。如果她也走了,你记得烧给我,不要给别人了。”
何明答应了。春丽在心里白了全世界男人一眼,也答应了。但谁都不晓得,老贾一语成谶。
最先发现老贾很久没有来的是春丽。她问起何明:“老贾最近越来越精了,是不是连我上厕所的时间都要算准了再来,不让我看到。”
何明抬起头说:“他是一个月没有来了。”
“不知道会不会怀孕,哈哈哈哈哈哈!”
春丽被自己的小聪明笑得前俯后仰,没想到何明一点都没有笑出来。她觉得自己大概是开错玩笑,毕竟何明从来没有给她机会说过这样的话。但春丽不是这个意思,她取笑的是奥客老贾,他还有相册钱没有付呢,照片也都落在他们店里。怎么人消失了。
“怎么人消失了。”何明喃喃自语道。
问遍整个小区,何明才知道,老贾也在找他。
老贾是半个月前中风的,中风以后直送加护病房,半边不能动了。医生仔细检查,又发现他脑出血。弥留之际,老贾一直都支支吾吾叫着“何明,何明”。家人都以为那是某种食物,他想要走前吃一下。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人名,没有想到他临死前要见的人竟然是一个摄影师。
在何明找他的時候,老贾的家人也在找何明。待何明与春丽终于到医院病房,见到那些照片里他帮忙去掉皱纹的老妇人、去掉痘痘色斑的女儿和儿子时,何明觉得自己早就认识这些人了,了解这个家族的许多事,只是他们一个也不认识他。这些人甚至感到疑惑,疑惑中还带着某种难以名状的紧张。
何明不理会这些眼神,他握着老贾的手说:“老贾,你是不是想拍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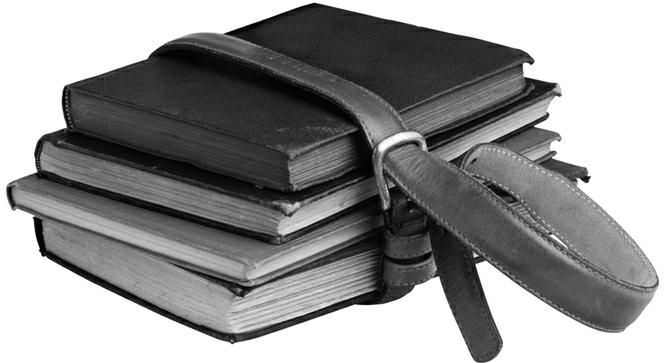
老贾艰难地点点头。
何明又问:“你是不是想和儿子女儿一起拍照?”
老贾摇摇头。
何明说:“我把照相机背来了,你是不是想拍一张自己的照?”
老贾点点头,他还示意老伴要坐起来。护士帮忙将床调整为坐姿。老伴毫不避讳地指责他“实在不想多活几秒钟,脑子有病”。
老贾真的病了,他半边的脸是瘫痪的,带着氧气罩,看起来真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春丽被这个场面吓傻了,她从前那么讨厌这个人,但断然没想到他会一夜间变成这个孱弱的面貌。春丽觉得自己错了,老贾其实是个挺好的人,爱照片、爱家人、不逾矩,也不怎么赊账。
老贾还想要自己穿衣服,只可惜,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他的子女也不希望老人这么折腾,女儿一直在小声抽泣。何明看了她一眼,想到她一年级的奖状,觉得老贾没有错爱她。何明没有什么权利提要求,只适时说:“老贾,这个衣服也可以的。你坐好,尽量笑一笑。”
见何明对焦,护士帮忙摘掉了氧气罩。那一瞬间,老贾像是回光返照,眼睛突然变得有神起来,嘴角咧开,可惜是歪的。
何明赶紧按下快门。
老贾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钱,钱。”他眼睛朝着何明夫妇掷去坚定的光。护士又将床摇下。
这么重要的话,堪比遗言,所有人都当没听到。只有春丽听到了。春丽想,老贾真可怜,说话都没有人听。
何明当日回来就开始修照片,整日没有睡。翌日接到了老贾家人的短信,老贾拍完照后四个小时就走了。走前什么话都没有留下。而病床上的最后一张照片,成为了老贾相册的压轴。从百日照,到临终前四小时,大完满的一生,统统留了影像。
何明夫妇在老贾的追思会上哭了一场,他的家人收下四本相册时显得有些麻木,何明把放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的话对老贾的太太、子女说:“这是你爸爸一生心血,精心挑选,他在我这里做了好几年。你们一定要好好珍藏。这是旧照片,也还给你们。”
谢谢。他们淡淡说,都没有打开相册望一眼何明通宵达旦赶出来的成果。亲生子女也不过如此,何明心想,也就安了心。
倒是何明夫妇按照老贾留下的字条找到“这位小姐”家时,那位白发苍苍的小姐看着何明还给她的旧照,眼眶红了又红。她大概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照片藏在老贾身边,老贾思来想去觉得最适合藏匿这些“青春罪证”的地方竟然是何明的照相馆。她蹒跚着去找钱硬要付给何明。
何明说:“你的这一份他早就付过了。”
老妇人愣了一下,说:“那他还有没有付过的吗?”
何明看了一眼春丽,春丽说:“都付过了。都付过了。”
老妇人笑了,笑得那么尴尬,喃喃自语道:“我知道的,他除了我,谁都不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