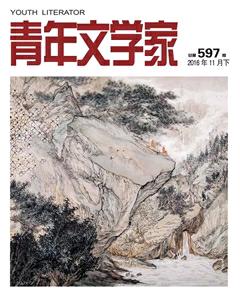浅谈《诗经》中“赋”、比、兴手法的应用与发展
马尧
摘要:“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重要的表现手法,三种手法的运用使得诗歌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颇具特色。这些表现手法不仅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风格,也为探究古代先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宝贵财富和丰富的资源,而其在后代的发展过程中又展现出日趋完善,不断补充的态势也极大丰富了古代诗歌的中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诗经》;“赋比兴”;分析;应用与发展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不仅在内容上涵盖古代先民生产生活诸多方面,其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亦有相当大的考究意义。今天我们常说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就是根据诗经内容体裁与表现手法上来说的,将其混为一谈则是完全错误的。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显然作法和体裁是诗的两个角度两个方面,其实关于“赋比兴”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之后呈现不断积累,不断成熟之势。从《周礼·春官·大师》中可以得到“教六诗……日赋,日比,曰兴”的概念,到了汉代《毛诗序》便对赋比兴的定义更加明确化,系统化。直至今日对这种手法沿袭也一直存在,下面我们就仔细分析诗经的赋比兴以及后世的沿用、变形和发展。
一.诗经概说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取整数称《诗三百》,相传有采诗官深入田问地头进行采诗,后由孔子编订。西汉时期推崇新儒学,《诗经》则被尊为儒家经典,而《诗经》也是在这一时期变为了“官学”。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手机了各地民谣(共十五地,也称十五国风),大量记录了古代先民对亲情、爱情、劳作、迁徙等活动的歌颂与赞美,但其中也不乏反对欺凌,不甘压迫的作品,充满美刺意味。《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内容多为贵族文人祭祀歌谣,祈福先祖,风调雨顺,其中也包含夜宴歌咏等娱乐之作。《小雅》中也收纳了部分民歌,反映百姓诉求,像《采薇》、《东山》等富有情感,温暖徜徉的作品。对于《颂》的解释,见于《诗·大序》:“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可见《颂》是与宗庙祭祀活动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想要研究春秋时期祭祀活动往往取证于诗经里的《颂》,其也分《周颂》、《商颂》、《鲁颂》。大体上讲,风、雅、颂是按不同音乐分的,而赋、比、兴是按表现手法来分的。诗经的特点在于他的语言风格,重章叠句,曲调悠扬,后世沿用这些特点突出的表现手法是司空见惯的。
赋、比、兴始记见于《周礼·春官》,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中解释:“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便很清晰的将“六义”区分开来。
二.赋一直陈其事,铺陈叙述
对于赋的含义,郑玄在《周礼注》中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惡”,认为其是平铺直叙,好比今天的我们所说修辞手法中的排比,使诗文中每一章充满乐感,重章叠句。典型代表是《诗经·豳风·七月》叙述农家人在四季中的生产生活。
挚虞在《艺文类聚》五十六卷中提到“赋者,敷陈之称也”,他一改汉赋的繁杂申述,提到“以事行为本”,则说明了“赋”的表现手法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描绘意象、循序渐进、重章叠句,更要有指摘时弊,有意义、有内涵的思想内容。宋李仲蒙也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便很接近今天赋的含义了,所以“叙物”并不是简单的铺陈直叙,还必须添加情感,客观意象与主观情感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情感表达的出神入化,淋漓尽致。简言之,“赋”不必借住外物,不像“比”和“兴”必须借助具体的物象,只需直抒胸臆便可,正所谓“随物赋形”。
《诗经》中对于赋的运用最为广泛,“国风”尤为突出,就拿《七月》为例:春耕开始、妇女蚕桑、制作衣帛等等,共描绘了一年之中不同光景的生产生活。像期间描述的“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爿斤,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运用简单的事物罗列堆积,毫不含蓄的直接表现农家八月割把芦苇,三月剪桑树。用斧头砍掉长枝,攀着细枝摘嫩桑的生活场景,这就是“赋”的表现手法,突出重点,直陈其事。
对于“赋”的用法具体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为描物。比如最熟悉的要数《诗经·秦风·蒹葭》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唏”、“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每章开头的意象描写将清晨微寒、夕阳异彩、芦草的千姿百态临摹的拍案叫绝,既朴实无华又将主人公爱慕伊人的失意惆怅、无可奈何描绘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第二种是写人。比如《诗经·邶风·静女》中说“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短短四个字“搔首踟蹰”将男子内心的渴望与急迫表达的一针见血。除了描摹景物、刻画人物。其实如果再细分的话,“赋”还可以描绘某一过程,比如《魏风·伐檀》中“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记录了劳动人民合力伐檀的情景,从中不难看出那些杂揉着不满与悲愤而又无奈的复杂心理情感。总而言之,“赋”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在后代的发展中也是逐渐丰满,“通正变,兼美刺”。
三.比一以物比物,富于变化
相比“赋”而言,“比”的理解便较为容易理解,根据朱熹的解释“以彼物比此物”,就是今天的修辞手法当中的比喻,也有的说法是类比、比拟。用一个事物鲜明的特点来突出使人要表达的本体或情感,让晦涩难懂的义理变得通俗化,形象化。
《诗经》中这一手法使用尤为突出,比如《魏风·硕鼠》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道理显而易见,将剥削阶级的贪得无厌与伪善表现的尤为突出。再如《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硕人》中连续用“柔荑”来比作美人之手,“凝脂”比作美人的皮肤,瓠犀比作美人的牙齿,形象生动,画面感强烈。
这些“比”的手法与“兴”不同,“比”往往是两种毫不相干的事物进行比较,二者是同向的,并不矛盾,这种比的方法既可以将微小事物扩大化,使本体看起来黑白分明,更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又可以使难以理解的义理变得通俗化,这种收放自如,灵活多变的表现手法使《诗经》表现手法上的艺术贡献变的显而易见,为后人所运用。其实“比兴”手法往往联用,专用以指诗有寄托之意,所以比兴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兴”有时也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比如《国风·周南·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河洲鸣鸟兴起君子配偶。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看作是“兴”的“比”,所以比兴之间是有联系的,不一样的是“比”的运用本体和喻体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只是单纯用一物比一物。而兴则不同,往往与下文要引出的论述主体是有一定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诗经中还经常用比喻把抽象的心情具象化,也可以算作“比”。例如在《邶风·柏风》中“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如《卫风·淇奥》中“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语言重章复沓,言简意赅却不显骨感。
四.兴一起兴渲染,比似兴时
《诗经》中的“兴”,郑玄在注疏《周礼》时引用郑众的解释:“托事于物”(《周礼·春官宗伯·大师》郑玄注引),后朱熹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他物以此来铺垫。在《诗经》中,“兴”的作用大体分为两种,第一种只是在文中起到帮助押韵,引领下文的作用。比如在《小雅·鸳鸯》中提到的“鸳鸯在梁,戢其右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而在《小雅·白华》中又再次提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不难看出前者兴句与后者“君子万年,宜其遐福”的祝福在意义上是没有联系的,而《白华》中的兴句却是表达了作者的怨念之情,用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来反兴薄情寡义的丈夫。
“兴”的第二种用法是在兴起下午的基础上與下文有着含蓄隐晦的联系,这种联系看似山重水复,其实牵引下文。就比如上文所说的比如《国风·周南·桃天》中提到“逃之天天,灼灼其华……逃之天天,其叶蓁蓁。”将桃花茂盛美丽,花朵怒放的样子来兴起女子的容姣好,青春貌美。这种前后铺陈,物我交融的表现手法加之以联想与想象所形成的行文风格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诗经》中“比兴”的手法一直沿用,并且呈现出形式多样的笔法。例如《离骚》中,用“香草”比作忠君爱国情怀,以芙蓉比作清新脱俗,甚至用动物自喻等等。再如长篇叙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北朝民歌《木兰诗》都承袭了《诗经》中起兴手法的沿袭。而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在其基础上添加了美刺讽刺的内容,刘勰《文心雕龙》中说“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甚至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所以高举“比兴、兴寄”的旗帜,亦要强调诗歌的社会内容,用诗歌发挥社会意义。到了宋代更把“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清晰化,提出触物还要用以“动情”,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既索取物象又抒发情感,这样就不会像汉赋那样大量运动比喻比拟显得一丝冗长。
通过长期地研究,“赋、比、兴”的使用让人们看到了《诗经》的审美价值,这种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不断丰富和完善,而对于后世的变形与表现手法的分支则也大大提高了诗歌类作品的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