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神化”的《镜花缘》才是经典
朱锐泉
一年一度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总是不缺乏话题性。比如2015年2月19日甲午马年的春晚,在不少人眼中,尤其因为充斥着嘲笑“剩女”“女汉子”“胖子”“女领导”的段子,而被打上“歧视女性”的烙印,令人久久无法释怀。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当年2月25日的报道称,至少令人欣慰的一点是中国新生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抗议得到了回应。据说,网络上发起抗议春晚歧视女性的请愿书征集到了1300个签名,并且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和社交媒体用户的支持。
两年之后回眸这一事件,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不断有人拿对待女性态度作为衡量当年春晚的其中一项指标,而且深层反映出类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容易发生的举国上下对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高度敏感。
俗话说,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上一次女权主义的话语强势登陆中国,还要追溯到晚清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
现代小说的巨擘鲁迅曾言“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明白揭示了稗官野史在古代社会的低下地位。但在清末民初,经历了日本、欧美风雨沐浴的梁启超等人,为了追求“新民”目标,开始有意识地拔高通俗小说的地位,以提倡“小说界革命”来变革百姓的思想情操。
这一衣钵到了“五四”时期,得到胡适等人的继承传扬。古代小说研究,也并非仅仅是现代学术演进的一个环节,而成为整个社会思想嬗变的一种症候式反应。由此视角以观,晚清萌發,至1923年胡适文章《〈镜花缘〉的引论》酝酿而成的对于清代中期章回小说《镜花缘》的女性∕女权主义解读,就成为我们了解、评说古代名著之神化历程的一个上佳案例。
李汝珍(约1763—1830)为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人。他字松石,号二铭,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20岁到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定居。《镜花缘》一书是李汝珍35岁开始写作至53岁结束的作品。
这部小说,今日的学界一般沿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说法,认为是清代学问风气的产物,属于“才学小说”的代表作。作者本人也拥有着音韵学家的头衔。故而余集在其所著《李氏音鉴》的序言中如是介绍:“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求源索隐,心领神悟。”这些时人眼中的“杂学”,也都进入了虚构人物的世界。而李氏友人许乔林则在《镜花缘序》中评价小说:“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即饮程乡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综其体要,语近滑稽,而意主劝善,而津逮渊富,足裨见闻。”直到宣统二年(1910)华琴珊著《续镜花缘》时,还在第一回开头,向前人致敬——“国朝李君松石所撰《镜花缘》一百回,繁征博引,感慨苍凉,妙绪环生,奇观迭出。”
值得一说的,是全书设置了百花仙子贬谪下凡,化身百名才女欢宴赛文,并参加唐朝武则天治下科举考试的故事框架。由此,对于女性性情才学、禀赋品格、事功前途、家庭婚姻的描写叙述,就成为小说的重要组成。
《镜花缘》对于妇女问题的呈现与讨论这个特点,早在清代读者那里,就受到重视。例如《负暄絮语》中载有一段评语:“《镜花缘》在说部中,为晚近之作,文笔视《红楼》《水浒》,良有不逮,然而诙谐间作,谈言微中,独具察世只眼,似较他书为胜。其言女学女科,隐然有男女平权之意味。”《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收入《小说丛话》,作者之中的定一也说《镜花缘》:“其述当时才女,字字飞跃纸上,使后世女子,可以闻鸡起舞,提倡女权,不遗余力。”
至1923年2月到5月,胡适撰写《〈镜花缘〉的引论》(收入《胡适文存》二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的论点逐步产生巨大影响,开始为许多人所接受。胡适认为:
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胡适明言:“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在另一篇发表于1924年的英文论文《中国的女权宣言》中,胡适认为《镜花缘》既批评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又提倡了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他进而提出,《镜花缘》是“中国的女权宣言”。
在胡适身后近百年的学术史上,他从女性主义角度对《镜花缘》的分析、评价,起到了类似典范的作用,主宰着相当一批研究者的观点。林语堂就在发表于1935年的《中国古代的女权主义思想》一文中,称《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女权主义小说。
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东原著《中国妇女生活史》。著者将李汝珍的观点归纳为七层:反对修容、反对穿耳、反对缠足、反对算命合婚、反对讨妾、承认男女智慧平等、主张女子参政。后来台湾鲍家麟《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一文,又对胡适观点继承、深化并作出局部修正。这篇原载《食货月刊》复刊1卷12期的文章(后收入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79年版)认为,“《镜花缘》中所见李汝珍的女权思想可约略归纳为六端。他反对双重道德便准,反对缠足,反对涂脂抹粉,反对算命合婚,提倡女子教育,更进而主张女子参政”。其中就第一点展开论述时,鲍氏声明不尽同意胡适的论点,“事实上李汝珍并未反对贞操观念,反而赞扬旌表节烈妇女之举,他所深恶痛绝的是男子纳妾,也就是觉得男女应有同样的严格道德标准”。
后来张蕊青径直以“先锋”小说看待《镜花缘》。在《为女性谋解放的“先锋”小说——〈镜花缘〉》(《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中,她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镜花缘》的主题具有多向性,妇女问题不是《镜花缘》探索的唯一问题,但在长篇小说中,《镜花缘》是对妇女问题探讨得最全面、最深人的第一部,则是毫无疑问的。李汝珍是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讨论妇女问题,小说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民主主义倾向和批判封建礼教的精神,尽管还不够彻底,还有点游移不定,但确实已经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准。
对《镜花缘》的女权主义解读的最大挑战来自于以夏志清(Chih-tsing Hsia)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夏志清在《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The ScholarlyNovelist and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Ching Hua Yuan,黄维樑译,《幼狮月刊》第40卷第3期,1973年)一文中指出,《镜花缘》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妇女观提出挑战,相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完美女性形象,“书中的一百多个才女个个裹小脚”。《镜花缘》赞扬了一种与传统道德观相符合的女性美德和才智。李汝珍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不是儒家,就是道家,或者是亦儒亦道。所以他不可能像鲁迅在他短篇小说里所做的那样,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镜花缘》里的三位女主人公—唐闺臣、师兰言、孟紫芝——在夏志清看来,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护卫者”。夏志清总结道:“小说的主要寓意就是要弘揚一种中国式的妇女形象以及与之相称的美丽,品德和才智。”
与之形成同调的,还有美国汉学家白保罗(Frederick P. Brandauer)。他认为《镜花缘》更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在《〈镜花缘〉中的才女们:一种符合儒家理想的解放》(Women in Ching-hua yuan: Emancipation toward a Confucian Ideal,《亚洲研究学刊》1977年8月)一文中,白保罗完全不同意《镜花缘》是“女权主义宣言”这一观点。他详尽分析了《镜花缘》中才女的描写与班超《女诫》之间的对应关系,据此认为《镜花缘》塑造的才女们就是脱胎于早期儒家描绘的理想妇女形象。
应该说,夏志清得出作家之作不过是为了“写给朋友消愁解闷,炫耀才学的作品,以娱悦和自己性情相通的学士”这样的观点,更加切合古典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常规生态,有效地避免了在文化价值判断上流于偏激的风险。他正面批驳了胡适给《镜花缘》的溢美之词,也同时区别于那些苛责作家思想不够先进的论调,转而主张作家的道德观、妇女观与文化理想仍从属于传统社会的辐射范围。
随着时间推移,海外汉学界的这一派观点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也是在世纪之交回眸时,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对胡适的观点给出了商榷意见。汪文认为,“妇女问题”确是《镜花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胡适对之极力关注并大加弘发,自是出于其推行新文化的热诚,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接触到了李汝珍创作是书之实际。只是仅以妇女问题为《镜花缘》之主旨,则忽略了该书其他方面的思想倾向,而所谓男女平权之类的思想,也有“削”李汝珍之“足”以“适”西人思想之“履”的嫌疑(《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P62)。
接下来,对于胡适为代表的、“神化”《镜花缘》女性问题描写的学术观点,学界也开始出现清醒的声音。四川宜宾学院王洪泽《“神化”的实质是“误读”——对〈镜花缘〉中妇女观念的再认识》(《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就释放了这样的信号。作者认为《镜花缘》中的妇女观念并未表现出超前的意识,倒是其中反而夹杂着许多的传统意识和封建残余思想,从而导致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他进而指出,对《镜花缘》的过高评价,本身正源自一个误读,文中的妇女观念也在学者们的一片叫好声中,戴上了一个人为的光环,全书的思想意义已经被“神化”了。
王洪泽恰当地评估了《镜花缘》中的女性观念描写:小说家受当时思想的影响,对妇女的地位作了一些思考和认识,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而又没有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于是在叙述中难免会前后矛盾,难以深入所致。这只能说明,小说家已经开始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仅此而已。
这里顺带提及《镜花缘》与其前驱之作《红楼梦》的关联。一粟编的《〈红楼梦〉书录》将《镜花缘》列为《红楼梦》的“仿作”。实际上,曹雪芹写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闺阁昭传”,而李汝珍笔下小说第四十八回《睹碑记默喻仙机 观图章微明妙旨》,唐小山看到泣红亭的碑记之后,有泣红亭主人的总论一段,也同样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信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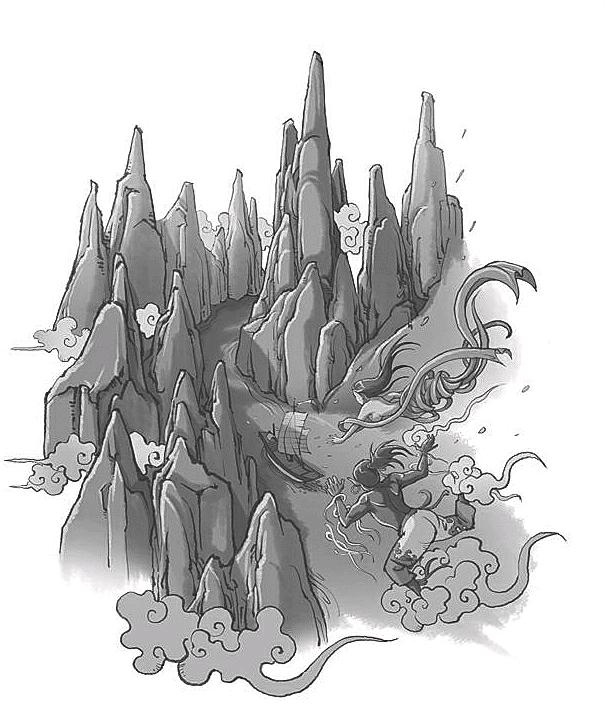
但考察作品实际描写,可知两位小说家的才女意识存在显著差别。阎续瑞《〈镜花缘〉与〈红楼梦〉才女意识之比较》(《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月,第1卷第2期)一文指出了他们宣扬女才的立足点不同。也就是说,李汝珍提倡的女才依然从属于女德,所以,《镜花缘》在开卷便引用班昭的《女诫》所谓“德言工容”作引以阐明其主旨。他的思想尤其是妇女观虽有一定的进步性,却依然受到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所以他没有为众多才女提供一个独立自主追求爱情与婚姻的空间,没有深刻挖掘众才女内心的真实情感,只是让她们在赢得才女的美名后依然走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步人婚姻、遵从 “三纲五常”相夫教子的道路。曹雪芹认可的女才则超越了传统女德观念的束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丰富。
中国人常说,百年之后,可论学术思想之升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胡适由尼采“从新估定一切价值”,来谈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意义》)。同时的旗手陈独秀更在《偶像破坏论》的文章里呼吁:“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原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这颇能从又一个世纪之交得到回响,王菲的歌曲不就这样唱么,“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开到荼蘼》)。
如果把今人对古代名著的神化,与古代读者大量的阅读反应对照起来,不难发现“厚古薄今”的思维惯性在起作用。罗浮居士給嘉庆九年(1804)《蜃楼志》作序称:“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神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这种批判性的阅读态度,值得后人学习。实际上,即便是古代小说中的经典名著,在清初刘廷玑看来,也还有一个“人之善读与不善读”的问题,正所谓“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在园杂志》)。
谈到古代典籍祛魅后对今天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于一般鉴赏评论的文学接受者来说,应尽可能区分作者叙事意图与文本客观意蕴。虽然清人谭献有“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的通达之论,但众所周知,知人论世、言必有据才是研读作品文献的一条康庄大道。对于专业学者来说,与其学术观点稳健趋于保守,切切不可代以用极端夸张的口号进行鼓吹,一味追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者,只能落得欺世盗名的历史定位。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开世人无限眼目的明清小说评点之中,汲取正确的阅读心态。笔者希望与当代读者分享其中的两则: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十回批语
“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
——1803(清嘉庆八年)刊印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回评
正如同“人不可无癖”一样,文学作品也是“真玉有瑕”的。我们在摈弃了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外,反过来应努力提高欣赏“美人陋处”的眼光、素养、能力。如此,方不辜负了时间浪潮淘洗下依旧闪烁真金光芒的经典之作。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毕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