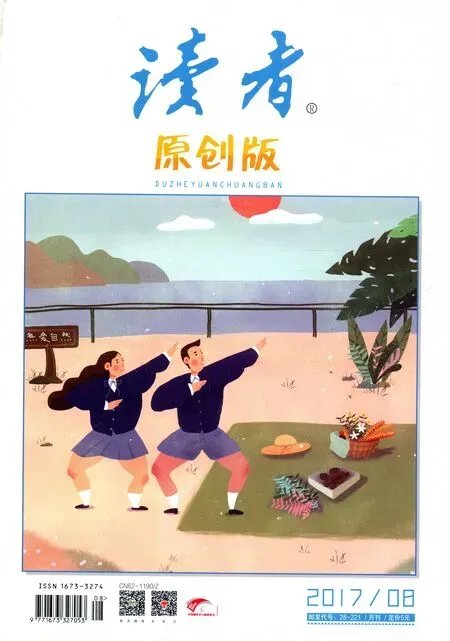语言的孤独
文|米 周
语言的孤独
文|米 周

一
一位同事的女朋友是日本人,有一次一起聊天,她说她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是Murakami Haruki。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把话题转到了别的上面。直到有一天我去逛书店,看见书架上正在销售Murakami Haruki的《1Q84》,我才恍然大悟:她最爱的作家是村上春树。第二天上班,我急匆匆地跑去找那位同事,兴高采烈地让他帮我转告他的女朋友,我最爱的日本作家也是那位Murakami Haruki先生。然而,我的这位同事显然不能理解我找到语言之桥的那种快乐。
在《圣经》里,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是从建造巴别塔开始的。在那之前,所有人都说着同样的语言。直到大洪水过后,人们打算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高塔。这触怒了上帝,于是上帝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彼此无法交流,也就不能继续建造巴别塔。写出这个故事的人一定和我一样,感受过语言的孤独。语言的孤独就像个魔咒,而这个魔咒有着不同的层次,层次越高越孤独,而且越难治愈。
最初级的语言孤独,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根本不会说或者只会说一点点当地的语言。这时候产生的语言孤独,和语言关系不大,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孤独。比如当我到波兰旅行,我不会讲波兰语,而波兰人又不怎么讲英语,所以基本没法和当地人交流。打开电视,所有的节目我都看不懂;坐在餐馆里,所有的菜谱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文盲”。这种孤独感其实比较好克服。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有时候甚至还有些乐趣在里面,因为当语言不通带来麻烦的时候,你需要动脑筋想办法。比如想去火车站不知道该怎样讲,就模仿火车进站的声音;想吃牛肉不知道怎样讲,就在头上比画出两个犄角。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做错了事,也可以赚取同情,得到理解。
二
第二阶段的语言孤独藏在文学作品里。这时候,就没那么好玩了。
我刚刚看过三岛由纪夫的《春雪》。虽然我被里面美妙的爱恋所打动,但仍然觉得,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这些日本作家,虽然行文流畅,但有时让我觉得不过就是堆砌辞藻罢了。作品有时似乎衔接得并不是很好,少了一些穿针引线的东西。直到前两天,我在豆瓣网上看到一位旅居日本的网友写的一段话,他说“夏天结束了”在日语里面并不仅仅表示夏天终结的意思,更有可能是在说“恋爱结束了”“童贞失去了”“女孩子月经初潮了”,或者说“一切全都完了”。看到这里,我猛然想到《春雪》。我把书又找了出来,翻到小说开始不久,清显带着本多和两位暹罗的王子去父亲位于海边的行宫度假。其间三岛由纪夫写到了清显对聪子的思念与误会,也写到了两位王子对情人的思念。章节结束时,末尾一段赫然写了五个字:夏天结束了。
原来,三岛由纪夫很早就埋下了草蛇灰线,预示了清显与聪子的爱情悲剧,甚至在此一箭双雕,顺带连两位王子的命运也一并做了交代。只可惜我读的是中文译本,自己又不懂日文,读到“夏天结束了”,就当真以为只是说夏天结束而已。
这不禁让我想到,《春雪》这本书中,到底还有多少被译者抹杀(当然有时并非译者的错)的细腻心思,不得被我所见?而我读过的所有译文中,又有多少是我真正领略到了文学作品的趣味,而不是仅仅读了一个故事呢?
第二阶段的语言孤独,阅读译文的读者无疑能感受得到,然而更大的孤独感应该来自作者。我的美国同事得知我出过几本书,都说要看。但得知只有中文版本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由些许的敬佩转为了一种调侃—“哦,所以你才敢告诉我们吧?”“我可是有朋友懂中文,你不要骗我们啊。”每当这时候,我更同情的是那些生来就只能用小语种写作的作家。我熟悉的作家大都来自英美,除此之外,也有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德语这些大语种的作家。对于斯瓦希里语、僧伽罗语、阿尔巴尼亚语,我似乎想不出使用这些语言的文学家。有些语言甚至都没有专门的译者,比如我读过的一本冰岛诗集,是中文译者参照着英译本翻译过来的;而那个英译本,又是英国译者根据瑞典语译本翻译过来的。一首诗被倒了三次手,才从作者到读者,如果作者知道这件事,估计会抑郁而死。
三
语言孤独的第三阶段,出现在当你了解一门语言之后。
上大学那会儿,我在法国,由于有语言环境,我的法语一度突飞猛进。我曾经觉得,我的法语如此之好,以至于我好像窥探了身边所有法国人的秘密。然而一门外语,无论你说得多么好,它总是会在某个时刻给你出一道难题,明确地告诉你,它并不属于你。
我在读大学时参加了一个戏剧社,每周上课的时候,老师都要让同学们即兴表演话剧,我是这门课上唯一的外国人。有一次,我们在表演一个类似于法院宣判的场景,我的角色是法官。被告人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杀了酗酒家暴的丈夫,因而必须被判刑。根据剧情设定,我要在宣判之后对寡妇说一句类似“实在抱歉,我也无能为力”的话。
那句台词是“Je suis impuissant”,而我当时因为紧张,一时间忘了这句台词,便临时想了一句“Je peux rien faire”。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这两句话表达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表演结束之后,老师总结说,在台上最好不要轻易改台词,比如“Je suis impuissant”的话外音是“我不想判你刑,但法律如此规定,我也无能为力”,但如果改成了“Je peux rien faire”,就有些敷衍的意思,好像在对人家说:“我什么都做不了,就这样吧。”
我当时坐在台下,心里无比委屈—我怎么能知道这两句话在法语里会有这么微小的差别呢?我是外国人啊!但我的心情没办法和任何人说,因为不会有人懂我的。
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多了,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孤独感。那门戏剧课,我后来再也没有敢随意发挥过,每次都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记住每句台词,也因为如此,我觉得它不再有趣,那个学期之后再也没有去过。
四
语言孤独的最后一层,是当你在外面转了一圈,体会了所有的语言孤独之后,回到家乡,说着自己的母语,却忽然因为想不到某种表达方式,而被卡住的时候。
我在美国工作,周围的同事都是美国人,我最长一段没讲中文的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到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我脑子里面主管语言的部分感受到我的母语快要丢失的压力,我会在说着英文的时候忽然蹦出中文词语。我当时说得非常流畅,以至于自己并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我的同事提醒我,说最近我总是讲一些奇奇怪怪他们听不懂的词语,我才察觉到。
这种情况反过来更可怕:你明明知道你说的英文是什么,却想不到对应的中文。
我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会上向别人做presentation,形式一般是用PPT,花半个小时,向对方讲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需要对方提供什么帮助或者反馈。有一次,我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presentation,家里打来电话,我妈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准备一个……”我妈不懂英文,显然不能跟她讲presentation,但应该用中文里面的哪个词代替呢?演讲?报告?汇报?演示?最后我选择了“汇报”。所以,在我妈的印象里,我每天忙的就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想不到中文词更让人感到孤独,就好像回到了久违的家乡,但再也没有认识的人了。
我曾经想,如果将来我有小孩,一定让他们从小掌握三种语言,这样也许就不会像我一样,体会到如此多的语言孤独。但仔细想想,语言不过就是一串音节、一组符号,本无意义。不同地方的人赋予其意义,并自得其乐,本是一件美好的事。就像出门远行一样,既然有勇气跨过一座座横跨溪流的桥,就别怕有孤独陪伴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