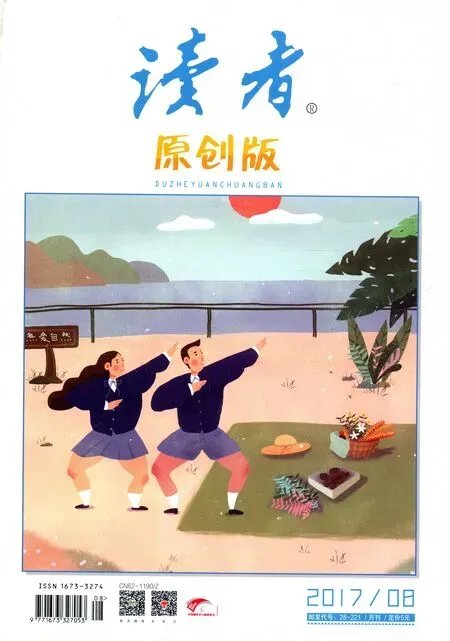上海邻居
文|铜豌豆
上海邻居
文|铜豌豆

楼上的上海老两口中,我更喜欢老太太。
她瘦且白皙,下巴微微内收,一头银发,时常在外衣上套一件马甲,一排纽扣工整而静默,带搭扣的黑布鞋一尘不染。她下楼时会扶楼梯扶手,脚步轻盈,没什么动静。我常与她在楼道里遇见,她总是不吝对一个中学生报以微笑,并适时奉上问候,“上学去啊”“回来啦”“吃饭没有”。
支援三线建设到西北多年,老太太的口音辨识度依然极高,浓重的上海腔,黏腻婉转,好像永远也不会愤怒,像糖锅里拔丝,螺蛳壳里挑肉。说话大抵也能成为慢工细活,时而是快要起势的歌唱,时而是即将收尾的吟咏。我家住一楼,是她出入的必经之地,常能听见她与人打招呼或有片刻的闲聊,那个声音恰到好处,听得见但又不钻耳朵,进退有度。
老太太手巧,每年端午都会送来两个肉粽,软糯醇香,每一粒米都沾着肉味儿。她几乎每年都重复着同样的话:“这边买不到大的粽叶,要是在我们老家,能包更大的粽子。就是个心意,你们尝尝。”有一年端午,我们都不在家,老太太直接把粽子挂在门把手上,但家人都知道那是她挂上去的。这边的人,没有包肉粽的习惯,更做不出那么鲜美的味道。
看上去,老头儿是在另一个极端—一年四季穿深色中山装,旧得不像样子,戴一顶蓝色有檐儿的帽子,草绿色解放鞋,略微驼背,衣服裤子都很松垮,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大而圆,像是随时要提问。
老头儿的细致,在纤毫之间。走在路上,他总是低着头,看见煤球便捡起来,摘下帽子盛着端回家,这令我常常把他与上海人区分开—那样一个光鲜洋气的国际大都市里来的人,怎么会捡煤球呢?又怎么会把煤球放在帽子里呢?但是他一张口,的确是浓重的上海腔。
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踢着一个螺丝钉边走路,老头儿在背后叫住我,大约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只是不停地喊“哎哎哎”。我回头看他,他说:“这个螺丝钉不好踢的,有用的。”少年的倔脾气上来,自然不甘心,直接回道:“这东西又不是你的!”老头儿上前捡起螺丝钉,继续喃喃地说:“我捡起来就是我的。”
老头儿不知是何时退休的,早年承接些修自行车的活儿,常常满手油污。他走路仿佛抬不起腿,鞋底老是拖在地上,人也因此显得没精神。从那以后,他与我更不怎么打招呼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我主动开口,他会有回应。但那是极为僵硬的礼节,狭路相逢时对视,他的目光里也有不情愿。那个瞬间,双方都会为已经打过招呼或终于擦肩而过而庆幸。
就这样淡淡地做了几年邻居。高三那年秋季的一个雨天,放学回家时我发现钥匙落在教室了,父母也不在,只好在楼道里等。但很不巧的是,老头儿也在楼道里摆弄一辆自行车,不知道是谁家的。那是一辆“三枪”牌自行车,他不一会儿就修好了,起身拍拍座位,大声读出了后座上的英文字母:“BSA。”他背着手转了一圈,摇摇头,又兀自说了一句:“Three gun。”天哪,这么洋气的发音是出自这个老头儿之口吗?我向楼道里四下张望,企图找出另一个人。
我表面平静,内心开始暗流涌动—他从哪里来?他以前做过什么?他又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正暗自思忖,老太太系着围裙、扶着楼梯扶手走到拐角处,对着老头儿说:“吃饭了。”见我也在,照例亲切地问我:“吃了吗?”我说:“没吃。”老太太说:“怎么在楼道里站着?”“没带钥匙,等爸妈呢。”“那上来一起吃吧。”“不了不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这时,老头儿说话了:“走吧,先到家里坐坐也好。”
这个家与老太太一样爽利、整洁,想必是她的杰作。正想着,一双黑且粗壮的手把一杯茶放在我面前,抬头时,老头儿已换了雪白的衬衫,几乎要发出刺眼的光。老太太招呼我们吃饭,我的确饿了,便一屁股坐在饭桌前。白米饭,三四样菜,用小碟子盛着,印象比较深的是红烧扒皮鱼,不多的几条,做得精致,味道很好。老头儿捧着碗,时而看看我,时而低头吃饭,依然不怎么说话。老太太十分热情地招呼,一会儿夹条鱼放我碗里,一会儿询问我上学的情况。我倒是没有客气,先于他们好几分钟吃完了饭。当我望向对面的老头儿,他的饭碗四周竟然没有一根鱼刺。他抬头看我的时候,依然像要提问。
有一次,我正在午睡,外面传来连续而轻微的敲门声,我不耐烦地开了门,老头儿一如既往小心翼翼地开腔:“你的钥匙还插在门上。”说完,趿拉着老式解放鞋,弓着背转身离开。
这个不可捉摸的老头儿,尽管他以那样沉默的方式把鱼都留给我吃,尽管他雪白的衬衫一度光芒刺眼,尽管他提醒我收好就快丢掉的钥匙,但因为煤球、螺丝钉以及老旧的中山装、解放鞋,还是无法令我感到亲近。特别是那次,我在院子门口与人打架,寡不敌众落荒而逃时,恰好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撞见那像要提问又不置可否的眼神。老头儿无疑窥见了我全部的秘密,这令我羞愤难当,却也无言以对。我报以一个恶狠狠的眼神,转身离开。那一刻,我真的不想再见到老头儿,甚至连同那个讲究而白皙的老太太都不想再见到。
此后的生活并无二致,他依然在院子里低头走路,我在通往新世界的路上飞奔,俨然两套生活体系。高考结束后,我们的生活终于不再有交集。每年放假回家,我几乎没有印象是否再见过他,也不怎么能想起这个楼上的邻居。只是1998年的暑假,经历过武汉那次惊心动魄的大洪灾回到家里,一个傍晚,终于在单元门前遇到老两口,老太太依然热情地问候:“回来啦,好像瘦了。”老头儿依然一言不发。简单的寒暄后,老两口准备上楼时,老头儿转身轻轻地说了一句:“水好大的吧,小心。”
那天以后,我再没见过老两口。
在这个没吃到粽子的端午,对送来肉粽的上海邻居会有怀念,但想来也不遗憾。许多话大概不必说出口,许多事且撒手放过。头顶总是有反复流经的云,是白云就看看,是黑云就去收衣服。至于那个既令人感动又有意疏远的老头儿,他神秘莫测,似乎要提问的眼神里仍然有我曾经的羞愤。在骄纵又卑微、自信又恐慌、怯懦又嚣张、纯真又世故的今天,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一刻,这些往事已然成为面对未来的底气,就像老头儿从地下捡起的螺丝钉,“捡起来就是我的”。
图 | 孙 岳